杜甫在科考两次落第、干谒十年不中之后,向天子献赋,终于被看到了。
天子给了他一个小官:河西县尉。河西此地究竟在哪里,尚无定论。或许在河西走廊,或许在云南边陲,总之是个不太宜居的地方。杜甫以为这官实在太小,要求换个官做。天子倒也开明,直接给他升了职——兵曹参军,做官的内容:看守仓库。杜甫欣然接管:好歹还是在天子脚下,说不定有朝一日还能翻身呢。
但是,他得到这个官职,是在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
当时,杜甫在长安流落已久,已经敏锐地闻到盛世之下倾颓的气息。他知道此时繁荣只是表象,大唐早已危急四伏。但是一个仓库的看守员振臂呼号,又能引起谁的把稳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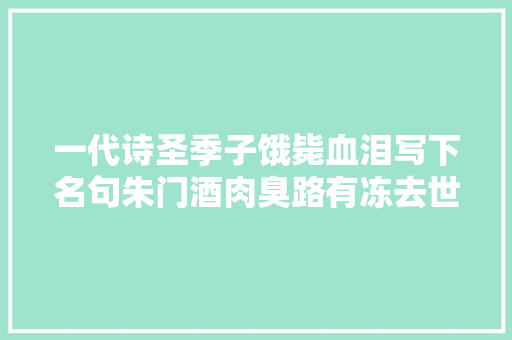
当他还乡探亲时,远远就听到家中有人在哀哀哭泣。他的不详的预感加重了。走进家门,眼眶发红的妻子尚抱着她小儿子的尸身。杜甫好歹是个小官,现在好歹刚过秋收时节,但是,他的儿子竟然活活被饿去世了。
惊诧、悲痛、愤怒……强烈的情绪席卷了杜甫的心脏。但他的意识里镇静彷佛始终占着上风:他不由悲哀地想:就连自己境遇都已如此悲惨,普通百姓又该是生活在若何的水深火热之中啊!
杜甫和夫人受到巨大的打击,痛澈心脾。安葬幼子、哭过之后,杜甫写了一首《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痛斥当时社会贫富差距之大:“豪门酒肉臭,路有冻去世骨”便出自此诗。
杜甫感叹自己:“穷年忧黎元,嗟叹肠内热”。他整日整夜为百姓的担忧,为国家的出息嗟叹,急得五内宛如火烧。他关怀的并不是一个又大又空的国家的观点,而是他亲眼见到的流落失落所的、背井离乡的、饥寒交迫的人,是他扶过的一双双瘦骨嶙峋的手,是他触摸过的失落去温度的皮肤,是他的国人更是他的家人。
比起残酷的现实,天子选择相信了更好接管的太平假象。他不再是励精图治的明君,整日沉迷玄门,希望在神仙极乐世界里永续生命;生活用度穷尽奢侈,“一骑尘凡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只是一个侧影。另一个缩写是“斗鸡舞马”:有500匹舞马生来就专门被演习做在天子生日宴会上演出的小丑。马的生命彷佛更该当去驰骋疆场,但他们被演习随着节拍排队、踏步、腾跃、下跪,给天子祝寿。李隆基沉迷在这种外界弗成思议的虚荣中许多年,直到至德元年六月,安史叛军攻陷长安。
七月,杜甫一片拳拳之心向着朝廷,希望能为大唐做出贡献,意欲投奔唐肃宗。然而途中不幸被叛军俘获,带到长安。
但是他不像王维还被投入了大牢,他的官位太小,连叛军都不愿囚禁他。就这么一个芝麻官,朝廷没空理他,叛军都不屑管他,他却在长安城急得团团转。只管没人听得到他的声音,他也要声嘶力竭地呼喊,为了他的国家。
此时,长安城封了,又一个春天却仓促地来了。
春天来得如此残酷,长安城成了一座暗澹的去世城,春天却还会准期到来,活气勃勃,野蛮成长。杜甫看着无情的自然,再次痛楚地流下泪来,写下这首《春望》。
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都城长安被敌军攻破了,但祖国的大好河山却一如往常;长安城的春天又来了,乱中韶光竟也过得如此快,不觉已春深如海。长安何时有过如此茂密的草木?都是由于人走城空,无人践踏,这些杂草才又得到了活气。看似是活气勃勃,实在却是荒漠之状。“国破”对“城春”,强烈的比拟和光鲜的反衬让长安城如今的惨象更加触目惊心。
司马光评价:“古人为诗,贵于弦外之音,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耐也。晚世墨客,唯杜子美最得墨客之体,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他皆类此,不可遍举。”
我感伤国事,涕泪四溅;鸟鸣惊心,徒增离愁别恨。
花鸟本来都是玩物,与闲适的感情挂钩,此处却也变成了惨景的一部分。这句诗要么是环境描写,要么是拟人,无论如何都在反用常见意象的含义。以是杜甫连着四句话,感情浓郁到不得不反复用比拟来突出,且也没有忘却“语不惊人去世不休”。
战火连绵,一封家书抵得上万两黄金。但黄金可求,若是家人已不在,家书便更是代价令媛了。烽火苦教家信断。这句诗非常普通易懂,但也因此更能引起大家的共鸣。战役来临时,最耐劳的还是平民百姓。
悲哀缠绕着我,我不住挠头,头发越来越少,发簪都要挽不住了。国破家亡,离乱伤痛之外,又嗟叹不觉已过不惑,险些还没有造诣就垂垂老矣,对当下现实又无可奈何,更增一层愁绪。家国之悲和年命之思夹杂在一起,杜甫内心忧虑。
杜甫的生平险些都是这样,被历史的大浪推着走——或者拍在沙滩上。
“无可奈何”这四个字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故事。但是他没有遁入虚空躲避,而是始终直面人生的惨淡和命运的悲苦,秉笔直书,不避丑陋,以心血写出沉郁抑扬的诗篇。
这又何尝不是最年夜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