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往常
作者:罗伯特·瓦尔泽
灯还在这里,
桌子也一贯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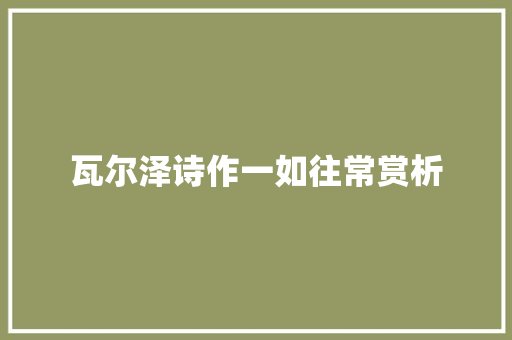
我依然在房间里,
啊,我渴望着,
连声嗟叹,也一如往常。
怯懦,你还在这里吗?
谎话,你也在吗?我听到模糊的应答,在:
不幸还在这里,我依然在房间里,一如往常。
《一如往常》在写作韶光上早于卡夫卡的《审判》和《城堡》,也早于所有进入世纪命题的伟大作家。纵然在本日来读,这首堪为先声的诗歌丝毫未在光阴中褪色,同时带给我们不轻的阅读震撼。
该诗很明显是一首室内诗。室内给人的感想熏染是局限。一个作家或墨客很难通过一首短短的室内诗表现时期。能做到这点,就解释写作者具有超强的捕捉力和表现力。我们在这首诗里瞥见的极其大略,不过是一盏灯、一张桌子和一个人。而且,诗歌在一开始,瓦尔泽就将三者全部进行了交代,“灯还在这里,/桌子也一贯在这里,/我依然在房间里,”作者利用的“还”“也”“依然”等语气副词就已经表明,这些人与物是一以贯之的存在。事物不新鲜,不即是感想熏染会随着迂腐。瓦尔泽将灯与桌子摆在自己面前,也摆在读者面前,产生的效果是深入骨髓的孤独。在瓦尔泽这里,孤独的不仅是他自己,还包括这些没有措辞的冷漠的物体。孤独使他和这些物体有了相同的属性。这时候的瓦尔泽想到的不是如何摆脱孤独,而是往孤独里沉浸,乃至“连声嗟叹”。
他为什么不想办法摆脱?答案是摆不脱,这个时期是孤独的时期。从诗题和每段的结束句“一如往常”来看,瓦尔泽自然不会时时坐在室内。他当然到过室外,但室内和室外是相同的性子,在哪里都摆不脱孤独的困扰。这不是瓦尔泽外在的孤独,而是充满全体时期的内在。以是,“一如往常”既是瓦尔泽内心的感想熏染,也是他对室闺阁外的空间感想熏染。当他从自身出发,表达出这一感想熏染,就使读者的感想熏染得到更深入地打开。我们从中创造,瓦尔泽诗歌蕴含的,的确是一个时期的内核。
如果第一段的灯光和桌子只是外在的描写,第二段则陡然进入了内在。我们乃至没看到瓦尔泽有任何铺垫,就直截了当地到了表达的核心,“怯懦,你还在这里吗?/谎话,你也在吗?”这两个问句令人读来惊心,瓦尔泽的问话剖开了这首诗的封闭。但他不是让封闭出来,而是让自己和读者能够进入。瓦尔泽将提问工具指认为“怯懦”与“谎话”,就表明瓦尔泽从自己的生活和环境中体会到二者是人无法摆脱的陪伴。我们从他的提问中创造,瓦尔泽早已体会“怯懦”与“谎话”不仅属于人,还属于物;不仅属于室内,还属于室外。正是它们的无处不在和无时不在,才成为当代人之以是孤独的最大缘由。
瓦尔泽知道自己提出的问题极为恐怖,而比恐怖更冷漠的是他听到“在”的“应答”。这让瓦尔泽明白,回答切实其实定就意味着“不幸还在这里”。当他更为肯定“我依然在房间里”时,我们能感想熏染瓦尔泽的绝望也便是卡夫卡随之将描述的绝望。人体会到个人的不幸,也便是体会到活着的不幸。瓦尔泽在这里表现的,既是自我的真实,也是时期的预言。
在罗伯特·瓦尔泽这里,不仅这首诗,包括他耗尽毕生心血的小说和散文作品,都没有被他生活的时期下决心承认过。纵不雅观瓦尔泽生平,坎坷不断,失落意落寞。文学上,他一贯郁郁不得志,命运犹如生前缄默无闻的卡夫卡那样寂寞悲惨;经济上,他与历史上许多天才作家一样,常常陷入捉襟见肘的田地;精神上,他在晚年不幸患上精神分裂症,悲惨遭遇一如德语墨客荷尔德林。然而,他的作品笔墨和思想却持续不断地抖擞出巨大的光芒。他不仅受到同时期的著名作家如赫尔曼·黑塞、瓦尔特·本雅明、弗朗茨·卡夫卡、罗伯特·穆齐尔、斯蒂芬·茨威格、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等人的极度欣赏和推崇,而且受到后世作家如J·M·库切、苏珊·桑塔格、W·G·塞巴尔德等人的赞誉和膜拜。个中,奥地利著名作家罗伯特·穆齐尔曾剖析认为:“卡夫卡不过是瓦尔泽人格的一个分外侧面而已。”并且公开夸奖说:“瓦尔泽是当代主义德语文学的开山鼻袓,是二十世纪当代主义文学的象征,是游荡在恶行世纪中的一个轻灵而天赋异禀的灵魂……”(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