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杰
9月26日是大哥去世的忌日。一晃大哥去世已经一周年了,每每想起,其音容笑脸都会浮现在面前,亦勾起我对他的无尽思念。
我们兄妹六人,大哥老大,比我大11岁。我开始有影象的时候,他已是十六七岁的青年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们百口随父亲事情调动从赤峰来到林东。那时我还在妈妈的怀抱里,大哥读小学五年级。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期间,由于孩子多,加之父亲做了胃切除手术长期病休在家,家里生活很是困难。据二哥回顾,他记得那时大哥上学连个像样的书包都没有,找一块包裹布将书本文具包起来系在腰间就上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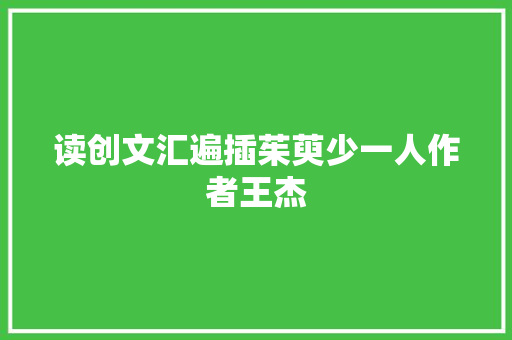
小学毕业后,大哥到王干池一个亲戚家砍柴火。那时家家户户烧火做饭用的燃料不是玉米秸、干牛粪,便是干树枝、树疙瘩。大哥晚上住在亲戚家,白天上山砍柴火,刨了一大堆树疙瘩却没车拉,末了仅弄回来一小部分。事后多年,一提起这事妈妈就心疼,说我儿刨了那么多树疙瘩末了都白受累了!
从王干池回来后,爸爸通过当交通局长的老同学赵戎生,给大哥在汽车客运站候车室找了个做事员事情。大哥发育早,十六七岁已经长得和爸爸一样平常高了。他胸戴红绒布佩章,冬天领口处掖个口罩,两条白线露在表面,每天兴致勃勃地去上班。一进候车室,他便紧张地事情起来,一下子扫地喷水,一下子为乘客排忧解难,一下子安顿和照顾老弱病残。一有发车,他还拿着铁皮喇叭呼唤乘客排队检票,整天忙得不亦乐乎。那时我还没上学,没事就常常到大哥事情的候车室翻看报刊夹里的小人书。一次大哥蹬手推车帮小卖店进糕点,竟把我放到面包箱中间,喷鼻香喷喷的面包馋得我吞咽了一起口水。
大哥喜好画画。我们小时候,他常在自己手指肚上画三国的五虎年夜将,画完便嘴里响着鼓点,一边摆弄一边唱着给我们演他的“指头戏”。
一天天下了雪,候车室的窗玻璃上起了一层白霜。大哥看了上来画兴,便在玻璃上勾勒了一只小老虎,还没等画痕消尽,他又在空缺处顺手写了句“×××万岁”。二者本无关联,却又都是无心之举。没成想这一瞬间情景却被车站一位想表现积极的人看到了。他告发到站领导,且与我家出身不好相联系,末了单位开除了大哥。这件事对我大哥、对我们百口的震撼和打击该有多大,可想而知。
车站做事员的事情没有了,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子总不能呆在家里。于是大哥便和他的小学同学丁国生、丁国明兄弟以及朋友王敬宇、张友等在一起揽一些出苦力的零活干。所谓零活无非是拆屋、抹房、拓坯、砌墙,他们还到郊野树林里拉大锯放木头。丁家兄弟有事情,一个在农场,一个在木器社,五人组合不能持续,末了大哥和王敬宇、张友三人组成了维修“三剑客”,一起打零工干了好几年。下图左侧是大哥,中间是王敬宇。
三人中大哥年事最小,两位老大哥干活时总把最轻巧的活儿让给他干。比如抹房,王敬宇不才面和泥,和好了,用叉子往房上甩;大哥在房顶跑坡,将泥端给张友;张友年纪大有技能,专门卖力抹。三个年轻人,各司其职,合营得珠联璧合,干起活儿来也是有说有笑。特殊王敬宇,不仅长得漂亮,而且爱说爱笑,我们百口人都喜好他。
大哥小时候因被坏人推进枯井受到惊吓,得了口吃。一次三人抹房,王敬宇往房檐上甩泥,一下子甩多了,泥开始往下滑。大哥看到了想提醒王敬宇躲开,可一焦急,嘴上光“哎,哎,哎”地叫,话却嗑吧得一句说不出来,眼瞅着一大堆泥滑下去砸在了还在专一和泥的王敬宇背上。王敬宇疼痛地直起腰,望着房顶的大哥怒气冲天,说你哎哎什么,赶紧说话呀!
这件事过去了四五十年,大哥去西乌旗王敬宇家,在酒桌上王敬宇还给他的女儿们当笑话讲,说这便是我给你们讲的“‘哎哎’叔叔”!
总打零工也非长久之计。既然大哥跟王敬宇、张友学会了泥瓦工,爸爸便托人把大哥安置进了林东镇综合厂维修队。张友后来进了翻砂场,王敬宇则带着寡母去了西乌旗。
这个综合厂维修队是个街道集体企业,统共有七八个泥瓦工,个中一半人不是出身不好便是身有残疾,用现在的话说全是社会草根。维修队的事情,无非给人干些修房抹墙之类的力气活儿,人为挣到就发点儿,很不稳定。也是这时候,大哥和队里的张瘸子、李恒、老聂、小隋等因时常下饭铺儿学会了吸烟饮酒。维修队的劳作非常辛劳,夏天大哥他们常常光膀子在烈日下砌砖抹墙,每天收工都累得腰疼腿酸,躺下就呼呼大睡。妈妈常常心疼地说,我大儿子都被晒成“黑蚰蜒”了。
在维修队挣不到几个钱,大哥就利用空余韶光考试测验着私下找零活儿干。后来索性和维修队达成协议,个人出去单干,每月给维修队缴纳“积累”——实在也便是后来改革开放最初实施的“停薪留职”。
开始大哥小打小闹,不是铺炕搭灶便是接房搭屋,冬天没活儿干时就给武装部马厩铡料草。施工军队由他一个人逐渐扩展到大嫂和正在读书的大姐和二哥,再后来发展到大嫂的二妹张淑华和社会青年张贵发、王武运等,组成了一个灵巧机动的“迷你”施工队。林东的招待所、电影院、戏园子、药材公司、粮油厂等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们费力劳作的汗水。
大哥从没学过承揽工程、绘图和工程核算,更没学过工程设计和施工,统统全凭在维修队已有的施工履历,举一反三,举一反三。大哥设计的厨灶火力旺、不倒烟,和他盘的火炕一样,深受用户的夸奖。
大哥的单干,越干胆子越大,不仅在林东街各个单位干,后来还发展到杨家营子和坝后。那时候来回外地没有便利的交通工具,大哥他们去杨家营子不是找顺风车便是骑自行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去一百多公里远的坝后,他带着几个年轻小伙伴背着干粮和水壶徒步跋山涉水,犹如进行万里长征。
一次大哥从坝后跋涉回来,一起又渴又饿,回到家里便瘫倒在炕头。妈妈心疼地赶紧给他盖上被子问寒问暖,问他想吃什么,大哥怠倦万分地竟说想吃黄瓜!
当时是早春时节,还没有后来的蔬菜大棚,哪里会有黄瓜?妈妈给他端来一碗温开水,说先喝点水吧,妈妈这就出去想法给你买!
后来大哥缓过劲,也不再提黄瓜的事了。
本来说好的“停薪留职”,没想到不久来了场“一打三反运动”,综合厂把大哥召回批斗,说他是黑包工,不但没收了“积累”还对大哥进行了大额罚款。大哥交不上罚款,无奈只好将结婚时找人做的一只栆赤色小桌子拿出去卖了。
大哥对他五个弟弟妹妹非常疼爱。记得我们小时候,他从同学丁国生那借回一台135相机,给我们屋里外边地拍照,还带我们去郊野的小河边。五六十年过去了,当年大哥给我们拍摄的照片成了我们童少年最宝贵的影像。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形势有所好转。赤峰建筑公司来林东招工了,大哥凭借一身建筑技艺被成功召入。在赤峰建筑公司,他从砌砖工开始,没日没夜地苦干,不久便当上了小组长,几年后又当上了施工队长和突击队长,随后又当上了预算科长、经营管理处处长和分公司经理。
1999年企业改制,大哥办理了退休手续。退下后,他也是闲不住,又被一些建筑企业聘去做老总和顾问,发挥了好几年余热。
大哥喜好吸烟饮酒,一辈子养成的习气,想改也改不了。大哥嘴馋,自己爱吃的全都会做。我每次回老家都能吃到他亲自烹饪的扣肉,肥而不腻,柔喷鼻香满口。
大哥喜好拍照和录像,我给他买了摄影机和录像机,不论是到喷鼻香港、深圳、海南、盘锦旅游,还是家庭聚会大事小情,他都端着拍、端着录。爸爸去世三周年的时候,他还专门剪辑并配音了爸爸的纪念专辑放给大家看。专辑拍得生动动听,看了令人热泪盈眶,唏嘘不已。
大哥把自己录制的影像,按内容一盒盒标好,当成家里最宝贵的瑰宝,谁想看了,有借有还。他还把和大嫂到外地旅游的照片放大后挂在墙上,每天面对,对生活的美好瞬间充满了无限的眷恋。
大哥喜好兄弟姐妹大家庭欢聚,每到节假日百口聚在一起的时候他最为高兴。特殊每年春节初二,是他在家里招待百口人的“法定节日”。一过月朔,他便开始做准备。初二这天他亲自下厨,烹炒煎炸,会弄满满一大桌子,而且个个都是大鱼大肉的“硬菜”。看着大家吃得大快朵颐,贰心满意足。妈妈常说,你大哥心疼他弟弟妹妹,有啥好东西非让弟弟妹妹们吃了他才高兴,心情没比的!
大哥喜好读书,各种古典名著、各种演义早就废寝忘食地读过,讲起里面的故事更是滔滔不绝。大哥尤其喜好《三国演义》,讲到诸如“蒋干盗书”之类充满聪慧和哲理的情节张口就来。后来上了年纪,读书改成了听书,不论到哪,手里都哇哇地带着个小收音机。
然而天不假年,三年前大哥溘然被查出肺癌晚期。由于位置不好,无法手术,靶向治疗又配不上型,只好化疗吃中药。
一年多韶光,化疗的副浸染就将他健硕的体魄彻底摧毁,他走路缓慢,吃东西恶心,脸庞急剧瘦削,一让他喝中药眉头就皱起个大疙瘩,表情痛楚不堪。
本来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大哥大嫂倆人关在屋里严防去世守都安全过来了。那成想一欠妥心大哥竟被藤椅绊倒摔成骨折。送到医院又查出得了新冠,于是又赶紧送到呼吸科。呼吸科担心病情恶化转成“大白肺”,又把大哥送进了ICU。一番检讨,一番折腾,等我得到的时候,大哥已报病危。
我急速飞回到ICU探望,这时的大哥浑身插了管子正在与去世神搏斗。我和家人轮流守在病房门口,希望奇迹发生,愿望大哥的病情能有转机。经由一段韶光的治疗,能拔掉管子出ICU了,能自己坐起来看电视了,能坐着轮椅到走廊转悠了……统统好似在奇迹般地好转。然而,就在大家还没欣喜完,大哥的病情却又溘然恶化了!
一次二哥去病房探望。大哥问他“……杰呢?”二嫂名叫宝力杰,二哥说:“你问宝力杰么?她本日有事去她妈家了……”还没等二哥说完,大哥头一扭不理他了。我当时正在美国加拿大旅游,以为返国后再去看他还来得及,哪想到病情发展得这么快!
事后我得知这一情节,心里十分懊悔——在大哥末了的日子里,他最想见到我,而我却没在他身边!
大哥躺在病床上,或许是预感到自己快弗成了,他溘然对身边的二哥说:“给我穿衣服吧,我要找妈去!
”妈妈在一年前刚刚离我们而去。大哥能做如此想,对他来说或许多少会减轻一些内心的恐怖——离开这个天下,还有一个妈妈的天下在等着他!
我亲爱的老大哥,被病痛折磨了两三年,终极还是走了!
姐姐以前曾念叨,说父母不在了,我们六个兄弟姐妹要好好保重自己,未来生活一个都不能少!
如今大哥已先我们而去,且天高气爽又一年。我想起了唐代墨客王维的诗:“独在异域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遍插茱萸登高短缺的不是我这个游子,而是我们兄弟姐妹最亲爱的老大哥。思之,悲痛的心情无以言说。
大哥已登天国,没准此刻正在和爸爸妈妈及我们的两个小姐姐欢聚在一起。愿他们亲亲热热无病无灾,保佑着我们和所有的家人安然幸福!
【作者简介】王杰,1959年生,1979年就读于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后在鲁迅美术学院、辽宁省新闻出版局、辽宁公民出版社、新华社喷鼻香港分社、中心公民政府驻喷鼻香港特殊行政区联结办公室、喷鼻香港商报和深圳报业集团从事专业和管理事情。
从事出版事情前后20余年,策划责编的图书有二十余种获省部级以上精良图书奖,个中《邓小平设计中国改革开放实录》荣获1996年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精良图书一等奖,《爱向汶川——深圳人震区接济日记》荣获第三届“中华精良出版物”特殊奖。
在派驻新华社喷鼻香港分社期间,曾荣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中心迎回归宣扬领导小组颁发的名誉证书。
主编过图书《天下体育趣闻》《院士的青少年时期》,揭橥过各种文章五百余篇,出版过散文集《三情集》《乡愁,抹不掉的影象》等作品,系报纸专栏作家和深圳市委宣扬部出版物审读专家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