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韶光。
诗歌中的韶光是夏日中午,韶光的选取匠心独运。墨客特意忽略了春耕秋收的环节,只管春耕秋收才是我们对农业生产活动更为熟习的认知。
那为什么要选取夏日中午呢?
由于夏日中午在一年四季之中最是酷热,此时锄禾也最是辛劳,带给读者的冲击力就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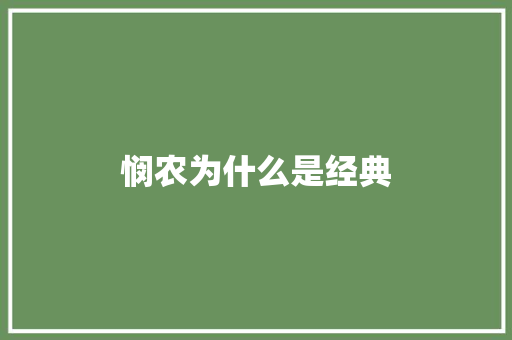
有人说夏日除草是由于这个时候草去世的快,这种读法显然不是在读诗,由于诗歌从来跟实用代价没有关系,诗歌是审美的是抒怀的,跟理智是冤家敌人。
如果用实用代价来衡量诗歌,“冬雷震震夏雨雪乃敢与君绝”岂不是扯淡?“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岂不是弱智?“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岂不是神经错乱?
第二,“汗滴禾下土”的“滴”字。 诗中说的是“汗滴禾下土”,不是“汗落禾下土”,也不是“汗流禾下土”,还不是“汗垂禾下土”,为什么不用“落”不用“流”不用“垂”偏偏要用这个“滴”字呢?首先是由于这个“滴”字表现汗水的颗粒状的液体最贴切最形象。
如果用“落”,那么液体可以落,固体也可以落,而汗水是椭圆状的,滴才是它的常态。
其余无论是“落”还是“流”亦或是“垂”都表达不出汗水那种周详繁多的觉得,而正是这种周详繁多的汗水表达出了夏日锄禾的艰辛感,让人以为当个农人真是他妈的辛劳。
有人会问用“流”那岂不是更好?“流”字表示汗水的量大岂不是更能表现农人稼穑困难?
关键在于下面有一句“粒粒皆辛劳”,这个“粒粒”既可以理解成汗水又可以理解成是粮食,也便是说,这两句特意建立一种这样的遐想:一滴滴汗水点到土里,变成了一粒粒的粮食。用滴字很通畅的建立起来汗水和粮食的联系,由汗水想起粮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用“流”字就不能建立起汗水和粮食的顺畅遐想,因此用“滴”不用“流”。
第三,句式的问题。
末了一句“谁知盘中餐”读起来平平无奇,但妙用非凡。
试问如果这一句改成“须知盘中餐”,读来给人什么感想熏染?“须知盘中餐”给人的是说教感,而那种满口大道理的说教总是让人难以接管的,这就让农人艰辛这一主题大打折扣。
前三句都是陈述句式,而疑问句式带来情绪上的变革,整首诗就有了情绪上的弯曲,要有韵味的多,由于绝句这种题材它善于的便是表现情绪上的奇妙变革。 这种句式在唐诗里不是有时的,比如白居易“谁知尽日卧”“谁知到晓啼”“谁知临老相逢日”钱起“谁知古石上”张继“谁知颂德山头石”杜甫“谁知酒熟喷鼻香”孟浩然“谁知鸾凤声”张籍“谁知余寂寞”等等,都是用的这个句式。
绝句之中,凡是第三句或第四句利用疑问句或否定句的大多都是好诗。
绝句的魅力或在是焉,汉语的魅力或在是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