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的焦点在于:她将《悯农》中的“锄禾”理解为“播种庄稼”,将《春夜喜雨》带来的觉得描述成是“四川人吃火锅”,又在解读《乌衣巷》的时候说“燕子”象征着社会的变革,它来到百姓的“变革之家”。
实在,仔细看了一下她在节目中的原台词,创造她对“锄禾”的阐明比较笼统,谈不上缺点。而她在对《春夜喜雨》的解读,前面基本是精确的,只是末了用了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而已;在《乌衣巷》的解读中,也是末了涌现了问题。她站在一个当代人的态度误读了刘禹锡,以是跑偏了。
蒙曼的专业是历史学,解读诗词只是业余水平。她对这三首诗的理解,没有出错的部分,基本上是照本宣科,远远够不上“大师”水平。
一、从语境来看,蒙曼对《悯农》不存在误读有人曾经说过,让现在的中国人去看古文,有时候和看外语差不多。不信你看一看《楚辞》和《诗经》的各种译本,口语翻译的内容差别之大,切实其实让人无语凝噎。而这些,还都是北大、复旦专家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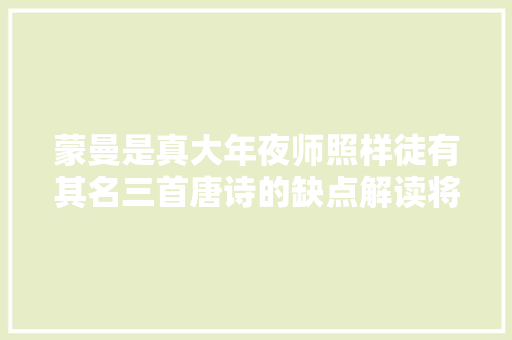
当代人读唐诗实在也是一样。虽然它们多数是古代口语写成,但是不知道创作背景,不知道诗中引用典故,读起来总是让人一头雾水。
蒙曼在一档节目中向一个城市里的小孩子阐明:《悯农》中描写的是古代农人在种庄稼的场景。于是有人指了出来:锄禾不是“播种”,而是除杂草。就有人责怪蒙曼没水平,是个“假大师”。这一点我是不认同的。
虽然我也不知道蒙曼是否明确“锄禾”的本意,但是蒙曼在提到的“种庄稼”这个词组,是有“语境”的。汉语语汇在不同的语境下,意义大不相同。
在节目中,主持人拿了一幅古代《耕织图》让一个女学生作解读。节目组用了三个备选答案,让女孩子挑选一个。个中一个答案便是“锄禾日当午”,结果女孩子不假思虑地挑选了这个答案。
由于《耕织图》表现的是农人收成的环境,以是蒙曼才会对这个女孩子说:《悯农》不是讲“收庄稼”,而是“种庄稼”。
蒙曼实在并没有对《悯民》全诗展开解读,从语境去理解,蒙曼所谓的“种庄稼”不能大略地理解成是播种”,而是指播种、除草、施肥的全过程。以是,因此而批评蒙曼,有一点儿上纲上线。
二、一个缺点的比例和一个跑偏的理解蒙曼针对《春夜喜雨》的解读,从她讲课的内容来看,基本上便是上辞版《唐宋诗鉴赏辞典》里面专家解读的内容。包括喜雨是若何表达喜悦的心情,下雨的韶光是有多么地长,末了墨客又是若何产生遐想。只是当中掺入了很多“口水话”,听起来比较像给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讲课。
不过蒙曼在电视节目中对这首诗的解读,还是有一个亮点。蒙曼认为杜甫是一个“公民墨客”,因此他见到下雨,遐想到的是雨水滋润津润万物,他替天下人而欢畅。
清朝期间,有一个孔姓墨客也作过同样的表达,他在诗中写道:“为惜行路难,为汝老农喜”。意思是说:我不介意由于下雨导致我旅途困难,我只为田间的老农感到欣喜,这是由于:这一场春雨会滋养田里的禾苗。
中唐墨客李约在《不雅观祈雨》这首诗中,对下雨则产生了另一种遐想,那便是:豪门几处看歌舞,犹恐春阴咽管弦。老农爱下雨,盼下雨,是由于他们要种庄稼。有钱人才不在乎,他们只会担心下起了大雨,丝竹声就没有那么清亮动听了。
蒙曼对《春夜喜雨》的解读整体上是无误的,基本上算是照本宣科,坏就坏在她末了打了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末了提到了写四川,写火锅,这和前面讲的写春雨完备不搭调,只是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她的审美水平。
末了,蒙曼《乌衣巷》对这一首古诗的解读,在前两句上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包括句子中的“乌衣巷”对“朱鹊桥”,“夕阳斜”对“野草花”的对仗工致,以及“野草花”的“花”是当动词,理解成着花。诗的头两句有“一石三鸟”的效果,这些基本上是辞典中原封不动的说法。
但是在末了,她特殊强调了野草着花的美,与燕子飞入平常家的欢畅。她说“燕子”象征着和美的家,象征着“变革的家”和“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这种解读就过分了。
刘禹锡的这一首诗,写的是旧时豪门随着人事的变迁而泯没的过程。作为一个古人,刘禹锡的大脑里会有“社会变革”与“变革”的意识吗?刘禹锡对付“乌衣巷”易主,明显是叹惜多于光彩的。如果强调燕子带来的“变革”与新气候,意思明显就跑偏了。
结语只管对诗词的解读是很个人化的,但是我们通过蒙曼对三首唐诗的中后两首的解读,基本上可以判断:她诗词解读的水平,属于“照本宣科”(拜会上辞版《唐宋诗鉴赏辞典》)。而她额外添加的那些内容,还是有一些小问题的。
那么,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水平呢?个人认为,她在某音频和某电视节目中表现出来的水平,勉强能算是普通小学语文老师的水平。同“大师”的水平相较,差不多是一个地球到冥王星的间隔。
但是一部分网友对蒙曼的解读,也存在恶意扭曲和放大的方向。例如蒙曼对《悯农》的解读,大家忽略了她讲话的“语境”。
《春夜雨树》的问题,紧张暴露了她“脱口秀”的真实水平。说得多,错得多。她前面背诵上辞版专家解读原文就很好,后面没必要再去多此一举。结果误用了的“四川红油”,烫着了“自己的皮肤”。
《乌衣巷》则进一步显示出,她有一点抓不住重点。她便是个历史专家,不太懂古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