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留白叙事”,使人物保持着现实繁芜性和天然性,通报了作者的真切体验,同时作为弹性的审美空间,引发读者深入思考,使作品形成了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
一、《莺莺传》作者及其文化环境
唐传奇写作以虚构为主,可以说是为了故事好看而着意编造。《莺莺传》却是基于元稹的亲自经历,并非纯粹虚构的故事。
宋代赵令畤《侯鲭录》引王铚《传奇辨正》说道:“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
王铚自称家藏元稹《元氏古艳诗》百余篇,中有《春词》二首,其间皆隐“莺”字;元稹的《莺莺诗》《离思诗》《杂忆诗》,与《莺莺传》所写情景,一模一样。王铚又指出元稹的《古断交词》《梦游春》诗,前面阐述相遇,后面谈为义而舍情,与《莺莺传》意旨相同,而且元稹诗中多以“双文”称呼抒怀工具,“莺莺”的名字为两字重叠,即为双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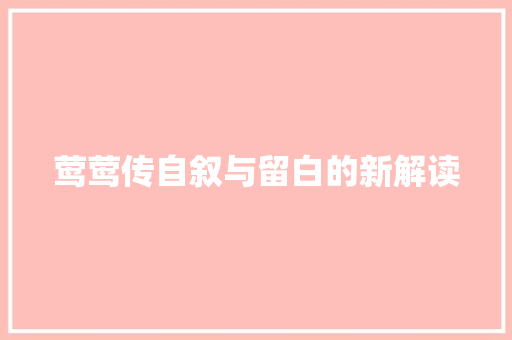
王铚的考证还是颇有说服力的,这诸多证据可解释元稹便是张生的原型。元稹出身士族河南元氏,元氏为北魏皇族拓跋氏的汉化姓氏。他的母亲出身荥阳郑氏,是唐代最显著的门第“五姓七家”之一。元稹第一任妻子韦丛,是太子来宾韦夏卿之女,属京兆韦氏;第二任妻子裴柔之,属河东裴氏。元稹父母及其本人的婚姻,完备符合唐代士大夫门当户对的结婚原则。
唐代是门阀制度的尾声阶段,全体社会依然重视门第,士族彼此通婚,也努力与更高的门第结亲,乃至瞧不上皇族。以至于唐文宗大发牢骚,实在,二百年天子算什么,门阀制度从汉朝发展到唐朝,高门士族哪个不是绵延了几百年?
“妻者,齐也。”妻子与丈夫齐等匹配,地位主要。对付大家族来说,妻子的职责是传家事、承敬拜、教养子女,与家族的延续和兴盛密切干系。唐代的墓志铭,凡是为某某夫人撰写的,都是赞赏她贤德、端庄,有相夫教子的光辉业绩。
而唐代那些缠绵悱恻、艳情入骨的诗句都不是写给妻子的。士大夫家庭对女儿的教诲,便是把她们培养成社会所须要的妻子和母亲。《礼记·曲礼》《礼记·内则》等记载了各种行为规范,严格限定女子与外界的联系。女子到了得当的年事,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挑选好的夫婿,在另一个家族连续相同阶层、相同代价不雅观的生活。
在这种大环境中,正常发展的青年文人险些见不到门当户对的未婚女子,更谈不上交往。因此,爱情故事的主角多为拘束较少的青楼妓女,乃至妖怪鬼狐。唐传奇中还有一类表兄妹恋爱故事,如《离魂记》《无双传》等,是一方家庭遭遇不幸,从小寄养在另一方家里,乃青梅竹马的关系,这种情形在现实中并不多见。
二、《莺莺传》之叙事留白
《莺莺传》却开展了一段不屈常的自由恋爱,其常规之内和冲破常规的各类成分,都相称耐人寻味。青春年少,两性吸引,乃人性之常态。可是按照道德规范和礼法,莺莺和张生根本没机会自由交往,社会规范约束人的本能,生活空间杜绝来往,这是当时社会之常态。此故事发生在寺庙里,却打破了世俗社会的空间限定,为主人公的相识相悦供应了机会。
唐代寺庙具有旅店的功能。如柳宗元被贬永州,就带着母亲居住在龙兴寺。韦应物在仕宦的间隙,多次寓居寺庙,先后住过洛阳同德寺、长安善福精舍、苏州永定寺等。《莺莺传》中,崔夫人郑氏携子女,带着家财奴隶,长期住在寺庙里,只管与官员情形不同,但是图个节约、方便该当是一样的。
应举的读书人如张生,借住寺庙也很常见。大家同时住在寺庙中,崔莺莺的母亲郑氏和张生先行认识,并叙了亲戚关系。张生的母亲姓郑,故张生称呼郑氏为姨母,莺莺和张生可以算是无血缘关系的表兄妹。只不过,莺莺作为闺中女儿,和陌生表兄张生的活动也是隔绝的。
偏巧此时发生了兵变哗乱,波及寺中人的安危,张生出面请朋友解除危难,惠及寺中老小。郑氏设宴感谢张生这个外甥,给莺莺和张生创造了见面的机会。倘若没有前面的认亲,估计郑氏也不会非让女儿出面。作为才子佳人小说的奠基之作,《莺莺传》对男女主角的描写非常符合大众生理,才子有貌,佳人亦有才。
张生“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如此品貌,却不是随随便便的人,“是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
张生对莺莺一见钟情,也可以说是见色起意。他私下里贿赂莺莺的侍婢红娘,希望她能通报。他第一次表明意图时,“婢果惊沮,腆然而奔”,红娘直接吓跑了。第二天,红娘又来了,张生羞愧道歉,不敢再说什么。谁知道红娘彷佛认可了张生,问他为什么不请媒人求娶。
张生说他一见莺莺就爱得无法自持,纳采问名之类的全套求娶程序韶光太长了,自己等不及。红娘信了,出人意料地支了大招,说莺莺沉吟章句,让张生写情诗攻心。张生大喜,急速写了《春词》二首交给红娘。当天晚上,红娘就带着莺莺的回答来了,是一首诗《明月三五夜》,聪明的张生急速参透了诗谜。
仲春十五日的夜里,张生攀援着大杏树翻过墙头,来到莺莺居住的西厢,创造门是半开的,红娘正睡着。红娘被张生惊醒后,非常吃惊。这个细节解释红娘根本不知道莺莺给张生的诗笺写了什么,以是她半夜溘然看到张生,才会如此惊异,这个细节也同时解释,约请张生翻墙来约会,完备是莺莺自己的主见,没有任何人鞭策她。
此时的张生,既狂喜又害怕。喜的是机会在前,必能亲近佳人;害怕则是恋爱心情的患得患失落,以及对冲破交往禁忌的担心。
莺莺“端服严容”涌现,可见她在郑重等待张生前来,然后把张生训斥了一通。她的这番话有理有节,层次分明,并且阐明了自己的行为:张生于崔家有恩,郑氏感激,让弱子幼女相见,是把张生当作自家人来请托;张生居然让奴婢通报淫逸春词,意图掠乱,其行为与盗贼无异。
作为当事人的莺莺,如果对此默不作声,相称于粉饰了张生的奸行,是不义的;如果报告给母亲,又出卖了张生,违背了他原来的恩典,是不祥的;如果让奴婢转达这些意思,担心传话有误,歪曲了意思;如果亲自写信解释,又担心张生理解不透,仍有难堪。
左思右想,莺莺故意用“鄙靡之词”,也便是不高雅、违背礼仪、有损形象的情诗,把张生勾引过来,当面骂他,希望今后“以礼自持,无及于乱”!
张生被训懵了,昏昏然翻墙回去,从此绝望。如果就这样罢了,《莺莺传》也就全篇闭幕,没有往后了。
可是,仅仅三天之后,仲春十八日的夜里,已经心灰意冷的张生正在睡觉,忽然被红娘惊醒。红娘抱着被褥枕头,铺在张生的床上,又扶着莺莺进来。
此时的莺莺“娇羞融冶,力不能运支体,曩时端庄,不复同矣”。
张生大喜过望,得偿所愿。天快亮时,红娘又把莺莺带走。从手臂、枕席上的残妆喷鼻香气等各种痕迹,张生知道这真的不是做梦。一夕幽会后,持续十几天,张生没有莺莺的任何,他忍不住写了《会真诗》三十韵,交由红娘转达给莺莺。
莺莺收到情诗后,两人又开始偷偷约会,同居长达一个月。其后,张生离开此地去长安,数月之后返回,还像以前那样和莺莺幽会同宿于西厢,持续好几个月。接着,张生“文调及期”,前往京城应考。分别后,两人还有书信往还。张生留在长安,中断了联系,两人各自婚嫁。后来,张生以表兄身份求见婚后的莺莺,莺莺谢绝相见。这段恋爱故事就彻底闭幕了。
三、从读者角度看叙事留白解答前述谜点的过程,相称于为叙事留白点染读者色彩的过程,每个读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补充叙事留白。红娘是莺莺的贴身婢女,在古代,这种身份的婢女一样平常都会陪同小姐出嫁,然后再成为姑爷的通房丫鬟或者侍妾。
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和平儿,平儿便是王熙凤的陪嫁丫鬟,王熙凤的丈夫贾琏也是平儿的丈夫。红娘看张生,实在也是在看自己未来的归宿。她该当是对张生很满意,才主动支招,意图撮合张生与莺莺。
元曲《西厢记》就谙熟这层意思,让张生对红娘直截了当地说出:“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
莺莺是如何对待张生呢?第一次家宴上见面,她根本不在意张生,顶多便是看了一眼大致长相。是张生的《春词》起到了推动浸染,两人的关系发展也可描述成“诗为良媒”。张生的诗句一定打动了莺莺,否则她接到《春词》直接丢开,或干脆奉告母亲,一定能把张生的动机断干净。
她不仅没这样做,还主动写了约会的诗句,引得张生翻墙前来。张生的举动,助长了莺莺的自傲,她可能第一次体会到恋爱对别人的巨大影响力。当她端起面孔,教训了张生一番时,张生没有任何辩白,乖乖地听她训话,又乖乖地原路翻墙返回。这种呆痴的举动,进一步助长了莺莺的自傲,也提升了她对张生的好感度。
张生俊秀有才,该当是莺莺在有限的活动范围内打仗到的最出色的青年。他所表现出的激情亲切爱恋,一定程度上知足了闺中少女的虚荣心,使得少女对爱情的憧憬第一次有了实际的寄托。张生痴情、乖巧,又给了莺莺安全感,使她放心去考试测验未知的恋爱的甜蜜。
这次翻墙训话,加深了莺莺对张生的认识,也让她看清了自己的内心。张生思慕莺莺,不想等待,不想错过。莺莺也同样不想错过张生。因此,训斥张生之后才短短三天,她就自荐枕席,何尝不是害怕张生真的就此放手,两人再也无缘?这便是才子佳人的真意,确定般配,彼此有情,谁都不想错过对方。再对照文章特意强调的两人性格特点“坚孤”“贞慎”,更能证明这一点。
郑氏的态度,文中写得非常模糊。郑氏只有一子一女,外加一些奴隶,按理说不会对莺莺疏于看顾。在闺范严格的唐代,女儿长达几个月与人同居,做母亲的居然什么都不知道,也是说不过去的。张生曾讯问莺莺郑氏有什么意见,莺莺的回答是:“我无可奈何矣。”也便是说,她不能旁边母亲的见地。莺莺由于离去而悲泣的时候,奔向母亲处寻求安慰,可推知郑氏应该知道莺莺和张生的关系。
几个月的同居,连郑氏都暗中许可,为什么没能走向婚姻,把这份关系巩固住呢?最可能的缘故原由是莺莺、张生有门第身份上的差异。如前所述,唐人结婚最重门第,莺莺的母亲显然对此无能为力。唐代博陵崔氏、清河崔氏都是顶级高门。
倘若莺莺出身这两个崔氏,求婚者也会踏破门槛。但是,文中只说崔家资财丰硕,多奴隶,别无信息。张生并未努力匆匆成婚姻,从他的态度推测,莺莺的家庭并非良配。崔姓只是作者元稹行文时的假托,与现实中的士族崔氏没有关系。
结语就像现实中的元稹本人,虽然婚配高门,早期的恋爱却成为萦绕不去的幻梦,为之迷离终生。“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离思》),他在追忆回味中写下了一首首诗,还有这篇惊才绝艳的传奇。
《莺莺传》是经得起一读再读的经典文本,可以超过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不雅观念,而无损其审美的、道德的代价,其人物性情的深度更是超越了后代的各种改编版本。
参考文献《莺莺传》
《中国古代戏剧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