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心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 孙媛媛
音乐是人类抒发情绪最直接的表达办法之一,是国际公认的“天下措辞”。作为音乐主要组成部分的声乐艺术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每每有“先行后知”规律和特色,我国文籍对此多有论及,比如《毛诗序大序》载:“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敷,故太息之,太息之不敷,故咏歌之,咏歌之不敷,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从发展历史过程看,中西方声乐艺术虽然各有特点和上风,但在发声演习和审美追求等方面实在是相通的,完备可以相互借鉴、互补生辉,共同为当代天下声乐艺术繁荣发展作出贡献。伴随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和我国声乐艺术的快速进步,目前中西声乐艺术已经超越了“土”“洋”之争,相互认可却又更加看重回归本源、各美其美,交融贯通、中西合璧、美美与共已经成为我国声乐艺术界的广泛共识和进一步探索的时期课题,中国声乐艺术迎来了一个崭新发展阶段。本文将结合笔者的传授教化体会和艺术实践,就中西声乐艺术融通的紧张方面进行磋商,并就如何用泰西美声唱法演绎好中国作品提出一些粗浅的意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
“美声”不仅是一种发声或歌唱方法,同时也是一种歌唱风格和流派。当代美声唱法起源于16世纪末的意大利佛罗伦萨,17、18世纪在全天下特殊是欧洲遍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往后,西方当代美声唱法传入中国,我们习气称之为泰西美声唱法。百年来,中国声乐艺术发展经历了从“以洋为尊”“洋为中用”“土洋之争”到“美声唱法民族化”“民族唱法美声化”,再到以我为主、“土”“洋”互鉴,致力于建立中国声乐的理论体系和艺术演习体系这样一个繁芜弯曲的历史过程。经由大量的艺术实践的考验,泰西美声唱法科学的声部划分、发声方法、演唱办法、声乐理论、传授教化方法和雅俗共赏的审美取向,终极赢得了中国声乐从业者和广大不雅观众的青睐。目前,在中国专业音乐院校的声乐传授教化和文艺演出团体的声乐演出中,大多都因此美声唱法作为发声根本事理进行传授教化和演唱的。以中国传统唱法为主的声乐教诲机构和单位中,不少西席在保持民族声乐艺术精良传统的同时,也大胆借鉴包括泰西美声唱法在内的其他各国声乐艺术的科学发声方法,大大拓宽了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发展道路,取得了丰硕成果,受到各方的关注和赞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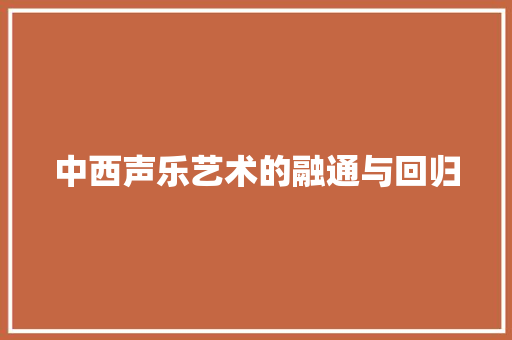
从发展规律看,声乐艺术都因此身体为乐器的歌唱艺术,各国各民族人们的嗓音干系的身体构造大同小异,中西声乐艺术在演唱的共性上该当是相通的,都希望达到发声自然、音色统一、音域宽广、措辞清晰、歌唱寿命长等艺术目标和空想。和很多其他舞台演出艺术一样,声乐艺术的演唱技能传承和发展仍紧张依赖示范与模拟等口传心授的个体办法进行,其根本要素紧张包括:良好的呼吸支持;清晰的吐字归音;统一的声区状态;顺畅的起落音连贯;合理的音量掌握;幽美的音质呈现和灵巧的个体演绎等。归结起来,中西声乐艺术融通的基本条件紧张表示在以下三个方面:
良好的呼吸支持和气息掌握
呼吸是发声的原动力。呼吸是歌唱中的杠杆,也是歌者全面调度发音及歌唱状态的动力源泉。建立良好的呼吸支持状态是每一位歌者在学习和演习中的必修课,是担保和提高歌唱能力的根基。中外很多歌唱家、声乐教诲家对呼吸在歌唱中的主要性都做了很多精辟的论述。我国古代就有“气为声之帅”“气为声发,声靠气传,无气不发声,发声必用气”“善歌者,必先调其气”等名言金句。当代老一辈声乐专家常说,“在气息支持下歌唱”“用气息托住声音”“懂得良好地呼吸,就会很好地歌唱”“声音坐在气上”等,这些关于节制呼吸支持状态办法的语句,看似朴实无华,却蕴含了深刻的道理。我国著名歌唱家、声乐教诲家沈湘教授认为,“要使声音有生命力,就要有呼吸的支持。呼吸是歌唱的动力,是歌唱的支持力。”“歌唱艺术便是呼吸的艺术,由于歌唱中所有的变革都来自呼吸的支持。”意大利著名歌唱家卡鲁索也认为,“只有正常的呼吸,才能给予产生准确音高所需的准确频率,也才能有正常的音量、响亮度和音质。”声乐传授教化中所说的呼吸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生理性呼吸是有差异的,歌唱演习中,初学者常常会对呼吸觉得和生理呼吸直觉产生抵牾和错觉。歌唱中的呼吸是随着乐句的是非、根据感情情绪的变革而变换着利用的呼吸,属于故意识、有目的、有技巧的呼吸。在现今我国专业声乐传授教化中,很多老师不再纯挚倚重学生天生的好嗓子,而是越来越看重用生理学来阐明和讲授呼吸的详细演习方法,大多会用启示式的措辞和比拟、暗示等手腕来启示学生们的想象力,把繁芜抽象的呼吸感想熏染直不雅观化、生活化,调动学生自己对身体呼吸的感知,从而达到对呼吸支持状态更切身的领悟。因材施教是教诲中的一个根本原则,这一点在声乐传授教化中表现得更为严格。由于歌者个体的客不雅观差异性,老师会根据学生的不同身体构造和理解力,进行科学确定声部等有针对性的传授教化。笔者在传授教化中创造,学生在初期学习阶段对付呼吸支持随意马虎涌现认知错觉,大多片面地强调身体的局部,乃至过于把把稳力放在身体的某些或者某个位置的调度而导致整体呼吸状态失落衡,涌现声音稳定性差等弊端。对呼吸的精确认知和科学调度是声乐传授教化中的重点和难点,须要永劫光的履历积累,既磨练老师的辨识能力,也磨练学生的领悟能力。
中西方声乐艺术风格和表现手腕虽有差异,但对歌者呼吸的哀求却是大致相通的,那便是通过横膈膜起浸染保持稳定气流和气息的对抗平衡。声乐传授教化中常讲的呼吸和气息实质上是同等的。从生理学角度讲,呼吸或者说气息是坚持生命的一种内在的身体性能;从生理学角度讲,歌唱所说的气息之“气”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意念上的支持。无论是从事音乐传授教化的专家还是从事演唱的歌手,不管对呼吸的理解不雅观点有多不同,却都有一个基本共识,那便是借助自然的呼吸状态,保持喉部稳定,后咽壁特立积极,喉咽通道顺畅,使其形成良好的歌唱共鸣。这样声音才不会受音乐的高低、强弱和旋律变革影响,始终保持如挺立的建筑形象一样的稳定状态。中外演唱者在发声时都须要头腔共鸣和横膈膜的支持,须要喉部的打开和喉头的稳定,同时还须要用良好的呼吸状态掌握音色变革。不同的声乐作品对演唱者的呼吸处理要有不同的哀求,须要演唱者依据作品调度呼吸的深度、张力、灵巧性和穿透力,使声音的表现力更丰富。从身体力学角度看,呼吸的气压、气流以及宇量之间的关系是:气压大小决定歌唱的音高,气流的快慢决定了音乐的戏剧性和抒怀性,宇量的多少决定了音量的大小。在这些条件的综合哀求下,歌唱中的“气口”如何正常利用,如何能够平稳、更深地“换气”,在多音阶多小节的长乐句中如何能够在演唱中不易被人察觉地“偷气”,这些技巧和方法须要歌者在不断演习和舞台实践探索中学习积累。以是,演习和保持良好的呼吸支持和气息掌握是中外歌唱家生平都须要修炼的基本功。
清晰的措辞表达和吐字归音
歌唱是一种分外的措辞表达办法。中外声乐界对歌唱措辞表达的清晰度哀求都很高。宋代张炎(1248-1320)曾在《词源》中写道:“曲有三绝,字清为一绝。”明代魏良辅(1489-1566)在《曲律》第十二中提到,“曲有三绝,字清为一绝,腔纯为二绝,板正为三绝”。我国著名声乐教诲家喻宜萱教授就认为:“歌唱是措辞的升华,音乐与措辞的有机结合,是歌唱艺术的基本特点,必须重视措辞的演习。”国外不少著名歌唱家也有一个共识:“清晰的吐字绝对不会对声音有损,相反会使声音更完美、更集中、更柔和。”绝大多数声乐作品的表现都必须通过措辞笔墨来描述演出者内心的感情活动,舞台上许多细致的、生动的演出也有赖于对笔墨措辞的准确节制。只管由于中西方措辞发音上的差异,演唱对歌者的身体利用以及咬字行腔变革均有不同哀求,但是中西声乐艺术演出中都存在吐字归音的问题。这是中西声乐艺术融通的一大难点。
详细而言,泰西美声唱法提倡咬字清晰和语感、语气的生动准确,但因对声音位置统一连贯和整体共鸣有严格哀求,在字的延长音中每每随意马虎将演唱时的把稳力转移到声音共鸣位置的保持上,这样就随意马虎表现为模糊和弱化字的歌唱状态。我国传统歌唱的美学理念因此字行腔、字领腔行,讲究字正腔圆。因此,我们在练习中国作品唱法时,习惯用一个元音字在无论连贯的行腔或用休止或气口断开的拖腔中,多次借助口腔和身体摆位变革形成元音的状态,从而在保持声音的平稳、均匀、放松、位置统一的同时,又能唱出字与旋律的和谐统一,不失落措辞和旋律风格,凸显民族旋律行腔的风格和艺术美感。歌者在演唱中国作品时强调依字行腔、字字清晰,而在演唱泰西作品时更强调把每一个音节里的元音唱清晰。欧洲的措辞虽然一样平常都由母音(亦称元音)和子音(亦称辅音)组成,没有汉语那样繁芜的归韵,但在发音上各有特点、力求顺畅清晰。比如,意大利语被称为“歌唱的措辞”,其紧张缘故原由是意大利语发音相比拟较大略明确,只有五个元音,即[a][e][i][o][u]。而在艺术实践中,歌者在用意大利语歌唱时,除常用的五个元音外,还增加了[Φ][ü]以及[ai][au]等二重元音、三重元音的变革,语音爆裂子音多,歌唱时喉音有时会更有冲击力。再比如,法语有着浓重的鼻音,十五个元音和三个半元音的变革使法语的发音变得更为繁芜,歌唱难度更高。而英语的吐字发音位置较低,用英语歌唱时要把声音送到高位置上对付歌者而言也须要作相应调度。正由于不同的措辞发音有其自身措辞的语腔调整、语势、语意、语气以及语法上的发音特点,针对不同措辞自身的发音色彩和节奏韵律,歌者须要折衷不同的神经和肌肉以及发音部位予以处理,但目的只有一个,那便是让歌唱中的措辞清晰明确且带有音乐美感。
中文或者说汉语的发音虽与欧洲措辞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中文有相对独立的措辞体系,其发音具有光鲜的多民族特色和地域方言的繁芜性。汉语多以单音组成,一字一音一意,每个字分为字头、字腹和字尾,根据字的尾声不同又分为十三辙,且有四声的变革。汉语四声腔调变革是长期的文化传承中故意识追求抑扬抑扬、幽美悦耳的措辞效应的结果。除四声外,汉语演唱吐字哀求“五音(唇音、舌音、齿音、牙音和喉音)”配“四呼(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中国戏曲演唱则在这方面最为清晰和讲究,戏曲演员只要准确地节制五音的位置,再合营“四呼”的利用,即能做到吐字准确,就被称为“五音完好”“四呼到位”,才可能达到“出字千钧中,听者自动容”的艺术效果。这里说的“五音”和许多非专业人士称自己“五音不全(常日理解为唱歌音不准)”是有很大差异的。这些中国作品的吐字归音办法和规律都须要美声唱法歌者在平时的演习中悉心领会,并在歌唱实践中加以创造性的利用,才能让中国传统唱法和泰西美声唱法有机结合,真正做到让美妙的声音为幽美的作品做事。
在我国,不少能够演唱好泰西音乐作品的歌者感到要高水平完成中国作品的演唱存在较大困难,个中最紧张的症结在于吐字不足清晰准确。造成这种征象的一个客不雅观缘故原由是中国歌唱习气和方法上与泰西歌唱方法之间存在一定理念上的冲突,须要在日常演习中加以科学调和。泰西美声演唱对字的起音哀求是轻松、自然、通亮、准确、圆润,即在歌唱时看重“软起”,以保持声音的弹性和持久力,反之“硬起”则易损耗歌唱能量和音色音质。美声唱法起音准确与否会直接影响到声音位置、声区的统一和呼吸状态的保持。而汉语中的四声、五音以及韵辙上的变革,须要演唱者调度自身的吐字习气。在演唱演习中,虽然我们常说歌唱时吐字要像说话那样清晰、亲切,但如果真用说话时的状态发声、吐字去歌唱,就会涌现“有字无声”的征象,而实际上歌唱发声是“像说话”而非“真说话”,须要结合自身嗓音条件加以领会。不少中国声乐作品在创作过程时刻意加入一些民族文化和戏曲音乐元素,因此在四声的根本上加上“儿化音”“尖”“团”音等装饰性较强的语调色彩,有的还根据不同地方或民族的语音特点在行腔特殊是“起音”和“落音”上作分外处理,以增强作品的艺术传染力,这也加大了演唱的精度和难度。
朴拙的舞台演出和情绪表达
精良的音乐作品都蕴含着丰富的情绪。但这种情绪的表达和传播不仅须要我们常常理解词曲作者的艺术创造,同时也须要歌者、指挥、演奏等经由再度创作才能完美呈现给不雅观众。词曲作者是一度创作,他们把自己的情绪转变成笔墨和音符。这些笔墨和音符虽然倾注了词曲作家们的情绪和心血,但作为歌词和乐谱本身是没有生命力的,只有经由演唱、指挥、演奏等的二度创作,注入自己的思想感情并用声音表现出来传达给不雅观众,才能授予音乐作品鲜活饱满的艺术生命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音乐演出也是一种创作,是一项充满创造性的艺术活动,演唱家、演奏家绝不等同于复制音响的机器,他们不仅传达作曲家的声音,而且在作曲家创作成果的根本上进行审美的再创作。以是,在音乐作品的呈现过程中,歌唱、指挥、演奏等演出者的艺术创造力和舞台表现力同样十分主要和不可或缺。正如指挥家卡拉扬所言:“指挥家不但是总谱的实行者,而是授予总谱以生命的人。”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各国公民情绪表达办法有差异,演唱者对作品中“情”的理解不尽相同,他们会通过调度声音表现力去表达不同的艺术情绪。几千年来,中华文化授予了中国人蕴藉、儒雅、温和、清秀、内在的性情。而以欧洲为紧张代表的西方人的情绪表达办法每每更加激情亲切、旷达、爽朗、外在。只管各国和各民族文化特色反响在声乐艺术和代表性演唱者身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中西方声乐界和不雅观众对付歌唱演出者在舞台演出和情绪表达的朴拙程度上的哀求是高度同等的。
作为用人声表现的歌唱艺术,“情”在演出中霸占分外的地位,歌唱者必须把自己融入到音乐中,积极调动情绪动机,借助歌唱的希望和激情亲切,尽力做到朴拙、投入和准确,切忌只知唱声、不知唱情,但注入个人情绪时须要把握好度,既要尽力以“情”传染不雅观众,但也不能过分,用力过猛、过度演出,会毁坏作品本来具有的艺术魅力。一个精良的声乐作品终极是要通过演唱者的声音或者舞台演出与不雅观众见面,达到与不雅观众互换产生共情从而传染不雅观众的目的。我国清代声乐理论家徐大椿在《乐府传声》中对“声”与“情”的关系说得十分通透:“唱曲之法,不但声之宜讲,而得曲之情尤为重……使词虽工妙,而唱者不得其情,则正邪不分,悲喜无别,即声音绝妙,而与词曲相背,不但不能动人,反令听者枯燥乏味矣。”这也是中国传统声乐美学中所倡导的声情并茂原则的表示。演唱者要做到这一点是比较困难的,须要在幕后做很多作业。在歌者演唱之前,词曲作者都授予了声乐作品既定的情绪和内涵。歌词为演唱者供应了文学形象,演唱者要通过对时期背景和歌词内容的研究,初步确立措辞思维层面的音乐形象。歌者再通过理解曲作的创作背景和内容,剖析包括伴奏部分在内的全部曲作确立起旋律意义上的音乐形象。然后,通过对歌词按音乐节奏律动进行准确朗读,歌者将歌词与旋律有机合成。末了,歌者将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情绪融入到词曲创作的整体音乐形象中去,并用声、用情、存心歌唱,尽可能完全地诠释作品丰富的艺术内涵和思想情绪。正如法国音乐家皮埃尔贝尔纳克所说:若何才能担保音乐和歌词的完美统一呢?这个问题歌唱家必须从技巧上去办理,然而最根本的还是从心灵上去办理。
在声乐演唱中,歌剧作为声乐的“皇冠之珠”,是国际声乐艺术互换中的宠儿。它是集音乐、文学、舞蹈、舞台美术等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其演唱难度是最高的,对演唱者的演唱实力和舞台把控能力都是极大的磨练。在这方面,泰西歌剧和中国歌剧(人们习气称民族歌剧)的衡量标准是同等的。歌剧不仅哀求作品整体上有幽美的音乐质感,同时哀求演出者用歌声传达繁芜的人物情绪,借助肢体演出去表达角色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授予角色以鲜活的舞台人物形象。以是,歌剧不仅哀求演出者有踏实的演唱功底,同时还要对台词、舞台演出、身体演习与其他角色间的人物合营,以及与指挥和乐队之间的协作等诸多要素进行综合精准处理。作为最能和泰西歌剧媲美的中国戏曲均属于天下戏剧和音乐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只管二者所呈现出的舞台表现以及演员的演出用力方向都有所不同,在演出上也表示出演员对舞台时空处理的灵巧性程度不同,但中国戏曲和泰西歌剧在艺术综合性特点和人物形象塑造上的追求是基本同等的,都是努力让角色说话、引发不雅观众情绪共鸣。虽然中国戏曲中一些舞台虚拟手腕和演出程式在泰西歌剧中很难见到,但泰西歌剧中的人物也是通过类似中国戏曲不同行当角色的演唱来推进剧情的发展。泰西歌剧通过Recitative(宣叙调)和Aria(咏叹调)以及重唱等形式来抒发人物的内心情绪、塑造艺术形象,实质上和中国戏曲一样,都是用音乐化的人声塑造人物性情和形象,并在经由精心支配的舞台时空中展现出来。随着社会科技发展和审美变革,当代中外歌剧舞台设计不再拘泥于传统,而大多在保持传统歌剧艺术特点的同时,为增强不雅观众的视觉审美感想熏染,增加了声、光、电等当代高科技元素,同样须要歌剧演出者给予合营,这也给演唱者增加了难度。以是,培养一名成熟出色的歌剧演员十分不易。中外专业音乐院校都把歌剧演出能力作为衡量声乐西席水准和学生培养潜力的主要办法。
如前所述,正因中外声乐艺术在实质上是同等的,在技能演习和审美追求上是相通的,当前中国声乐艺术领域中的泰西美声唱法和中国传统唱法在守住本源、回归各自艺术上风与特色的同时,也相互原谅互鉴,基本达到和谐共融的良好局势,我国声乐艺术正朝着交融贯通、中西合璧的方向康健发展。
二
经由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和不懈努力,泰西美声唱法终于在我国生根萌芽、着花结果,日臻成熟、发达发展并与天下接轨,呈现出了黄友葵、喻宜萱、周小燕、蒋英、沈湘、郭淑珍(点击查看《中国文艺评论》名家专访上、下)、黎信昌等一批蜚声中外的著名歌唱家、音乐教诲家,他们为我国美声唱法的教诲体系、理论体系、演唱风格的形成作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也培养了一批精良的歌唱家,他们在国内外声乐舞台上百花竞放、硕果累累,为国家赢得了宝贵名誉和文化肃静,得到了国际声乐界的高度认可和海内不雅观众的普遍欢迎。
唱法本身没有利害高下之分,对歌者而言只有得当与否的问题,毕竟唱法终归是为作品做事的,用作品打动不雅观众是歌唱艺术的硬道理。我国老一辈著名歌唱家、声乐教诲家对此都深有体会。黄友葵教授认为,“作为一个中国的歌唱家,应首先唱好中国歌曲……无论演唱任何中国歌曲,感情、风格、措辞必须是民族的。”喻宜萱教授认为,“对付学习泰西声乐的文艺事情者来说,终极目的还是唱好自己国家的作品,表达中国公民的思想感情。”只假如坚持以人为本、尊重自然规律、讲求科学发声,能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的唱法都是应该提倡和推广的。随着国际文化艺术互换的日益广泛和我国文化强国培植的全力推进,海内国际两个文化环境和艺术市场的多元化需求会更加兴旺,我国声乐艺术要想拥有更多话语权和主动权,就须要进一步冲破唱法藩篱,在发声方法、评价标准、理论体系、学科设置、课程体系、就业走向、创作沟通等方面做出更多考试测验和探索,真正进入交融贯通、中西合璧的良性循环。个中最急迫也是最根本的事情还是用泰西美声唱法演绎好更多精良中国作品特殊是中国传统经典作品,达到中外声乐艺术水准的动态平衡。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以下四个方面值得进一步深入磋商:
一是促进艺术思维和审都雅念的转变。从艺术哲学角度上看,歌唱中最紧张的抵牾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即发声技巧和演唱内容之间的抵牾。毫无疑问演唱内容是抵牾的主导方面,发声技巧要为演唱内容做事,二者的关系不能颠倒。不管什么声乐学派、不管用什么办法发声,声音终极都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作品的审美空想和艺术追求。我们在专业演习中得到的旋律、节奏、节拍、音高、速率、力度、和声、调性、调式等音乐措辞,终极都要通过民族措辞去表达和塑造作品的艺术形象。笔者在艺术实践中创造,一些学习美声唱法的学生或专业从事美声唱法的青年演员还存在着一种片面不雅观念,认为中国人天生就理解自己本民族措辞,只需稍加学习就自然能够唱好中国歌曲,从而在演习中把学习重心更多地放在泰西作品的研究上,而不太重视对中国作品的研讨。这种思维办法和审美认知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此外,一些从业者和不雅观众还片面地认为美声唱法是“唯声论”“唯美论”,实在不然。众所周知,美声学派的创始人佛罗伦萨小组提出的美学原则是“音乐之中,歌词为先,节奏次之,声音居末”。这是美声学派一贯坚信的歌唱原则和理论依据。中国传统演唱也非常看重字、声、腔的高度领悟,各地各民族的方言成分直接影响到其调式、旋律、演唱的发声、吐字以及行腔。美声唱法的歌者要唱好中国歌曲,演唱者既要理解所演唱作品的风格特色,更要充分理解汉语的发音规律和措辞构造特点。正由于中西声乐艺术各有特点和上风,我们在学习演习和舞台实践中,该当同等尊重和对待它们,兼容并蓄、齐头并进,不宜偏废。
二是加深对中国作品民族文化传统和演唱繁芜性的认知。从一定意义上讲,演唱中国古诗词犹如演唱欧洲的艺术歌曲,对演唱者的哀求非常全面,不仅哀求歌者有良好的文学水平、艺术教化、歌唱能力,还哀求演出者具有很好的作品诠释、情绪表现和舞台表现力。笔者在传授教化中创造,唱好中国古典诗词作品对提升演唱者的音乐教化、文化素养,拓展演唱者的艺术视野,提升演唱者的歌唱技巧,丰富其音乐情绪均有很好的促进浸染。在古诗词演唱演习中,歌者应看重措辞文本研究,对古文中分外的发音要有准确备注;在发音演习中,歌者应强调以字带声、依字行腔、以气引声、气随韵动,努力做到声情并茂、以声现境。这种演习对付学习美声唱法的学生和青年演员来说,既是一堂必须过关的专业必修课,也是一堂主要的文化必修课。
中国古曲演唱是当前我国声乐传授教化和舞台呈现的难点和薄弱环节。中国的古诗词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诗经、楚辞、乐府到唐诗、宋词及至元人小令,古曲也经历了雅乐、歌、诗经、楚辞、汉乐府、绝律诗、词歌曲、情歌、元曲以及明清小曲平分歧文体的发展和演化,终极形成了中国古曲独特的艺术魅力和艺术风格。个中,兴于晚唐盛于宋代并发展延续至今的词体歌在古代诗乐史上霸占主要地位。中国古代的词从一开始大都是合营音乐来演唱的,有的按词制调,有的依调填词。宋代由于经济的繁荣以及浩瀚文人墨客的爱好,宋词成为当时最盛行的文学与音乐高度结合的歌唱形式。唐诗宋词的发展使词体歌成为我国传统民族声乐艺术的宝贵遗产,有些作品(如《鬲溪梅令》《杏花天影》《声声慢》《水调歌头》《念奴娇》等)至今还仍旧传唱。“曲”是元明时的一种文学形式,有格律限定,为配乐诗歌,个中散曲是元代杂剧兴盛前流传于市井的一种艺术歌曲形式。散曲盛行于元明两代,在音乐上,散曲继续了唐宋以来的音乐风格,个中的许多乐曲直接出自民间。现存的元代散曲曲谱中,有些曲谱的旋律已经带有昆曲唱法的修饰。虽然现今依原谱演唱元曲的情形已经不多见,但仍有一些作品(如由作曲家高为杰师长西席用徐再思的《折桂令春情》、贯云石的《红绣鞋 欢情》以及马致远的《落梅风蔷薇露》创作的元曲小唱三首)在院校和社会上传唱,足以解释元曲歌唱艺术生命力的顽强。明清时期在声乐艺术上呈现出百花争妍的景象,明清小曲、民歌、杂剧及昆曲等都深得百姓喜好。此外,古诗词中还有一种以古琴伴奏、自弹自唱的作品,被称为琴歌,亦即有歌词的琴曲。著名的琴歌如《阳关三叠》《渔歌调》《浪淘沙》《满江红》《胡笳十八拍》《醉翁操》等,至今仍旧被传唱。可见,中国传统声乐作品除了吐字行腔有独特规律之外,题材选择和曲目形式也十分广泛,民族多样性和演唱繁芜性特点光鲜,须要我们在理论和艺术实践上引起重视。
三是增强对民族民间歌唱传统的敬畏。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源远流长的民族风格是音乐艺术的母体和民族民间唱法的渊源。丰富多彩、风格互异的民歌作品中,反响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背景、风土习俗和审美情趣的作品霸占非常核心的地位。民歌腔调旋律大多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民歌创作与方言语音紧密结合,音乐表现也很生活化,形式生动灵巧,没有固定的格律。在中国,前文提到古曲中《诗经》、楚辞、汉乐府、唐歌诗、宋词、明清小曲、小令、俚曲以及各地的山歌,都属民歌范畴,都是现当代中国民歌创作的深厚源泉。新中国成立特殊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民族作品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期间,在保持民族风格的根本上,音乐格调更加活泼、爽朗、热烈、明快,充满了向上的激情和积极乐不雅观的时期精神。大量中国民族声乐作品涌现,给我们供应了广阔的研究及演唱空间,为专业声乐艺术传授教化供应给了大量的文献和作品素材,也是国家声乐艺术繁荣发展的主要表示。中国传统的民族民间歌唱方法在字、声、腔、情、韵方面的高度折衷,在字正腔圆、以情带声、高亢通亮、甜美清脆等方面的优点都须要我们学习继续。无数前辈都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和突出贡献。像赵元任师长西席的《教我如何不想你》,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等,把中国化的措辞习气和欧洲风格的和声、作曲手腕奥妙的领悟起来,创作出中西结合的经典作品。我国当代的著名歌唱家迪里拜尔、吴碧霞等,都在唱法上积极继续发扬民族精良声乐传统,是中西唱法有机结合的典范。有鉴于此,我们在唱法的演习中,应该对中国民间歌唱传统心存敬畏,多向民间歌手学习,加大对民间歌唱传统的研究和传承,避免人亡艺绝的悲剧反复上演。
四是加强中西融通的声乐艺术实践。相互领悟、取长补短、相互借鉴,是艺术发展创新的不二法门。梅兰芳师长西席就常常听泰西歌剧唱片和不雅观看泰西歌剧,理解泰西歌剧演出的风格特点,并且将个中一些可借鉴的有益部分化用到自己的京剧艺术演出之中,为我们树立了中西艺术融通创新的榜样。我国当代不少歌唱家和声乐教诲家也常常去听京剧、地方戏等,从中汲取科学有用的发声技巧。各种唱法的相互学习借鉴是大势所趋,也是当代声乐艺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我国当代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诲家郭淑珍教授所指出的那样:“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虽有很多不同,但是艺术究竟是相通的。学习美声唱法能为民族唱法带来很多启迪。接管的东西多了,想象力自然丰富,在音乐上的表现手腕就不再单一了。”在大众文化盛行的背景下,不少非专业人士在音乐选秀等大众平台上故意忽略声乐艺术的内在规律,极力倡导演唱个性、抹杀艺术共性,实在是有害的,不仅误导了大众审美,也侵害了专业传授教化,不利于我国声乐艺术的整体发展。西方美声唱法的歌唱理念和演习方法的科学性是经由艺术实践考验的,中国传统唱法和无数精良经典的中国声乐作品也是经由数千年纪月沉淀下来的,它们在艺术规律上没有根本意义上的冲突。中国歌曲中有不少经典作品是美声唱法与中国传统唱法完美结合的例子。用古诗词创作的《阳关三叠》《枫桥夜泊》《乌夜啼》《花非花》《满江红》《念奴娇》《鬲溪梅令》《杏花天影》《红豆词》等浩瀚作品至今仍为高校专业学习中的必唱曲目。一些随处颂扬的地方民歌,如山西民歌《绣荷包》、四川民歌《梅花几时开》、新疆民歌《手挽手》、陕西民歌《兰花花》、河北民歌《小白菜》等作品也是学习美声唱法的人所常常演唱的。以是,只要我们把握得当,真正做到各种唱法的交融贯通,终极一定会呈现出中西合璧、相映成辉、美美与共的可喜局势。
三
总之,当现代界是开放的天下,艺术也要在国际市场上互换竞争,没有互换竞争就没有兴旺的生命力。正如习近平总布告哀求的那样,“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负责学习借鉴天下各国公民创造的精良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交融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实在,当代以来,我国文艺和天下文艺的互换互鉴就一贯在进行着。口语文、芭蕾舞、管弦乐、油画、电影、话剧、当代小说、当代诗歌等都是借鉴国外又进行民族创造的成果。……这种学习借鉴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起到了促进浸染。”“中国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天下的。……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接管外来、面向未来,在继续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创作出更多表示中华文化精髓、反响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代价不雅观念、又符合天下进步潮流的精良作品,让我国文艺以光鲜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派头耸立于世。”在我国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大的新时期背景下,秉持国际视野,站稳文化态度,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傲,用科学的演唱方法和诚挚动人的艺术演出,在国内外声乐舞台上演绎更多精良的中国声乐作品,提升中国声乐艺术的吸引力、美誉度和影响力,为我国声乐艺术发展和文化强国培植贡献力量,是我们这一代声乐艺术事情者的社会任务和神圣义务。
当前,中国声乐艺术的科学性、民族性、原谅性、时期性特色更加显著,领悟创新(而不是“相互取代”)的内在动力和外部环境条件都比较充足,只要我们增强整体思维和大局意识,尊重声乐艺术的科学规律,坚守中国传统(或者说民族)声乐艺术的独特文化代价和审美代价,接管包括泰西美声唱法在内的其他各国声乐艺术的精良成果,就一定能将更多中国精良作品和前辈文化代价理念传遍全天下,赢得天下同行的尊重。(孙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