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朝辉
若有人问:“被雨淋成‘落汤鸡’的觉得若何?”
你定会刁滑地反问:“你说呢!
”、“问你呢,说实话!
”、“尴尬、狼狈、无可奈何!
”你终极会回答。
是呀,这是很多人遭遇淋雨时的心境。但,有一个人却是例外:“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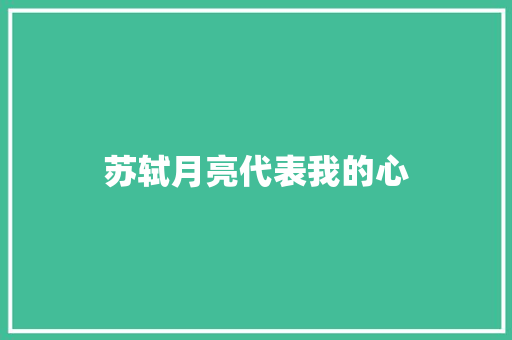
这是什么思维?但你先别急着惊异,惊掉你下巴的还在后面:“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意思很明白了:淋一场雨怕个啥,人生风风雨雨多了,由它去吧!
这位大侠级的人物,便是苏轼,宋代文学家、画家、书法家、美食家,官员。这么多的头衔,标准“牛人”一枚。
牛人归牛人,虽然他生性乐不雅观豁达,但面对人生的起起伏伏,如“过山车”一样平常的滋味,也会触动他的内心天下。
初贬黄州时寓居于定慧院,瞥见孤飞的大雁,他感叹道“惊起却转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夜饮东坡,夜深醉酒而归,被甜睡的家童挡在门外,“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怀营营。”他又感叹道 。
更多的时候,他会寄情于明月。特殊是在三五之夜,天上皎洁的玉轮俨然成了他的代言人:悲欢离合的亲情、沧海一粟的人生,都统统通过月光表达了出来。
“明月夜,短松岗”——明月见证你我夫妻情
北宋皇佑年间,眉州青神的中岩。中岩者,青神风景名胜之地。据《蜀中名胜记》载:“县之名胜在乎三岩。三岩者,上岩、中岩、下岩也。今惟称中岩焉。”
当地的文化人,乡贡进士王方在此办起学堂,招揽附近的好学少年,传授知识,讲授《四书》《五经》。浩瀚学子中,有一苏姓少年表现尤为突出,不但聪慧,而且容貌堂堂,深得王进士喜好。这个小伙便是苏轼。
回家后,王进士提及学堂的事,时常会提到苏轼。说者无心,听者故意,王家有一女,名一个单字弗,正处豆蔻年华,每听爹滴提及苏轼,心中充满了想象和好奇。
一天,他趁着跟随爹滴去书院的机会,偷偷不雅观察这帮诗人,当听到有人喊出苏轼名字的霎时,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就沉醉了:那个风姿翩翩的少年从此便深深地印在她的脑际,再也挥之不去。
至和元年,经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王弗正式嫁与苏家,小两口开始了十一年的夫妻生活。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噜苏中,小两口的生活更多的是温馨与和谐,读过书的王弗孝敬公婆,谅解丈夫,是苏轼虔诚的粉丝和贤内助。
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王弗在苏轼身边的主要浸染。苏轼为凤翔判官间,来一下属拜访,跟苏轼互换时,总是顺着苏大人的话走,客人去,王弗说:“此人不可交,他只会顺着你说话,不是一个实诚人!
”
然而,琴瑟和鸣的生活只持续了十一年,治平二年五月,王弗因病阖然离世。苏轼怀着无比伤痛的心情为爱妻撰写墓志铭,记下了两人在一起的幸福生活,并表达了对妻子的怀念。
“君得从先夫人于九原,余不能。呜呼哀哉!
余永无所依怙。君虽没,其有与为妇何伤乎?呜呼哀哉!
”
熙宁四年起,因与朝中实施新法的新党人士见地相左,苏轼自请外放离京,开始了为地方官的生涯。
熙宁七年秋,苏轼来到密州任知州。密州是个小地方,在这里,没有那么多繁杂的公务,他过着清闲的生活。
冬天里,他“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英武而豪迈。寒食后,他“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淡泊而从容。
虽说此时王弗去世已十年,且苏轼又娶了贤惠的王闰之,但当夜深人静时,花好月圆日,总少不了对王弗的思念。
熙宁八年正月二旬日夜,睡梦中的苏轼来到了眉山老家,透过绮窗,他瞥见王弗正在装扮打扮,而窗内的王弗也瞥见了心爱的丈夫,十年的离去,夫妻二人有千万的话语,却又不知从何提及,只有默默地相视。
十年死活两茫茫,不斟酌,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悲惨。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回籍,小轩窗,正装扮。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旬日夜记梦》
醒来的苏轼将梦境用一首词记录了下来,而这首词,也成了中国千古悼亡第一词。
“明月夜,短松冈”,在每个月明之夜,我压抑不住对你的思念。而我也知道,在那松柏护绕的坟茔下,你也会因对我的顾虑不舍而柔肠寸断。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明月牵手你我兄弟情
“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读过《三字经》的人都知道这几句话,个中二十七岁时开始发奋读书的苏老泉,便是后来“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厉害吧?但他还有两个儿子,比他更为厉害。
宝元二年,北宋眉山。苏老泉家喜添新丁,他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苏老泉为其取名苏辙。彼时,他第一个儿子苏轼刚刚三岁。
差距不大的年事,使兄弟二人有更多的共同措辞,为兄的苏轼,很有当哥哥的范儿,当手里有一块糖时,他必定先塞到弟弟嘴里。就这样,两人相依相伴,在玩耍、游戏中逐渐终年夜,伯仲之情甚笃。
比如,从政后的苏轼在经历“乌台诗案”劫难时,苏辙第一韶光上书天子:“臣早失落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非敢望末减其罪,但得免下狱去世为幸。”可见两人的亲情的深厚。
庆历八年,他们的爷爷去世了,父亲苏洵在家守孝。守孝的同时不忘对孩子的教诲,他将自己的学识传授给苏轼和苏辙。
一年又一年,苏轼苏辙兄弟在相互切磋,相互提携中共同进步着。随着读书量的增加,知识日益丰富,他们的诗词和文章越来越精彩,在当地,人们都知道苏老泉家有能诗善文的俩儿子。
是时候向外推介了。于是嘉祐二年,苏洵带领苏轼苏辙弟兄二人千里迢迢北上京城,参加了礼部组织的会试,二人名列前茅,特殊是苏轼的试卷,得到了大文豪欧阳修的高度认可。
四年后,两人又一同参加了制科考试,这样,他们得到了入仕的资格,从此开始了他们的仕途之路。
同年秋,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苏辙也有了任命,但他向朝廷提出留京照顾父亲,朝廷履行人性化管理,批准了他的要求。
苏轼离家赴凤翔,兄弟两人面临人生第一次离去。依依不舍下,百里相送,苏辙陪家兄同行直至郑州后,方在此话别:“哥,路程迢遥,人生亦难,后面就你一个人打拼了,多保重!
我送你一首诗吧!
”
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
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度古崤西。
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
遥想独游佳味少,无方骓马但鸣嘶。
——《怀渑池寄子瞻兄》
然后他目送苏轼远去,直至消逝在视线中。
几日后,独行的苏轼行经渑池,夜宿进京赶考时曾经住过的寺庙,五年间,人已换,物亦变,他多有感慨,想起弟弟临别时的赠诗,于是和韵而成诗一首。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有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去世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昔日波折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和子由渑池怀》
兄弟二人提到人生如雪泥鸿爪,在当时大概是年轻人的无意感慨,但是后来却在他们兄弟俩起伏的人生路上得到了应验。
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变法开始。苏辙大胆指出青苗法的弊端,触怒了王安石,被贬离京。两年后,同样因与新党人士的政见不合,已在京为官的苏轼自请外放。此后多年,两人各清闲地方上辗转为官,难得一见。
熙宁九年,苏轼任职于密州,此时苏辙在齐州为官。中秋夜,天上月圆,人间兄弟却各居一方,苏轼闷闷地饮酒,与家人在一起的光阴时时闪过脑际,是那么近,又是那么迢遥……他通宵未眠,把酒问月而成千古名篇。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上苍。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此后,这美好的祈愿就成了他们兄弟俩的生活信念,在往后愈加坎坷的人生路上,在那些聚少离多的日子里,这个信念支撑着两人一贯向前。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月明月暗如人生
“莫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骚人物。”这些句子,表示着苏轼的乐不雅观与豁达,同时,透过他的诗句,又可以看出他有着丰富的感情,是个脾气中人。
这些性情特点,能让他在困难面前无所畏惧,年夜胆向前,但有时,却会给他带来麻烦。
元丰二年四月,朝廷一纸调令,苏轼从徐州转任湖州知州。按老例,到任后的他要给朝廷写一封信,谈谈自己对主政地区的认识及对新职务的感想熏染,末了更要隆重地对圣上表示感谢,感谢皇恩的浩荡,感谢天子的厚爱。也便是说这样的信是有固定格式的。
然而苏轼偏偏把有固定格式的官文写成了一篇抒怀散文,字里行间融入进自己的丰富情绪。“陛下知其愚不应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他在《湖州谢上表》中说。
句中的“其”是他自己,“新进”是朝中履行变法的新党人士,“难以追陪”则是说自己难以苟同新党的政策。他说这些话,实在只是发发牢骚而已,要真干起活来,他还是很拼的。
常言道祸从口出。苏轼是因对变法有成见而选择外调的,这在朝中大家皆知,自打他任职地方后,那些新党人士就一贯警觉地盯着他,无时无刻不盼他搞出点事情来,从而可以光明正大地对其进行打压。这次,他们终于有了机会。
七月,御史台的李定、何正臣等人接连对苏轼发起弹劾,并挖空心思地找出苏轼诗稿中貌似“反动”的言辞,给他扣上了“愚弄朝,妄自傲大”,“衔怨怀怒”,“包藏祸心”等一系列大帽子。
神宗大怒,立马派出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往湖州缉拿苏轼。到达湖州后,皇甫遵态度十分强硬,蛮横地将苏轼扣押。史载“僎径入州廨,具靴袍,秉笏立庭下,二台卒夹侍,白衣青巾,顾盼狰狞,民气汹汹不可测。轼恐,不敢出,乃谋之无颇。”
八月,苏轼被关入御史台监狱中。在两个多月的韶光里,苏轼受尽了非人的折磨,经历了严刑拷打,昼夜逼供,“诟辱通宵不忍闻”。末了,李定等人强加给苏轼“四大罪状”,要求神宗处去世苏轼。
一韶光,朝野高下,舆论哗然,许多有识之士认为:苏轼未犯叛逆罪,不该重处。就连新法的发起者王安石也上书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这次,正义的力量霸占了上风,各方面的营救和舆论的压力,匆匆使神宗对苏轼从轻发落,乌台诗案终极以苏轼“蒙恩责授黄州团练副使”而告终。
这样,苏轼的命是保住了,但奇迹官职却一落千丈。
六年后,神宗驾崩,高太后摄政,起用旧党人士司马光为相,苏轼得以重回京城,官至翰林学士。至此,他的人生彷佛完美了,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当他看到掌权后的旧党对新党人士进行残酷打压时,他又看不下去了,他认为所谓新党旧党,不过是一丘之貉。于是,他又主动哀求外放。从元祐四年至绍圣元年,五年韶光里,他先后任职于杭州、颖州、扬州、定州,如此这样,让他安然度完此生也好。可是,命运总爱捉弄人。
绍圣元年,新党再度执政,又开始了他们对旧党人士的穷追猛打。六月,苏轼被贬惠州。惠州,便是那个“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岭南之地。是年,苏轼五十八岁。
身为带罪之身,你还能优哉游哉地吃荔枝?我让你炫耀!
旧党人士十分生气,于是加贬的文书又从京城发出。绍圣四年,一叶小舟载着六十有一的苏轼穿过琼州海峡,到达儋州。
当时的海南可不是现在人们争相去度假的海南,在宋代,那里是标准的蛮荒之地,流放海南,意味着让你“生不如去世”,是仅仅轻于满门抄斩的一种惩罚。
但乐不雅观的苏轼仍坚持着,他以这里为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说。
中秋来了,在红颜心腹朝云的陪伴下,他度过在海南的第一个中秋。宴饮赏月,把盏北望,他的思绪很乱。他想起了在雷州的弟弟苏辙,想起了两人在一起的那些快乐日子。他还回忆入仕之后经历的风风雨雨,起起落落,世事如梦,人生几何!
他发出了无奈的叫嚣。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
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
把盏凄然北望。
——《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
“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玉轮,本是又圆又亮的玉轮,可是,人间看到的玉轮,有几次是圆的?又有多少是通亮的呢?
月如人生,难求圆满,在暗淡交替中淡然度过,也不虚此行。
-作者-
杜朝辉,山东潍坊人,中学思政课西席,古诗词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