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的实质特色是燃烧,这带动了诗也燃烧。岑参《经火山》:“不知阴阳炭,何独燃此中。”蒲昌东的煤自燃事宜,把白云照得红艳艳,把天空烧得炎蒸蒸。宋诗,煤也燃烧。吴昭淑在《望江南》中写到和朋侪取炉生煤,烧喷鼻香把酒:“坐拥地炉生石炭,灯前小雨好烧喷鼻香。”司马光在《太行》中写到燕郊皆烧煤:“晋市飞樵札,燕郊落烧煤。”可见,诗中煤以燃烧作为主题,火焰纵横古今。
煤的燃烧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促进了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亦有诗为证。刘崧《赋壁煤》:“窗下煮茶久,烟煤半壁生。”陆游《初到荣州》:“地炉堆兽炽石炭,瓦鼎号蚓煎秋茶。”贯休《寄怀楚和尚二首》:“铁盂汤雪早,石炭煮茶迟。”于鹄《过凌霄洞天谒张师长西席祠》:“炼蜜敲石炭,沐浴乘瀑泉。”煤得到了广泛和普遍利用,哪怕是隐逸墨客和僧人,也已经离不开煤了。
写煤的诗表面看来强调暖的含义,实则凸显光明的象征意义。苏轼《石炭(并引)》:“投泥泼水愈光明,烁玉流金见精悍。”于谦《咏煤炭》:“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朱自清在《煤》中写道:“黑裸裸的身体里,/一阵阵透出赤和热。/啊!
全是赤和热了,/俏丽而光明!
”苏轼写“愈光明”、于谦写“照破夜沉沉”和朱自清写“俏丽而光明”,皆是作家推崇煤光明的象征意义。
古今循环,煤在诗中至少表现出两大当代转换。煤从客体转换为主体。新诗中的煤扮演了独立的主体,而不再是古诗中被言说的物质客体。郭沫若《炉中煤——眷念祖国的感情》中,煤化身为经由新思潮洗礼的知识分子“我”;朱自清《煤》中,煤化身为一位有着幽美姿态和高尚情操的舞女“你”;艾青《煤的对话》中,煤以“你”与当代人“我”之间,以问答形式磋商人生。煤的身份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精神一脉相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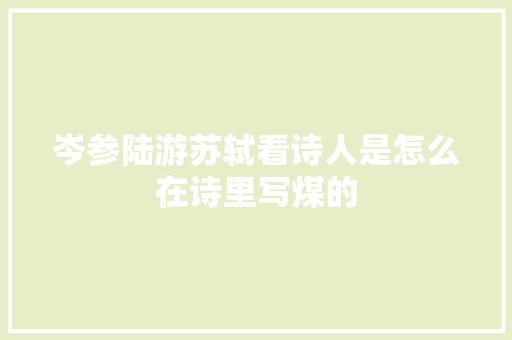
煤从苦难转换为幸福。古诗中的煤是荼毒生灵的苦难见证。刘崧在《石炭行》中阐述了人们挖煤的悲惨现实,去世人无数:“何年下掘得石炭,劫灰去世凝黑龙骨。”“乡夫如鬼入隧道,鞭血哭泪交滂沱。”墨客发出了悲天悯人的情怀:“我愿天公悯民苦,尽敕石煤化为土,随穴湮填永无取。”
新诗中的煤是国泰民安的幸福见证。郭小川《婚期问题》中男主人公说道:“十天半月不结婚,/真正的爱人中间不会有事件发生;/春节五天假期不采煤,/多少吨黑金子可就要落空。”煤变成了珍宝。郭小川在《胜利矿纪事》中写道:“在这里,什么东西最宝贵?/是那黑得发蓝的煤。”从“永无取”到春节加班加点开采,煤彻底地华美变身。
诗中一寸煤,人间百世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