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北征》
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
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向月明看。
长久的戍边生活,思乡成了将士心中不可触摸的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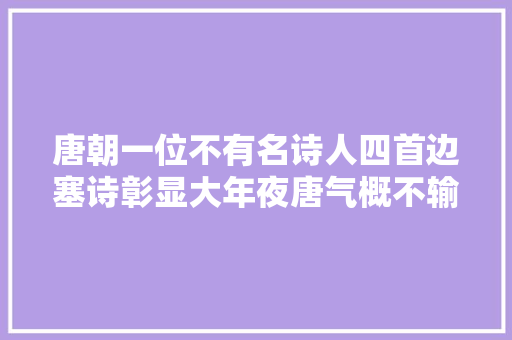
幽怨的笛曲《行路难》响起,久郁在他们心中的思念之情一引而发,三十万人由于笛声发出了一个动作“回顾月明看”。
这笛声不是一支、两支的声音,也不是微微弱弱的声音,而是很多支笛子亦很多笛音汇在一起,在夜空久久回荡。由笛声引发的举动,实在是先引发征人的心里感想熏染,然后才引发出行为动作。
雪后的天山下,砭骨的寒风里,溘然一阵哀怨的笛声响起,一定触动征人那久积在心里的怀乡思亲之情。“三十万”和“一时回顾”固然是夸年夜,但也最充分地表明笛曲的凄怨和无数征人的心情。画面既壮不雅观又凄美,正是王国维所说的“境界全出”的艺术效果。比王昌龄的“烽火城西百尺楼,薄暮独上海风秋”更加深邃耐品。
《夜上受降城闻笛》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先写月下边塞景景:了望大漠沙白如雪,近看城下月色如霜,一片凄冷的景象。“似雪”和“如霜”都是借寒气袭人的景物来表现悲惨愁苦的心情。这样的景物,这样的心情,为下面做了很好的铺垫和渲染。一声笛曲在寂静的夜空响起,圆月牵情,笛声牵情,那无尽的乡愁顿然触发无法遏制,其结果当然是“一夜尽望乡”了。
不说思乡,而是望乡,以人物情态展现人物心里,蕴藉写出那不尽的乡愁。景致,声音,心里感情三者融为一体,面前之景与心中之情相互交融,寓情于景,以景写情,动听肺腑。
画面感强,节奏平缓,意境浑成,诗意婉曲。
刘禹锡很喜好这首诗,晚年还写下“边月空悲芦管秋”之句,来追思李益。与范仲淹的“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一样,让人回味无穷。这首诗在当时流传很广,谱曲入画,被誉为中唐边塞诗的绝唱。
《过五原胡儿饮马泉》
绿杨著水草如烟,旧是胡儿饮马泉。
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边。
从来冻人关山路,今日分流汉使前。
莫遣行人照容鬓,胆怯干瘪入新年。
全诗八句,险些每句一景:无际的草原;清澈的饮马泉;吹笳的月夜;倚剑云边的将士;冰封雪冻的关塞路;汉使前的淙淙流水;不敢临泉照影的老人和回顾中的青春少年。就像八个镜头向我们依次推进,有远有近;有看到、听到、想到的;有面前的和有过去的。这些汇聚到一起,形成一幅蕴藉凝重却也色彩绚丽的五原画卷图,令人产生无尽的遐想与思虑。
该诗语句幽美,节奏和谐,忧闷多于欢欣,失落望多于希望,欢而不乐,伤而不悲,把繁芜的心里表现的蕴藉深奥深厚,婉转低回,是一首不可多得的边塞诗。
中唐期间,随着唐朝国力的衰落,周边异邦更加紧了侵扰的步伐,边患频发,战事连绵。无数戍边将士只能长期生活在无尽的痛楚与期待中。这一期间的边塞诗少了盛唐的豪迈冲动大方,多了些哀婉和凄凉。
《塞下曲》
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
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
比较于上几首的感伤哀怨,这首诗充斥着昂扬和雄壮。
用马援“就义沙场”和班超“生回玉门”的典故,表达了将士们决斗苦战疆场、舍身殉难的英雄气概。为了保卫国家,以马援为榜样,不效仿班超“但愿生入玉门关”,大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势和决心。
这还不算,用薛仁贵“一箭定天山”的典故,来表达将士的决心:不但要全歼仇敌,还要留驻边陲,让仇敌不敢再来陵犯。
比岑参的“亚相勤王甘辛劳,誓将报主静边尘”更加豪迈旷达。全诗音节洪亮,基调高昂,气吞胡虏的报国情怀跃然于纸。
一幅盛唐气候,大气磅礴,高昂自傲。
李益是凉州武威人,从汉代起,这里便是征战之地。李益从小受大漠烽烟的熏染,又自称是汉代飞将军李广之后,骨子里就很有杀敌卫国的情怀。他曾在燕、赵一带游历,又在幽州节度使幕中任过从事,经历加上诗才和情怀,使李益的边塞诗既雄浑又明快,既年夜方又悲壮,既有节奏美又有音乐美,既色彩光鲜又用笔凝练。不愧是唐朝中期精彩的墨客,也是唐朝中期边塞诗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