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一贯没把王洛宾和骆宾王分清楚,以为都是骆宾王,一个是《咏鹅》的骆宾王,一个是《在那迢遥的地方》的骆宾王。
为什么没分清,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我那会就没想过去分清。
诗,念着晃头。歌,听着凝眸。诗与远方,本来便是同来一处。
直到后来读到率情、浪漫的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听到她的《橄榄树》,也跟随她听了一遍《在那迢遥的地方》,然后忽然就真切的记住了王洛宾这个迢遥深情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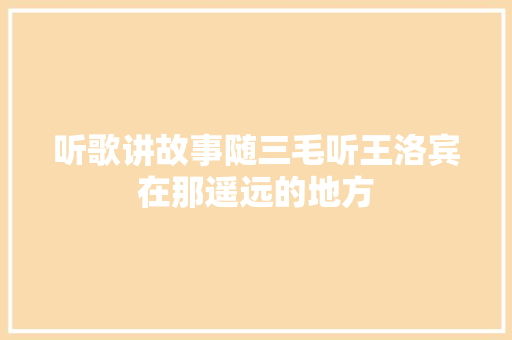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概也是诗和远方的召唤,让王洛宾取了这么一个格高意远的名字,且生活在一骑尘凡阔的新疆和俏丽天山北麓下的乌鲁木齐。广袤无边的大草原,予以了他策马奔驰的激情亲切,浩海沙黄的丝路,予以了他遐想连篇的故事,山花烂漫的城市,予以了他碧水蓝天的深情。
创作《在那迢遥的地方》之时,那年(1941年)王洛宾28岁,正是斗志昂扬之年。王洛宾随着电影拍照组来到青海湖畔拍摄《祖国万岁》,个中当地同曲乎千户的女儿萨耶卓玛扮演影片中的牧羊女,而在西宁教书的王洛宾则是扮演萨耶卓玛的帮工。
由于剧情须要,导演安排王洛宾和卓玛同骑在一匹立时。王洛宾起初很拘谨,坐在卓玛身后,两手牢牢抓着马鞍。卓玛却对此绝不睬会,忽然纵马狂奔,王洛宾一时不防,本能地抱住了卓玛的腰。卓玛狂驰了良久,在那大草原上,这才把马缰交在王洛宾手中,靠在他的怀里,不再撒野。
薄暮牧归,卓玛将羊群轻轻点拨入栏,夕阳下的卓玛亭亭玉立,晚霞的余照映照出卓玛的侧影……王洛宾痴痴看着卓玛,火苗映红了她的脸,如格桑梅朵般绮丽。
卓玛也觉得到王洛宾如波光荡漾般的眼神,于是跳出了火苗,举起手中的牧鞭,轻轻打在王洛宾身上,然后返身走了。
王洛宾依旧呆若木鸡,看着这个俏丽、俏皮、旷达的姑娘轻轻远去,也轻轻抚摸刚被鞭策的地方,陷入漫无边际的黑夜思虑。
第二天,电影队要离开了,王洛宾也要回到西宁。卓玛骑着马十里相送,终于在一个小坡上愣住。王洛宾骑在骆驼上,不住地回望着那渐行渐远的小点,随着驼峰起伏,驼铃叮略,王洛宾心中的情绪化为词曲,借助哈萨克民族的曲调唱出了不朽之作《在那迢遥的地方》:“在那迢遥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帐房,都要转头留恋地张望……”
三毛亦是一个至情至性的女子。她与荷西的那段死活恋,旷世不羁,让那些在爱中百转千回寻寻觅觅的人迷恋不已。当荷西命殒大海,三毛的灵魂也随之命殒大海,若不是为了任务而活着,或许她也早已跟随荷西而去。
三毛就这样一贯茫然的行走在苍茫的人间,至于灵魂、情归何处,茫然不知。
直到1989年,有一个人重新唤醒了她的灵魂,重新点燃了寂寥的情绪。作家夏婕在新疆采访王洛宾后,揭橥了《王洛宾老人的故事》。三毛读了之后,非常愉快,由于那可是王洛宾,自己一贯喜好的一位灵魂伴者。
随后,她理解到,王洛宾曾因“莫须有”的罪名,先后入狱两次,共长达18年,差点将“牢底坐穿”。在年近不惑之年,妻子病逝之后,他就孤零零地去世守在俏丽的新疆,不过仍旧痴迷艺术,不断辗转各地,采集民间歌谣。每天薄暮,他都坐在门前看夕阳沉坠;夜幕四垂时,总要对着悬在古旧墙壁上的太太遗像,弹一首曲子给她听......
这些都让三毛不可自拔的想起了荷西,也不可自拔的想着前往看望王洛宾。于是她不仅给王洛宾写了信,并积极合养分病,大病初愈之时,就迫不及待的来到了乌鲁木齐这个陌生而又熟习的城市,去见一个陌生而又熟习的人——王洛宾。
初次见面。三毛被同样留着胡子却戴着眼镜、刚毅的面庞却有着温顺似水的眼睛的王洛宾打动了。王洛宾亦被披着海藻般头发、带着秋水盈然般眼眸的三毛打动了。
他们仿佛便是莫逆已久的故友,只是大略寒暄,便是一番无边无涯的长谈。
余兴之余,三毛为王洛宾唱起了自己的代表作《橄榄树》,以作回应憧憬已久的《那迢遥的地方》。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为了天空飞行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
王洛宾也随声轻轻唱,看着三毛,无端想起那迢遥的地方的格桑花,还有萨耶卓玛。他仿佛听到,卓玛骑着马游弋在无边的格桑花草原上唱起那首神思梦绕的《那迢遥的地方》。
“在那迢遥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都要转头留恋地张望。她那粉红的笑脸,彷佛红太阳,她那俏丽动人的眼睛, 彷佛晚上妖冶的玉轮。我愿抛弃了财产,跟她去放羊,每天看着她动人的眼睛,和那俏丽金边的衣裳。我愿做一只小羊,坐在她身旁,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歌声曼妙遐远,三毛与荷西,王洛宾与卓玛,三毛与王洛宾……彼此相和。
投桃报李。尔后,王洛宾也为三毛唱了一首狱中的作品《高高的白杨》,并先容了歌中的故事:一个维吾尔青年在结婚前夜被捕入狱,俏丽的未婚妻不久便郁郁去世去,青年为了纪念爱人蓄起了髯毛。当王洛宾唱到“孤坟上铺满了丁喷鼻香,我的髯毛铺满了胸膛”这句歌词时,三毛哭了,只有经由爱断情殇的人,才能领悟这彻骨的孤独。
荷西之于三毛,王洛宾亡妻之于王洛宾,都是那高高的白杨,亦是那远方的橄榄树。
三毛哭了,在王洛宾看来,那是最美的珠花,就像那格桑花,悄然盈落绽放在他的内心。
回到台北后,三毛以满腔激情亲切倾付揭橥了《中国“西北民歌之父”王洛宾一鞭钟情》和《在那迢遥的地方找到了原作者》。王洛宾亦回应两篇短文《海峡来客》和《回访》,遥相呼应给予彼此最真的赞颂,且蜚声两岸。
尔后,两人书信来往,鸿雁传情,开始了继荷西后,三毛的又一段旷世恋情。
有人说,这段恋情,是三毛与荷西的爱情的一种延续。也有人说,这段恋情,是三毛感情的重生。但无论是那种说法,在这段恋情中,三毛表现得更主动和激情亲切,就像当年的荷西,而王洛宾表现得更内敛沉着。
或许,在爱情当中,主动一方,会心甘宁愿的付出。三毛亦是如此。
三毛在心中炙热的表达自己的感情,而写过无数情歌的王洛宾此时却犹豫了,他给三毛写信委婉的表达自己的彷徨:萧伯纳有一把破旧的雨伞,早已失落去了雨伞的浸染,但他出门依然带着它,把它当做拐杖用。
王洛宾在心中不无忧伤的自嘲:他就像萧伯纳那把破旧的雨伞。之后,王洛宾逐渐减少了给三毛写信的次数。
为此,三毛忐忑的来信,嗔怪他说:你好残酷,让我失落去了生活的拐杖。
后来三毛更是来信说要去到王洛宾家里住,且说:不住宾馆,住在家是为了走近你。
王洛宾没有推却,也盛情以礼相待,借军车亲自接送,专门为三毛买家私。相住期间,他们一起谈天、弹琴、唱歌、作词,买菜、做饭,甚是欢快,是他们久违了的幸福样子容貌。
可欢快的时候不长,藏在欢快背后的不安定成分终于导致事情急转而下。因听闻三毛来住在王洛宾家里,一大批纷纭来访。王洛宾或许是碍于情面和身份,不断动员三毛合营采访,或者说一些场面的话。而三毛却是只想和王洛宾独享光阴,不想受外界叨扰。
可王洛宾毕竟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耄耋老人,与四十多岁的三毛年事相差太多,囿于年事、子女或是社会的一些考虑,虽然有爱的勇气,但缺少爱的行动。
意气消沉,三毛末了还是拖着行李箱离开回到了台北,然后不久,自缢身亡。
噩耗传来,王洛宾悲痛不已。他以为,是他的镇静浇灭了三毛重生的激情亲切,让她再回到了那无边无涯的孤独,然后孤独了却生命而去。
恍恍惚惚,不知时日,王洛宾写下了末了的一首情歌《等待——寄给去世者的恋歌》。
“你曾在橄榄树下等待再等待,我却在迢遥的地方徘徊再徘徊。人生本是一场迷藏的梦,且莫对我责怪,为把遗憾赎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