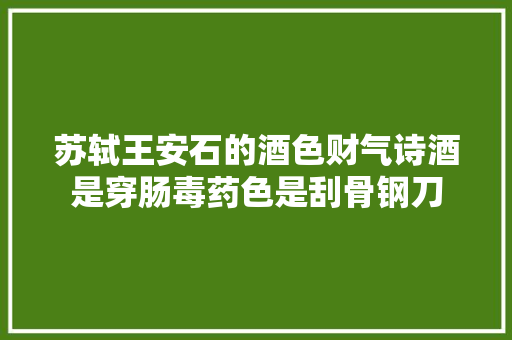传言,北宋著名僧人佛印,在大相国寺的墙壁上,题下这样一首《酒色财气诗》:
酒色财气四堵墙,大家都在里边藏。
谁能跳出圈外头,不活百岁寿也长。
弘一法师书法
佛印是空门中人,自然主见四大皆空,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酒色财气,都人的执念,沉沦在这些欲念之中,每每损命伤身,只有看破执念,“跳出圈外”,方得清闲,寿命延长。
佛印是苏轼的好友,一天,苏轼客岁夜相国寺找佛印,人没见着,却瞥见了这首诗,于是和了一首:
饮酒不醉是豪杰,恋色不迷最为高。
不义之财不可取,有气不生气自消。
苏轼是一个达不雅观之人,佛印的看破执念,实在也是一种执念,由于你要一直地与自己的希望作斗争。在苏轼看来,希望不一定是完备肃清,只要懂得将自己的希望掌握在适度的范围之内就好。
自古豪杰皆好酒,但过度就会伤身误事,以是饮酒不醉,才是真豪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不能沉迷于美色之中,也便是“君子好色而不淫”。不义之财不可取,反过来说便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凡人皆有气,但气会让人失落去理智,聪明的人懂得用理智来开导自己的怒气。
后来,宋神宗和王安石同游大相国寺,看到了佛印和苏轼的诗,宋神宗让王安石和一首,王安石和诗如下:
无酒不成礼仪,无色路断人稀。
无财民不奋发,无气国无活气。
王安石是墨客,同时也是精彩的政治家,他的视角与前两人完备不同,他看到的是酒色财气的浸染。
在王安石眼里,酒是聚会礼仪的必备之品,色有使令人们交往的主要浸染,钱财能匆匆使公民奋发向上,气能使国家焕发生机。王安石显然是看到积贫积弱的现状,北宋一贯受人陵暴,便是过于忍气吞声。
末了,宋神宗也和了一首:
酒助礼乐社稷康,色育生灵重纲常。
财足粮丰家国盛,气凝太极定阴阳。
神宗是天子,他的视角自然要站在国家的高度上,他进一步发挥了王安石的思想。在宋神宗看来,酒是国家礼乐的赞助,色是能使国家人丁茂盛,国家要财足粮丰才能或大,而气胜且凝聚在一处,便可定乾坤。
上述四诗,各从一个角度阐述了酒色财气的短长,但不太可能是苏轼王安石这样的大墨客写的诗,更有可能是小说家言,附会上去的,由于四诗虽有警世的浸染,但过于浅俗,完备没有艺术性。
后人将四首诗整合在一起,形成了更普通且流传更广的《酒色财气歌》:
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
财是下山猛虎,气是惹祸胎苗。
看来四字有害,不如一笔勾销。
无酒不成礼仪,无色路断人稀。
无财世路难行,无气到被人欺。
看来四字有用,劝君相机行事。
这首《酒色财气歌》,前半言害,后半言利,酒色财气到底是有害还利呢?终极还是看人,从皆有希望,懂得克制开导自己的希望,乃至利用自己的希望勉励自己奋发向上的人,才是真正的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