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不是文章之类的东西,一定要有言外的东西,格调、意象都还是壳,还在这里打转就永久不睬解诗。一样平常人写诗,开始都是追求一种格调、气势之类的东西,这是最初的阶段,所谓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然后能够打破这个阶段,就达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境界;终极,前一个阶段也冲破了,便是山还是山,水还是水,日日是好日,时时皆花时。站在诗词本身的角度,大多数的墨客都只是在第一个阶段打转,第二个阶段,实在便是全体海德格尔哲学末了的归属:诗意地栖居。存在即诗,诗即存在,能达到这种状态的,象李白、杜甫、苏轼这些超一流的墨客。至于第三阶段,就算海德格尔也难窥其门,在中国墨客里面,陶渊明在某种程度上算是有点眉目,杜甫在老年时偶尔也触及。
而在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层面,所有有关风格、神韵之类的谈论都是故意义的。不过,这里还是用一个最普通的字“味”。所谓味,有有形的、有无形的,有可以咀嚼的,有无法咀嚼只能神会的,也便是所谓的味外之味。有形的东西都很好说,无形的就比较麻烦。以前的人都喜好用水中之盐这样的比喻来靠近那种无形的东西,但水中之盐只不过说诗之形与诗之味的不可分,但这种不可分还是粗糙,按照现在的科学,就知道实在还是可分的,在分子层面就可以分开了,以是这个比喻在古代可能还有点意思,在现在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先看看李商隐的“天涯”:
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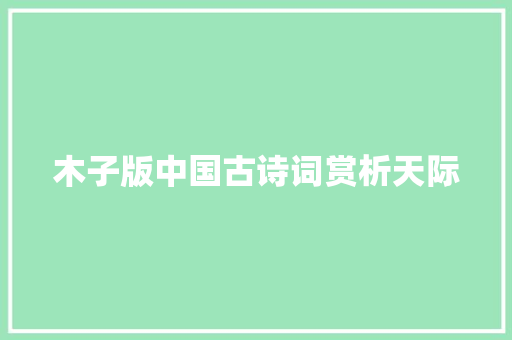
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
春日在天涯飘泊,飘泊已近薄暮;花开到最高枝则意味着将尽,而花开尽则春也尽,春日近薄暮,春天也近薄暮,而莺啼从鸟啼,也从呜咽,引出泪来沾湿最高花,是春天?是人生?是时期?是无穷的循环?如有泪,但泪岂曾有?无泪、有泪,但春日总在天涯,而天涯日总会斜去。失落意蹉跎、寥落孤独、生命凋零、天涯羁旅、空想幻灭、人生挫伤等等等等都成了剩语,浩浩乾坤尽迷失落在这有形无形的那一点泪上面。
不管什么人,总在这“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的时候,此时此有,涵盖六合,只是一样平常人无法体证,无法道出而已。而李商隐这 20 个字,盖天盖地,岂是那些纯挚大意象的堆砌而能够达到的?全体宇宙都在这一点有形无形的泪中融化,在这里,什么评语都是多余的。从某种意义上,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能算是诗,真正的诗一定是和全体宇宙交融的,最纤弱、又最雄大,统统的对立都在个中溶解又分绝不失落。在这种真正的诗歌面前,所有有关风格、格调、神韵之类的东西都成了头上安头,什么历史、时空之类的东西都成笑话,统统即一,一即统统,而一又何立?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参透这 20 个字去吧。正所谓情语、禅语,圆珠一点,非色非空,胡来胡现、汉来汉现,绝无虚言。
希望上面的剖析,对各位的诗歌视野的开阔有一定的帮助。那种把诗歌勾留在类性冲动的发泄的状态,不仅侮辱了诗歌,更侮辱了自己。诗即存在,存在即诗,你又如何能不诗意地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