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谈,来源:唐诗宋词古诗词(ID:tsgsc8)
三国的曹丕曾经说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一贯到了如今,曹丕也都变成了古人,但这句古话却从未过期。
不知诸位诧异否,唐朝的墨客,如繁星般残酷,涌现过不下两千多位,但我们实在又很少听说,谁和谁曾经激烈地争吵过。
我们从小接管的教诲,不支持我们凑热闹看吵架,但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墨客之间若然不相轻,多少有些说不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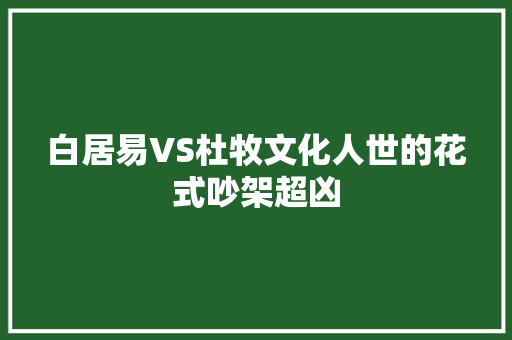
创作晚唐诗歌高峰的杜牧,曾经非常激烈地批评过白居易。白居易嘛,比杜牧年长约30岁,在唐朝众墨客中,排名第三,从资历到年事,都堪称长辈。
这两个人的争吵,该当比较故意思。
01
自古文人相轻,但坦率地说,唯独这二位,其实不该相轻。
首先,两人出身于同一个阶层,是同一类人。
白居易的妻子姓杨,妻子的哥哥名曰杨虞卿,杨虞卿曾经官拜京兆尹,即都城会长之职,但与杨姓的姓氏比较,“京兆尹”反而不算什么。
杨虞卿家族出生于虢州弘农,汉唐之时,对付来自此地的杨氏,后世学者给他们起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关陇王谢。
杜牧出生于京兆的杜氏,同样是豪门,当时的民间鄙谚还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之说。
此话的意思是说,长安城城南的韦曲和杜曲,崇高到离天只有一尺五寸。
唐王朝有“李武韦杨”四大姓,杜氏与韦氏并列,其崇高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京兆的杜氏,同样是光陇王谢。
唐朝中后期以来,宦官专权,他们乃至能旁边天子的废立,乃至是死活;天子掌握力有限,底下各个部将便拥兵自重,藩镇盘据的征象,也愈演愈烈。
在政治层面,白、杜两位墨客,都旗帜光鲜的反对宦官专权,也不能容忍藩镇盘据,他们由衷地希望,天子能够再度执掌天下。
然而,所有的希望,不过是徒劳,两人在政治上,究竟是无力的。
在日常生活中,白、杜的志趣竟也相通,皆好玄门,且好美色。而且,他们皆好以男欢女爱为题材入诗。
譬如,白居易在年迈之时,犹然作如下之诗:
昼听笙歌夜醉眠,若非月下即花前。
如今老病须知分,不负春来二十年。
通过此诗,白先生长西席为我们贡献了,“月下花前”这个针言。而杜牧同道,亦然不遑多让,在与某个妓女分别之时,他曾经作如下之诗: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仲春初。
东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杜牧更狠,他一股脑创作出两个针言,即“娉娉袅袅”和“豆蔻年华”。
毫无疑问,他们的艳情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各自霸占了两座高峰。
02
从出身、政管理想,到诗歌志趣,两人情况类似,本应成为忘年交才对,怎奈却话不投机。
若问个中缘由,还要从他们的“私仇”开始提及。须要指出的是,后世很多学者,言及杜牧批评白居易,常常从高大上的格局出发,譬如“为了中国诗歌的发展”如斯。
这种情由自然也无可争议,但却剥离了墨客作为“人”的实质,他们当然也有爱恨情仇,否则如何写就这细腻的诗篇?
笔者不妨“小人”一些,从两人的“私仇”动手剖析。
话说,杜牧有个朋友,名曰张祜。张祜本人家世显赫,为人清高,当时之人对他有“海内绅士”的赞誉。
张祜颇有诗才,却不善于科举文章,某次他到达杭州,拜访时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希望白能举荐自己,进京师参加进士考试。
白居易经由一番稽核,却择取另一个举子徐凝为解元,结果张祜终极未能考中进士。
如果说白居易对待张祜的行为,还有商榷的余地,白的至交好友元稹,则有落井下石的嫌疑。
有个叫令狐楚的节度使,很看重张祜的文才,便亲自写奏章举荐。在奏章中,令狐楚夸奖其诗歌曰:“研几甚苦,搜象颇深,辈流所推,风格罕及。”此评价不可谓不低。
天子看罢奏章,咨询元稹的见地,元稹的回答,则难免不免小气,他说:“张祜雕虫小巧,壮夫不为。”
元稹认为张祜的诗作,过于小家子气,大丈夫不会那样写,如果奖赏他太过,势必影响风尚教养,因此不同意重用之。
实事求是地说,元稹此语,多少有些昧良心。论起普通,以及“小家子气”,可能无人能超越他和白居易了。
由于白居易的谢绝、元稹的排挤,张祜遂以隐居为生。
与元、白不同,杜牧却非常钦佩张祜的诗才,对付元稹排挤的行为,他选择作诗为朋友鸣不平:
一闻周召佐明时,西望都门强策羸。
天子好文才自薄,诸侯力荐命犹奇。
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更不疑。
唯是胜游行未遍,欲离京国尚迟迟。
除了正面硬刚元稹,杜牧还不忘作诗回怼白居易:
睫在面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
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
诸位且看杜牧诗中满满的恶意:头一句,睫毛就在面前却看不见,可以理解为,说白居易,“有眼无珠”;末一句,则是阿谀张祜,您有千首诗篇,足以唾弃那个万户侯,还是白居易。
03
如果说白居易不待见张祜,还算是小打小闹;那他与杜佑之间的冲突,则直接让杜牧怒发冲冠。
杜佑何许人也?杜牧之祖父也。
墨客之间的抵牾,当然还要从诗歌开始提及。话说,白居易曾写过一组长诗《秦中吟十首》,十首诗中有一首名曰《不致仕》,开篇是如此说的:
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
何乃贪荣者,斯言如不闻?
《不致仕》嘲讽的工具,是七十岁却不肯退休,贪恋权贵的老头目。他们究竟是怎么一副丑态,白居易津津有味地描摹道:
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
挂冠顾翠緌,悬车惜朱轮。
金章腰不胜,伛偻入君门。
谁不爱富贵?谁不恋君恩?
“贪名利”、“忧子孙”、“爱富贵”与“恋君恩”,是这种人的真实写照。
白居易这首诗歌所指的是谁呢?答案恐怕就在《不致仕》的自序中,据白居易诗前的自序:
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
贞元、元和都是天子的年号,白居易的自序,说的是他当时在长安,见到一个贪恋权力的老头目。
不妨转头再看《旧唐书·杜佑传》的记载。杜佑,“贞元十九年入朝,拜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充太清宫使”、“元和元年,册拜司徒、同平章事,封岐国公。”……
对付这些官吏名字,诸位可以不用理会,大家明白的是,元和元年(即公元806年),杜佑是刚好七十岁的老人,人过七十古来稀,却依然当着大官。显而易见,白居易在长安所见之人,该当正是杜佑。
据《旧唐书》的先容,晚年的杜佑,“每与公卿宴集其间,广陈妓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常常与公卿王侯,在园子里宴饮聚会,还豢养了很多歌妓乐工。
将正史中的记录,放还进《不致仕》中,竟然绝不违和,白居易究竟说的是谁,该当毫无疑问了吧。
杜佑年事大了,当然不愿与别人论短长,其孙儿杜牧,就另当别论了。
04
杜牧曾经作过一篇叫《献诗启》的文章,个中言及自己的诗歌态度,用了如下字眼:
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绮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
杜牧追求“高绝”诗风,他所唯恐避之不及的写诗手腕,即“涉习俗”,不用细想,暗指的便是白居易和元稹的“元和体”。
如果说这段批评,还算是藏着掖着,杜牧之后的批评,则可以称得上是动真刀真枪了。
话说,杜牧有个叫李戡的好友,不幸因病去世,杜牧在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吹响了向白居易进攻的决斗号角:
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鲜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毁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授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撤除。
白居易于元和年间作《不致仕》,杜牧则针锋相对,说从元和年间起,他是如何伤风败俗的。
杜牧一起笔即是不尊重,白居易与元稹再怎么说也算其前辈,他直接称呼人家为“诗者”,两人的“淫言媟语”,引诱民气,到了令人无可忍受的地步。
对付如此行为,到底该如何处理?杜牧之后又恶狠狠地写道:“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他的意思是说,也便是我没有昔时夜官,否则索性法办了他们两个。
说回白居易和杜牧怼人的诗篇,有一说一,他们为了贬损对方,乃至有些不择手段了。
譬如,白居易讽刺杜佑,年过七十还贪恋权位。但白居易该当也知道,据《旧唐书》的记载,杜佑三番五次的要求退休,怎奈天子不许可。
元和七年,77岁高龄的杜佑,已然得了病,他前后四次上表,言辞悲切至极,天子不得已才批准了他的退休要求。
六月份退休,不到半年的光景,杜佑就撒手人寰了。
试问,杜佑果真就想当官吗?恐怕也未必,人家三番五次地上奏,情真意切地请辞,白居易却一次也没有瞥见。
白居易在这厢选择性失落明,那边的杜牧呢,很高兴地骂元、白,却不幸把自己也捎带上了。
众所周知,杜牧有很多种类型的诗作传世,但他同样钟情于艳情诗,换言之,“淫言媟语”的数量,他写的一点都不少。
杜牧若是伤敌一千,那他末了也自损八百。
杜佑、白居易和杜牧,在年事之上,分别差距30多岁。对付小辈的还击,父老也表现出了应有的大度,杜佑既没有回应白居易,白居易也没有搭理杜牧。
他们之间的争吵,逐渐也便消逝在历史长河中,与墨客的绝美诗篇比较,这点小摩擦,其实算不上什么。
然而,墨客们互撕的时候,与平常人满口芬芳不同,人家从来不说脏字。要想体会他们口中的恶意,我们还要多读几本书,掰开揉碎了去剖析。
可见,不管任何时候,多读书总是没有坏处的。
参考资料:
1,卞孝萱、刘维治:《杜牧为何诋諆元白诗》
2,丁启阵:《杜牧为何鄙视白居易》
3,李珺平:《如何理解杜牧批评元白诗的内在隐衷》
4,刘昫等:《旧唐书》
-作者-
老谈,always talk,总是夸夸其谈之人,除此外,别无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