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人类从自然界的丛林走入钢筋混凝土的丛林,舍弃了很多野性,可以说与自然界的其他生物们渐行渐远,但纵不雅观数千年来的文明进程,我们的衣物、食品、住所、交通、医疗,实在都离不开两位“朋友”——动物和植物。正由于人类长久以来都必须跟这两位朋友打交道,以是面对动物和植物,人类不只会直接拿来运用,也会在动植物身上倾注自身的审美情绪。在中国,人们抒发这种审美情绪的主要路子,便是创作诗词,对动植物进行歌咏。
从《诗经》时期的生态记录,到唐诗、宋词的浪漫抒怀,那些我们以为冷冰冰的动植物名词,一贯在古人的心尖上翩翩起舞。石润宏博士所著的《古诗词里的动物植物》(中华书局2021年版)一书,正是对上述环境的勾勒与阐释。近年来,石博士一贯致力于探索中国古代文学的植物天下,这一次,在他的笔下,给我们描述了一个超过数千年的充满各种非凡动植物的诗词天下。从野生动物到圈养动物、神话动物,从不雅观赏花卉到农业作物、药用植物,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每一种动植物,都充满了科学知识与审美遐想,等待我们去寻觅它们背后那些令人称奇的故事。
阅读本书,你可以在欣赏经典诗词的同时,理解到很多有趣的博物学知识。例如,现在正值夏季,我们在不少地方都能见到辛弃疾笔下“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喷鼻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场景。那是宋代的一个夏夜,辛弃疾经由黄沙岭,走动的声响惊起了树上的鸟鹊,但蝉不受影响,依旧叫个一直,水稻正在抽穗,稻田里传来田鸡的叫声,辛弃疾不禁想到,今年的粮食该当可以丰收了吧。这首词描写的内容虽然止步于此,但一些热爱思考的朋友们大概会冒出持续串问题:人走动的声响吓走了鸟鹊,可为什么蝉和田鸡不受影响,依旧叫个一直?“蛙声一片”为什么会预示着“丰年”?要回答这些问题,仅仅理解文学作品本身是不足的,还须要懂一点博物学知识。
本书见告我们,蝉的发音器是腹部的腹瓣构造,而且这种构造只有成熟的雄蝉才有,雄蝉腹部的第一节内部有一套完备的发音组织,由鼓膜和共鸣腔等构成,雄蝉的肌肉可以驱动它们进行高频率振动,因此小小的身体能发出很大的声音。而能叫的田鸡也都是成年雄蛙,它们的咽喉部长有两个内声囊,通过呼吸让声囊振动,就能发出很洪亮的声音。蝉和田鸡鸣叫有一个相同目的,便是警告其他动物不要靠近自己的领地,以是辛弃疾的脚步声惊走了鸟儿,却吓不到蝉和田鸡。田鸡栖息在稻田里,会捕食各种害虫,堪称水稻康健发展的守护者,以是田鸡叫声越大,意味着种群数量越多,稻田里的害虫就越少,水稻也就丰收在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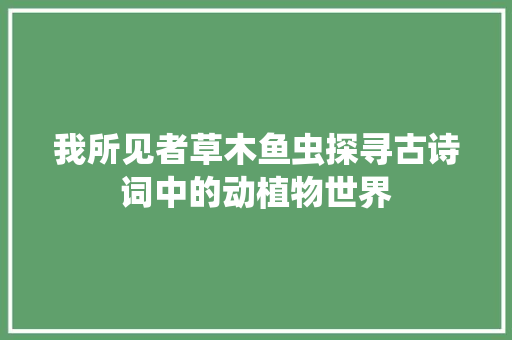
再比如,古人到了秋季的重阳节,会登高望远、饮酒赋诗,还会在头发上佩戴茱萸,王维诗“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说的便是这样的场景。那么,茱萸究竟是什么样的植物?古人为什么要头插茱萸?插茱萸怎么就成了重阳节的民俗呢?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同样须要透过诗歌文本,借助笔墨以外的博物学知识来解答。本书先容说,茱萸是山茱萸科、山茱萸属好几种落叶乔木、灌木的通称,它的叶片有喷鼻香气,开伞形小黄花,果实成熟后呈赤色椭圆形,可以入药。茱萸原来是自然界无数栽种物里不起眼的一种,后来由于自身的药用代价,而被我们的先民把稳到。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医书之一《神农本草经》就已记录了“山茱萸”的特性,后来李时珍在《本草大纲》中说茱萸肉有“久服轻身”“除统统风,逐一切气”等妙效。以是古时候民间认为茱萸能够辟邪,古人不只佩戴茱萸,也用茱萸来泡酒喝。而插戴茱萸跟玄月九日重阳节联系起来,后来演化成一种民俗,则是与东汉的一位术士费长房有关,古书《续齐谐记》里有记载。
像这样普通易懂的知识、引人入胜的故事,在《古诗词里的动物植物》一书中比比皆是。本书共涉及29种动物、41栽种物,作者用灵动活泼的措辞,先容了很多非常故意思的征象,如我们是何时开始吃桃子的,鸡的翱翔能力是如何退化的,杜鹃为什么把蛋下在其他鸟类的巢里,等等。当然在这些花草鱼虫的背后,我们还可以读出纯洁炽热的爱恋、羁旅他乡的客愁以及壮志难酬的无奈……
法国历史文化学派的奠基者丹纳(Taine)曾说:“美学本身便是一种实用植物学。”本书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对一个个具象的描述和先容,更多的是让我们领略诗词背后所蕴含的美的天下,阐发中国传统文化中美的内涵。天下本不短缺美,而是短缺创造美的眼睛,打开这本书,相信你会开启一段别样的美的旅程!
(本文作者系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