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市人有喝早酒的习气。街头巷尾的早点铺,除了供应大连面中连面早堂面之外,一样平常都备有一些下酒菜:烧牛排、烧牛筋、烧牛尾,卤喷鼻香干,卤鸡蛋,卤肥肠;羊杂汤、牛杂汤、海带汤,冬笋煨牛肉、黄豆煨猪爪。用铁盆或瓦罐盛着,放在煤炉炖着。见老主顾们提着酒瓶上门了,老板一边安排桌椅,一边激情亲切地张罗:“还是来一碗儿牛筋?”“刚出锅的肥肠,给您切一碟儿?”老哥儿几个把酒倒进杯子,菜也上桌了,于是端起羽觞,作势碰碰,抿一口酒,吃一口菜,扯几句闲话,惬意的一天就这么开始了。
当然,像这样过早,是须要一定的经济实力的。较之于周边几个城市,沙市的早点算便宜的,但这样一顿早酒下来,怎么也得三五十块吧。如果你囊中羞涩,而又好一口早酒,那也无妨,花两块钱买几块卤喷鼻香干或者干脆夹一碟不要钱的泡萝卜泡蒜须也可以下酒了。而老板并不因你费钱少而薄待你。
因此,在沙市,喝早酒可谓是蔚然成风。不过,近几年来,这一习俗饱受诟病——不仅由于这有违“莫饮卯时酒、莫骂酉时妻”的古训,还由于这座城市的没落——有人乃至将之归罪于喝早酒的习俗上来,认为是早酒导致了沙市人不思进取。这当然是很牵强的,一个很大略的道理便是:在沙市走向壮盛成为全国有名的明星城市之前,沙市人也是喝早酒的。
我没有考证过沙市人喝早酒的习俗形成于何年何月,但我预测,它的形成,该当与其地理位置有着一定的联系。沙市,春秋时名曰江津。唐时,更名为沙头市。津者,水渡也。市者,买卖所从之也。从这两个名字可知春秋之时这里已是楚之要津,唐、宋往后,已成巨镇;至晚清时,中日《马关条约》又将之增辟为通商口岸。由此可见,沙市自古以来便是长江中游举足轻重的商业港口,而所滞留者,显然亦多为坐贾行商、贩夫走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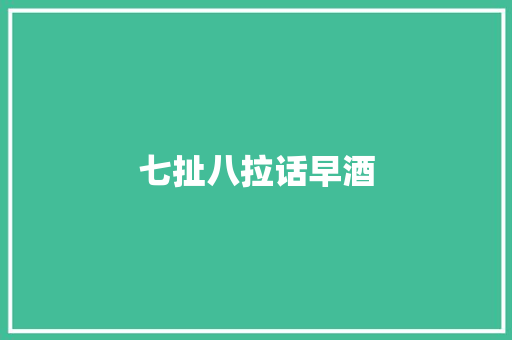
遥想某个隆冬的清晨,一个头戴破毡帽身裹百衲衣的挑夫,惺忪着双眼走出家门,照例去岸边卸货,以此来换取一家人的口粮。然而,当他哆抖动嗦地来到码头,船却还未到岸。于是蹩进小酒栈里,赊一碗老酒囫囵喝下,一来暖暖身子,二来也给自己提提劲。久而久之,即成习气。推而广之,则成习俗。
大概,同样是在一个薄寒的清晨,同样是在这个码头,来此做生意多年的殷商,忽逢捎来家书的故人。欲延故人入宅,细问故宅之梅,奈何归期已定,舟楫将行,于是只得借此酒栈,找一倚窗临江的酒桌坐下,备几碟小菜,温一壶老酒,长话短说,聊以抚慰乡愁之苦。
当然,这都只是我无端的预测。不过,喝早酒这一习俗,确实是古已有之。唐代墨客白居易便是一位酷爱喝早酒之人,他有一首诗,题曰《卯饮》,专门赞颂喝早酒的好处:
短屏风掩卧床头,乌帽青毡白毳裘。卯饮一杯眠一觉,世间何事不悠悠?
喝点早酒,睡个回笼觉,无丝竹之乱耳,无文案之劳形,此等逍遥清闲的生活状态确实让我等眼馋。而他的另一首《卯时酒》,更是将早酒吹捧成了神效无比的愉快剂。诗曰:
佛法赞醍醐,仙方夸沆瀣。未如卯时酒,神速功力倍。一杯置掌上,三咽入腹内。煦若春贯肠,暄如日炙背。岂独肢体畅,仍加志气大。当时遗形骸,竟日忘冠带。似游华胥国,疑反混元代。一性既完备,万机皆破碎……
而自言“不可一日无此君”并放言要“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的东坡居士,同样也是一个早酒爱好者。一百十五卷的《东坡全集》,每一页都散发着浓浓的酒喷鼻香。描述早酒的诗句,自然是时有所见。比如:“卯酒困三杯,午餐便一肉”、“三杯卯酒人径醉,一枕春睡日亭午”等等。在《和陶与殷晋安别》一诗中,他乃至号称自己“卯酒无虚日,夜棋有达晨。小瓮多自酿,一瓢时见分。仍将对床梦,伴我五更春。”
“卯酒无虚日”恐怕有点夸年夜,“小瓮多自酿”该当是实话实说。作为一个极品醉翁,东坡不仅好饮酒,也好自己动手酿酒。听说,他贬居黄州期间,西蜀羽士杨世昌,也便是后来与东坡同游赤壁,并于舟中吹洞箫者,云游庐山后又专程到黄州看望东坡。故人来访,岂能无酒。在接风酒宴上,东坡特意呈上一杯自酿的黄封,没料到杨羽士喝过之后,竟然涕泪长流!
东坡大为冲动,于是奉上第二杯,却把杨羽士吓得赶紧捂鼻掩口——原来,方才他之以是涕流满面,并非为东坡之盛情所动,而是由于那酒实在是涩如马尿,不堪入口!
杨羽士只得将私藏多年的酿酒秘笈倾囊相授。得此秘笈,东坡果真酒艺大进,不仅如法炮制出了“蜜酒”,还创造性地酿出了“松酒”、“桂酒”、“真一酒”,并凭借一篇《东坡酒经》晋升为一代酿酒大师。
不过,按东坡的《蜜酒法》及《东坡酒经》所述的工艺判断,他所酿所饮,并非当今蒸馏法酿造的白酒,而是传统发酵工艺酿制的酒,类似于黄酒、米酒。曹孟德刘玄德论英雄时煮的是这种酒,让李太白天子唤来不上船的,也是这种酒,武二郎景阳冈前喝的,还是这种酒……在动手写这篇短文之前,我也喝了一大碗……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