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期的官僚系统编制本身就很腐败了,再加上这等天灾,可谓天要亡大明,从万历至崇祯年间发生的蝗灾是明朝历史上的高峰期。
明朝初期也曾遭受过一些蝗灾,不过规模与社会影响力均远不及明朝末年,个中北方的蝗灾比南方更为严重,而北方浩瀚地区又以中原地区为重灾区!
开封府作为中国古代中原地区的核心经济带,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北宋期间被誉为天下第一府,《东京梦华录》记录了当时的繁华,这片地皮创造了令后世为之敬仰的文化艺术。
但鲜有人知的是开封府,也是一个蝗灾多发的地区,千百年这片地皮上的百姓,不知因小小的蝗虫而遭受了多少的人间惨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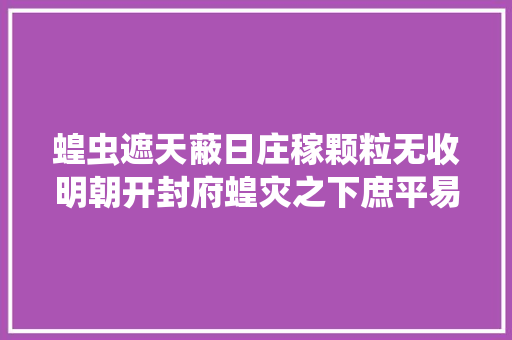
本日笔者就以明朝期间的开封府为一个窗口,浅谈一下蝗灾之下的中国古代百姓的真实生存状态,不正之处望诸君指出。
蝗灾所造成的的人间惨状,究竟有多胆怯
据开封府地方县志记载:
“嘉靖十九年钧州新郑密县皆蝗,食禾稼草木俱尽,所至蔽日,碍人马不能行,填坑堑皆盈,饥民捕蝗以为食,或曝干而积至,又罄,则人相食。”
看着满天的蝗虫,开封新郑密县的灾民都以蝗虫为食品,吃完蝗虫,无食果腹,就涌现了吃人肉的惨状,说到这里有的朋友或许会迷惑。
既然灾民可以吃蝗虫,那么蝗虫也不至于成灾吧,毕竟没有什么东西是中国公民办理不了的,实则非也!
蝗虫虽然可以吃,乃至现在某些地方都有吃蝗虫这道地方特色菜,但如果遮天蔽日的蝗虫从头顶飞过,足以对农业生产造成不可逆转的毁灭!
打个最浅近的比方,当蝗虫吃了一斤的麦苗时,农人丢失的不是一斤麦苗,而是这一斤麦苗完备成熟后的五斤粮食,相称于农业生产的进程被蝗虫冲破了。
尤其每当旱灾过后,蝗虫每每会大量涌现,扑打、网捕、效果都不是很明显,在蝗灾发生的初期,人们或许还能靠着存粮或捕捉蝗虫为食品。
可当粮食吃光了,蝗虫也吃完了的时候,人们就只能吃树皮了,乃至吃不雅观音土的都有,大批大批的百姓被饿去世,路上尸体到处都是。
有力气的往外迁徙,到别处找条活路,寻口吃的,没力气走不动的,直接就倒下了,沦为豺狼乃至差错的食品。
这时候别说有没有蝗虫吃了,只假如活物,除了人之外,基本都是拿来吃的,至于什么吃耗子肉、吃田蛙肉,那都是极其幸运的了,放眼望去四周一片光秃秃的,大夏天的就跟快要入冬似的,除了黄土,没有一点颜色!
蝗灾直接浸染于农人的庄稼粮食,粮食欠收所造成的饥荒,才是真正的恐怖之处!
如果饥荒严重时,尸行遍野,会进一步导致瘟疫,对付全体国家的发展都是毁灭性打击,明朝的覆灭就有这一方面的成分。
嘉靖、万历、崇祯三朝——开封府蝗灾的高发期
明朝嘉靖年间发生的蝗灾,是明朝自建国以来较为严重的,旱灾、蝗灾交替进行,山东、河南、山西皆受蝗灾。
当时的百姓称嘉靖一朝是“家家皆净”,嘉靖在位46年,开封府发生蝗灾的年份有19次。
万历期间的情形与嘉靖差不多,万历在位48年,开封府发生蝗灾19次,个中崇祯在位时,开封府的蝗灾,直接达到历史最高峰!
虽然崇祯在位只有17年,开封府发生蝗灾的年次只有10次,但崇祯期间的蝗灾比万历和嘉靖期间都要严重得多!
开封府发生蝗灾的县次数量,从嘉靖期间的62次、万历期间的70次,直接飙升到了崇祯期间的95次,这里的县次意为一个县发生一次蝗灾,这样统计的。
明朝期间,开封府下属30多个县,发生蝗灾县次却在60多次,乃至90多次,这解释有些县区是反复多次发生蝗灾的。
尤其是崇祯期间,加上当时的瘟疫盛行,旱灾后蝗灾、蝗灾后瘟疫,地方政府运转陷入瘫痪,再加上明朝末年的官僚的腐败,中心对地方也逐渐失落去了有效的掌握力!
明朝初期虽有蝗灾发生,但也不至于如此大规模,开封府的蝗灾之以是在明朝中后期,成为动摇地方统治的根基,其缘故原由有二。
一是景象的影响,明朝中后期环球景象转入小冰期,水点都结成冰块封起来了,海陆水循环自然也就放缓了。
雨水不敷导致各地涌现大面积的干旱,干旱过后的土壤,特殊适宜蝗虫卵的孵化,大旱生蝗灾,民不聊生。
二是明朝官僚系统编制自身的腐败,明朝自土木堡之变后,便开始走下坡路,文官集团拉帮结派,宦官专权弄政,中心与地方的监察系统编制大大失落效,官僚阶级对百姓的剥削,日甚一日!
在大旱、蝗灾来临时,地方政府对付百姓的剥削,无异于伤口撒盐。明朝崇祯末年的朝政腐败是众所周知的,加之要对付北方的游牧民族威胁,军费开支巨大。
不得不对百姓加大了税收力度,当时的百姓称崇祯一朝为“重征”,当蝗灾发生时,中心朝廷都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哪还有心思管那些被蝗虫侵扰的百姓。
明政府末期的天灾不是王朝覆灭的挡箭牌,开封府的百姓忍饥受饿,也不完备是天灾,地方政府的剥削,朝廷的不当举措,都是一场场蝗灾反复发生的催化剂。
一场天灾每每是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客不雅观标准,平时无论当局政府如何吹嘘太平盛世,可当真正的灾害来临时,政府的各种无脑操作,官僚系统编制的贪腐,都会暴露无遗。
这一条考验执政标准的铁律,适用于任何时期、任何国家、任何政党,在担保政局足够清明的情形下,也要从根源办理蝗灾问题,从科学管理的角度入手。
景象特色、地理环境、农作物构造,开封府蝗灾的三大诱因
明朝开封府之以是随意马虎发生蝗灾,缘故原由有三。一是当地的农业构造,刚好迎合东亚飞蝗的胃口,玉米、小麦、高粱、稷等禾本科植物,都是东亚飞蝗非常喜好的食品。
二是开封府辖区内,河网密布,其流经水量大多有雨水补给,但随着明朝中后期环球小冰期的来临,海陆水循环受到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像开封府这种大陆性季风气候,受到的影响更大。
以是每当旱灾或洪灾过后,河床上极随意马虎形成浅滩荒地,这些浅滩荒地正好又是沙秋科植物的最佳成长土壤。
大量的浅滩荒地不仅为东亚飞蝗的产卵供应了适宜的环境,浅滩上野蛮成长的沙秋科植物,也是东亚飞蝗喜好的食品。
三是开封府的大陆性季风气候,本身就随意马虎形成洪涝磨难,四季分明的景象特点便是汛期来临时,河道水位猛涨,汛期过后水位又极速低落,忽高忽低的水位很随意马虎形成浅滩荒地!
加之,上中游的黄河频繁改道,这就导致下贱的开封府内的河道更加不稳定,水位的极速变革致使农田被淹,大水过后便是一片大荒地,这些荒地成为了东亚飞蝗的天国!
据《明实录》记载:
洪武八年春正月,河决开封城;洪武二十年河溢,冲汴梁;崇祯十五年,河决开封;崇祯十六年秋玄月,河决入涡河。
开封府的农作物构造、景象特色、地理环境,三者均完备知足了东亚飞蝗的成长繁殖条件,在加上当时环球的小冰河景象影响,开封府的蝗灾就更加频繁了。
从开封府蝗灾的频繁发生中,聪慧的中国公民也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
一是兴修水利,这是从根源上减少蝗虫的产卵场所,只要河道不泛滥,浅滩荒地的少了,蝗虫的产卵场所就少了。
二是开拓荒地,如果已经形成了浅滩荒地,该当立马开垦,将“蝗地皮”变为“黄地皮”!
三是改变农作物构造,这一条实施起来难度比较大,由于中国各地的粮食作物基本上都是千百年来的总结,基本上已经是做到了地皮利用率的最优化。
也便是说这片地皮上,只能种这种作物,除非在改变作物构造的条件下还能实现经济收益的增长,不然一样平常情形下,是不会贸然改变其农业构造的,这个风险农人很难承担。
再说了,大规模的蝗灾也不是常常有,小量的蝗虫对付农作物的经济丢失,远低于改变农业构造所带来的丢失,因此“改变农业构造”以管理蝗虫的方法,可以认为是纸上谈兵,可行性不大。
四是积极保护有益生物,自然界的所有动物都是处于生态平衡的状态,蝗虫的克星大多是鸟类、蛙类、小型肉食昆虫。
因此保护晴天然的生态平衡,也相称于在抑制蝗虫的极度繁殖。
中国蝗灾的高发区一样平常是在山东、河南、河北,也便是黄河泛滥的紧张区域,还有便是蒙古草原地区。
由于黄河水的常常泛滥,造成了河道两岸极随意马虎形成大面积浅滩荒地,个中开封府的兴衰更是与黄河息息相关。
1938年蒋介石敕令炸毁河南黄河花园口,而开封府直辖下的大片区域正好便是位于黄河花园口下贱,滚滚的黄河之水泛滥成灾,给这片地皮上的百姓造成许多人间惨剧!
果不其然,就在黄河花园口被炸毁的第四年,河南爆发了1942大饥荒,这一年河南大旱,之前泛滥的黄河浅滩荒地,一下子就变成了蝗虫繁殖的温床。
大旱之后必有蝗灾,这句古话又被应验了,只是这次的蝗灾多多少少都有蒋委员长的任务,之前炸毁的黄河花园口,此时的副浸染凸显出来了。
蒋委员长当时的饮鸩止渴,在现在看来无异于拿百姓的生存去堵日军的枪口。
卖草席出身的刘备大军撤退时,尚且知道要带着百姓一起走,自称文章天下第一的蒋委员长却不知道!
与明朝崇祯末年发生的饥荒一样,国民政府在处理河南饥荒上,也是存在官僚贪污腐败的情形,使得本来就糟糕的灾情,又进一步扩大!
崇祯期间是内忧外祸,国民政府期间也是内忧外祸,二者处理大旱饥荒时的表现,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历史的车轮在这一刻又转回了原点,开封地区的百姓又遭受了一次人间惨剧。
结语: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和政府对付农业的生产是极为重视的,针对付我国的蝗虫泛滥重灾区,即黄河泛滥区域、蒙古草原区域,我首都设置了大大小小的蝗虫监控指挥部。
时候监控蝗虫的种群数量,当发生蝗灾时,就立马叮嘱消磨飞机喷洒特制的蝗虫农药,以达到杀蝗而不伤农的效果。
在党和政府的英明管理下,曾经泛滥的黄河水也变成了真正的生命之水。
开封府地区的百姓又重新过上了相对安稳的日子,如今的河南开封已经是中国中原文明的象征,各种古建筑和文化祠堂悄悄诉说着“天下第一府”曾经的光彩。
现今的开封已是全国著名的文化旅游名城,是河南浩瀚文化名片中的一张,这片地皮上的百姓有着坚韧的品性,他们降服了旱灾、消灭了蝗灾,传承着五千年的文化血脉。
参考文献:
《中国飞蝗生物学》
《河南蝗虫磨难史》
《明史》
《明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