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谈,来源:唐诗宋词古诗词(ID:tsgsc8)
双面帝王
在亚洲人的文化认知中,政治向来与女性绝缘。偌大的中国地,五千年华阴历史进程,涉足政治的女性,本来就屈指可数,更不消说,还能取得令男人侧目的政绩。
这样的奇女子,真的算是罕有物种,武则天是个中最出名的那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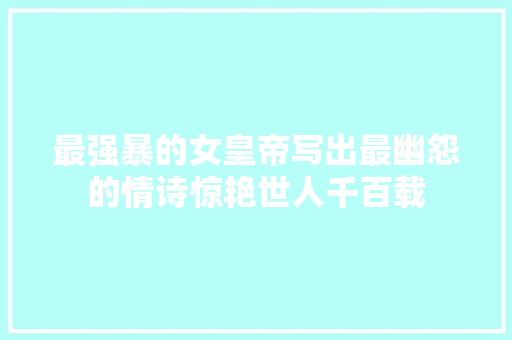
武则天出生于唐朝,唐朝是墨客荟萃的年代,武则天执政50余年,政绩颇佳,著述却不多,存诗仅有46首。
在笔者心目中,她最出名的诗歌,共计有两首。第一首诗歌颇为霸道,武则天实在因此诗歌的形式书写诏书,诗歌名曰《催花诗》:
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
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
诗歌简洁明快,却带着说一不二的爽利,武则天准备腊日赏花,她于是向百花下了一道命令,命它们连夜齐放。这首小诗洋溢着女皇的气度,其凛凛神威,令人不寒而栗。
武则天的另一首代表诗歌,却带着小女子的娇俏、忐忑、调皮与幽怨:
看朱成碧思纷纭,干瘪支离为忆君。
不信最近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从文本来看,这首《快意娘》,确然是情诗无疑。
很难想象,一个君临天下,执掌江山的铁腕人物,竟能写出如此的儿女情长。大概,哪怕是最凛冽的女子,也有一颗薄弱的、敏感的、追求爱情的本心。
这首诗歌,也是武则天唯一一首爱情诗。笔者斗胆揣摩女皇的心思,如果可以选择,在这首《快意娘》之前,她或许更乐意冠以“媚娘”的名字;至于那首《催花诗》的冠名作者,她则钟意于霸气的“武瞾”吧。
看朱成碧
《快意娘》之诗,用词朴实,也没有利用生僻字眼,读之却觉缠绵悱恻,低回宛转,有情思入骨之感。
武则天主业治国,作诗更像是任性而为,任性的行为,不经意间带出优雅,又无意中影响到当时最卓绝的墨客。
诗歌首句有“看朱成碧”之语,对付这四个字,历来有两种解读。
第一种说法是,诗作的主人公,痴心思念情人,痴心到神态不清的地步,竟然分辨不出碧绿和朱红的颜色差异。
第二种解读更为可怜,娇弱而断交的女子,等待着情郎的到来,她倚门凝望,望眼欲穿,从红花盼到绿叶,容颜都凋零了,那人却还是没有涌现。
“看朱成碧”之语,实在并非武则天原创。早在南朝之时,有一个叫王僧儒的墨客,曾经作《夜愁示诸宾诗》,个中有如下几句:
万行朝泪泻,千里夜愁积。
孤帐闭不开,寒膏尽复益。
谁知心眼乱,看朱忽成碧。
王僧儒其人,出生于没落的士族家庭,幼年的他活得很辛劳,王僧儒绝不气馁,发奋读书,他终于学有所成,出仕为官。
但颇惋惜的是,王僧儒之后又为人排斥,后半生过得极是萧索。
对付有城府的名流而言,愁苦是不应轻易示人的。在夜宴之上,王僧孺竟然将自己的愁绪,毫无遮拦地向宾朋展示。
个人以为,武则天对王诗的化用,到了“润物细无声”的地步,她以四字起底,却达到以少胜多的境界。
武则天在首句末端,还注明红绿不分的缘故原由,皆是由于思绪纷纭,思念成疾。
经由武则天的手笔,“看朱成碧”逐渐蜕变成,唐宋墨客惯用的针言。
譬如,大名鼎鼎的李太白,便有诗云:
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
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
而宋代的辛弃疾,亦在词中写道:
倚栏看碧成朱,等闲褪了喷鼻香袍粉。
上林高选,匆匆又换,紫云衣润。
哪怕不写诗词,稼轩也是绘画的高手,寥寥数笔,即把碧、朱、金、紫诸色,安排得妥当而融洽。
武则天作品虽少,却不乏峥嵘手笔,《快意娘》即是最好的例证。诗词不会说谎,后世的文人也不会说谎。更不用说,直至本日,我们仍旧将“看朱成碧”写进了歌词。
台湾歌手金佩珊的代表作《一代女皇》,个中即有对《快意娘》的隔空致敬:
“问情何寄泪湿石榴裙,看朱成碧痴情无时尽。纵横天下二十年,深宫迷离听凭添……”
石榴之谜
石榴裙是件妖娆的物事,它让女子俏丽,让男人臣服。“跪倒在石榴裙下”,又带着多少暧昧与诱惑。
何谓“石榴裙”?要说清“石榴裙”,首先要言明石榴的来历与传说。
听说,离中国万里之遥,有一个叫作“安石国”的小邦。某日安石国王子外出打猎,在山林中救起一只将要冻去世的金翅鸟。
金翅鸟为报答王子,不远万里飞回骊山,觅得一颗女娲补天遗落的红宝石,鸟儿又将宝石,衔送至王子的御花园内。
不久之后,花园长出一株花红叶茂的奇树,安石国王因此赐其名曰“安石榴”。
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一起跌跌撞撞行至安石国。彼时的安石海内正逢干旱,张骞来自大汉上国,也懂得兴修水利之法,他略施援手,竟然就救活了安石的子民。
临别之时,国王赠予给他很多石榴种子,张骞将其带回,石榴因此在骊山和长安的上林苑,成长繁衍开来。
这则故事被晋朝学者张华,记录在他的博物学著述《博物志》中,这本书带有神话志怪小说的性子,但传说却平添了一抹俏丽。
唐代墨客元稹,洋洋洒洒作《感石榴二十韵》,开篇即解释石榴之来历:
何年安石国,万里贡榴花。
迢递河源道,因依汉使槎。
至于“石榴裙”的典故,出自于梁元帝《乌栖曲》中的名句:
交龙成锦斗凤纹,芙蓉为带石榴裙。
日下城南两相望,月没参横掩罗帐。
经由梁元帝萧绎妙手演绎,“石榴裙”便也成为流传千载的衣饰格局。
如传说所言,石榴为赤色,而古代女子爱穿裙子,尤其钟爱石榴赤色,染制红裙的颜料,恰好取材自石榴花,这是“石榴裙”的另一个来源。
由于石榴多籽,古人谓之“千房同膜,千子如一”。古代女子着“石榴裙”,是否暗含着“多生子”的隐喻?这是笔者的个人不雅观点,是非对错还有待商榷。
说回武则天之诗,她在末了凄然说道:“如果不相信我为您流过多少泪,请开箱翻验石榴裙上的斑斑泪痕。”
武则天以铁一样平常的事实——红裙上的斑驳泪渍,表达了自己思情之强烈,痛楚之深奥深厚。
深奥深厚中却看不到卑微,这是女皇的自傲与肃静,她恨不得将情郎拽到面前,逼迫他去翻看、验收。
《越人歌》中的相思是卑微的,偷摸摸地喜好,不求对方知道,正所谓“心说君兮君不知。”
另一首远古情歌《有所思》,它的相思太过生猛刚强。诗歌中吟唱道,“闻君有贰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读罢,令人不寒而栗。
武则天将尺寸拿捏地恰到好处,不卑不亢,有理有据。
韶光疑云
众人皆知,武则天本是唐太宗的秀士,太宗去世后,她被安置到感业寺作尼姑。
武则天的残生,本该与青灯古卷相伴,但她从来都不是循分的女子,太宗还在世时,就已和太宗之子发生情愫。
人们因此断定,此诗作于武则天深居感业寺之时,由于思念郎君,万分伤感,末了便作了此诗。
武则天在寺庙已是一名缁衣尼姑,她如何能穿着或者保留石榴裙?就算悄然保留下来,也该压在箱底才是。但如诗中所言,武则天却是常常拿出,擦拭眼泪的。
这切实其实是不合逻辑嘛。
武则天曾经以“快意”作为年号,有些学者根据诗名推断出,此诗大概作于快意(692)年间。
问题是,彼时的武则天,已经是69岁的垂垂老者,石榴裙则是青年女性的盛行衣饰,她身居高位,该当不至于穿着华美的赤色。
历史学者有时候也要充当侦查的角色,他们用最笨的办法,将此诗套进武则天的不同生活经历,然后逐一打消。
譬如,有的学者考证出,此诗作于唐太宗去世后,武则天出宫为尼前,那段稍纵即逝的韶光段内,她抓紧韶光作此诗,是为了挑逗挽回太子李治。
伟大的爱情都是短暂的,工于心计的武则天当然要把握机会,任何一个女人都不敢担保,信誓旦旦和你山盟海誓的那个男人,永久不会变心,更何况天子乎。
类似的阐明和推理,严明中透露出俏皮,令人忍俊不禁。笔者也只能感叹,研讨历史的学者,除了通读经史子集,还要熟习生理学,真是难为他们了。
而所有辩论的起源,皆是在于,武则天本人便是个充满争议的天子。
武则天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女天子,换言之,她是一个异类,奇迹上愈发功名造诣,众人对她的误解就更加深刻。
持续的误解,反过来又催生出充满争议的武则天。
历史有时候也颇为有趣,武则天的丈夫叫李治,明朝又出了个李贽。李贽的名字发音,与武则天之夫相同;李贽的性情,又与武则天类似,他们都是“异端”。
封建社会里,史学家众口铄金批驳武则天为“篡政”,李贽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为武则天唱赞歌曰:“胜高宗十倍、中宗万倍。”
你说,诗的争议,人的争议,何时会有个尽头,又到底谁对谁错呢?
注:关于武则天《快意娘》创作韶光的不同说法,分别引用自
1,司海迪《武则天情诗<快意娘>写作韶光探析》
2,董灵超《关于武则天<快意娘>释义的磋商》
3,路荣《武则天诗歌研究》
-作者-
老谈,always talk,总是夸夸其谈之人,除此外,别无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