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不但在现实生活中颇受人喜好,更是尽情绽放在文人墨客笔下的字里行间,凝聚着文人特有的审美情绪。
桃花光鲜的外在特色,引发了三次文学关联,打破了花卉本物的生物性描写,创造了三个桃花的全新意象。授予桃花深厚的文化内涵,使之成为后世文学一主要题材。
桃花美人
早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涌现了有关桃花的描述,流传于后世。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千万枝怒放的桃花,色彩明艳到极致,热烈逼人。这位姑娘要出嫁了,春风得意去往夫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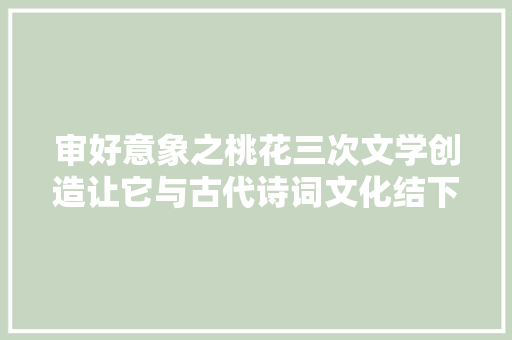
本来没有什么联系的桃花与新嫁娘,在这首诗歌中通过“比”与“兴”的创作方法,产生了极大的关联。直教人分不清,这夺人眼球的究竟是盛开得张扬热烈的桃花,还是那艳如桃花的女子。
此诗先以桃花起兴,借以遐想,引起所吟咏的真正工具【新娘】与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赞歌与祝愿。同时,“兴”中有“比”,以【明艳的桃花】比喻【俏丽的新娘】,贴合“景”、“事”、“情”,使新娘娇艳美好的形象深入民气。
自这一次关联创造,桃花便与女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清代文人姚际恒在其撰写的《诗经通论》中评论《桃夭》:
桃花色最艳,故以取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
的确,桃花花色妍丽,就彷佛女子含羞带涩时绯红的两颊。桃花绽放的饱满娇态,也随意马虎让人遐想到姝丽(美女)青春姣美的身姿体态。
不得不说,这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创造,它的核心是桃花与美人。然而,时期与创作者独特的情绪,又授予了美人不同的内涵。
《国风·周南·桃夭》中的桃花美人,青春康健,容颜姣美,更有着美好的内在品质——“宜”。后世诗词大量采取桃花来比喻女子的仙颜。
发展到后来的艳俗指向,桃花美人还暗指浓妆艳抹的风月女子,否定了内在人格。如:“南陌青楼十二重,东风桃李为谁容”。
又由于桃花的时令性特色,“寿之极短者莫过于桃”,又指代薄命的红颜,一如曹公《红楼梦》中的黛玉。同时也用凋落飘零象征红颜易老,美人迟暮。
桃花爱情朱熹的“桃之有华(“华”通“花”),正婚姻之时也”,大概与《周礼·地宫·媒氏》有关——
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
桃花盛开的仲春,正是男女谈情说爱的时节。此时桃花与恋爱婚姻已经有所联系。
当然,笔者认为桃花作为爱情象征的内涵,也是从《诗经·桃夭》篇衍生出去的,由女子衍生至爱情意象。
将桃花与爱情的关联推至高坛的,是唐朝才子崔护诗中,暗藏的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这一段“桃花缘”,还概括出一个针言『人面桃花』,成为女子和爱情的代名词。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东风。
——《题都城南庄》
整首诗,用“人面”、“桃花”作为贯穿“去年”和“今日”的线索,回顾一段露水情缘。短暂的爱情,一瞬间的美好,仍旧值得回味。
去年,南庄桃花盛开,偶遇一位艳若桃花的女子。在残酷桃花的映衬下更是人比花娇,主人公一见钟情,神思摇荡。
时至今日,同样的韶光,同样的地点,同样桃花含笑,却唯独没有了去年重逢的“桃花美人”,无限怅惘。
桃花带来的美感体验,融入了爱情故事,超出了个人体验,代表着诗化的追寻。众人都神往一份美好的爱情,历代文人将这份神往寄托在春日盛放的桃花上,创造出更深远的文化审美内涵。
桃花源
这第三次的创造,不得不提一位田园墨客,也是中国第一位田园墨客。是的,他便是“五柳师长西席”陶渊明。
提起陶渊明,也不得不提他的代表作之一《桃花源记》。笔者还记得这是初中必备的文言文,至今影象犹新。
地皮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这是陶渊明描述的内心的空想天下。这里与世隔绝,人与人之间和蔼相处,百姓安居乐业,怡然自得。没有兵荒马乱,没有尔虞我诈,隔离着世俗统统污浊阴郁的侵扰。
现实社会中的陶渊明,不愿与世俗与世浮沉,末了回到了他的田园,“采菊东篱下”,从来没有转头。
“古今隐逸墨客之宗”构建的这个“乌托邦”,植根于中国文民气灵深处。这种空想达到了一种审美共识,后世许多文人都借用“桃花”这一意象,来表达自己对付空想天下的追求。
例如王维的《桃源行》,唐寅的《桃花庵歌》,张旭的《桃花溪》……桃花源意象的不断衍生和丰富,实在便是思想文化上的传承与创造,具有永恒的魅力。
三次文学创造,使桃花本体的原始物象,逐渐发展与丰富,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中不可忽略的审美意象之一。花谢花开自有时,不变的是桃花成为了一种经典的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