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作为一种独特符号,是各种信息的浓缩载体,蕴含知名贵的历史资料。一个地名的出身,每每把人文、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文化成分席卷个中。以是,地名既能表现当地风貌,也能印证当年历史,是历史发展长河中代表社会特色、记载人文风情无法替代的活化石。
地名盩厔,一枝独秀,将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自然景不雅观和谐结合,有迹可寻,内涵丰富,耐人寻味。因此,关于周至(盩厔)县名的来历,近年来引发了不少学子的探究研讨,大家乐此不疲,成果斐然。
众所周知:周至县,旧作盩厔县,建于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当时,官吏们虽知地名“盩厔”,但却史料缺失落,未见名由。直到大唐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时,才有宰相李吉甫根据盩厔县详细的山川形势,推测剖析,撰有《元和郡县图志》一书,在卷二中首解‘盩厔’之义为“山曲曰盩,水曲曰厔”,义即:盩厔县名源于本地山环水绕的自然地理景不雅观。
此不雅观点补充了盩厔县名阐明的多年空缺,对宋、元、明、清的许多古籍皆产生过重大影响,被一些传世文献相互引用,以至于后人多以此为据,使此“二曲说”在1200年的沉淀中日益明晰,几成定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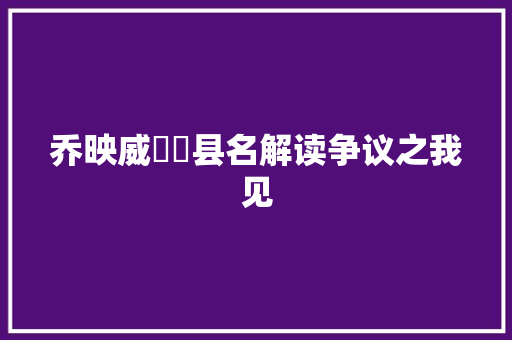
不过,山曲水绕之地比比皆是,“甲天下”的广西桂林更是如此,为何却只将“盩厔”释为“二曲”呢?
此问引来轩然大波,本县学者毛敏毅师长西席受高人启示,最早进行了艰辛的磋商。为了深入挖掘盩厔县名的本义,他至今已矢志不渝地趟过了36载的探索之路。特殊是从1987年开始的18年间,他不辞劳苦,奔波在周至、眉县、武功乃至扶风、岐山等地的村落寨堡拜访,查阅了一些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有关资料,还拜访过陕西考古专家、西安碑林博物馆馆长吴梓林等名家,独辟路子,写出了名为《解读“盩厔”》的考证论文,并于2006年首刊于《周至文艺》上。
2007年,文化功底深厚的著名汉字研究专家薛俊武师长西席匠心独运,又写出了《盩厔地名探源》一书,以策应毛老。二位师长西席独具慧眼,殊途同归,得出的同等结论是:盩厔,与山水二曲无涉,却与部族举行征战活动时为了勉励斗志、加强联络、攫取胜利而进行的隆重敬拜仪式有关。他们认为:“盩厔”一名是由周太公诸盩的宗庙“盩先王宗室”转化而来的。
此新说一岀,似石破天惊,众说纷纭,在周至大地上顿时掀起了研讨新浪潮,既有对新旧命名的评判寻衅,又有一些新的挖掘探索。后来,在县史研会的关注倡导下,2007年6月18日,第4期的《周至史志通讯》上公布了县地方志办公室关于举行“盩厔”地名探源漫谈会的关照,虽因故会未得开,但却有不少关心县名来历的新学者送来了发言稿,后经整理编撰,即在当年8月出版的《周至史志通讯》上部分刊载。因支持新提法和掩护旧说法并存,各自为政,据理力争,搞得不可开交,引起了环绕“县名成因”的新思考与谈论,连锁反应开始向县外、省外延伸,形成了“文化名县”大旗下的一股劲流。
辩论此起彼伏,时有闪光不雅观点冲击传统提法,但总是波未及岸。直到2019年,符明琨师长西席的《“盩文化”与哑柏魂》与梁理植师长西席的《“盩厔”之我见》分别在《周至文史》第二期上揭橥后,更拓宽了争议范围。
于是,2020年,《周至文史》上又先后揭橥了都城师大教授张鹏卜老师的《周至县名考义》、林茂森老师的《盩厔县域名探源》、李瑞祺老师的《关于在周至撤县设区时应规复利用原“盩厔”二字的报告》、南京师大教授施谢捷老师的《释盩》;2021年,《周至文史》上又先后转载了西北大学教授袁勘省老师与西安博物院副研究馆员葛天老师合写的《盩厔县名考》、史研会副会长杨军康的《浅言盩厔建县与盩厔共斗鼎》等文;2022年,又有薛俊武师长西席的《再以“盩厔”呈尊者辨》和史研会李瑞祺会长的《周至县是名副实在的千年历史文化古县》等文刷新了《周至文史》的新记录。
在坚持“盩厔”二曲论的文章中,代表作有赵寿铭师长西席的《对“盩厔地名新解”的几点意见》,浙江财经学院教授赵映诚师长西席撰写的《解读“盩山厔水”——兼与毛敏毅、薛俊武师长西席商榷》,还有地方学者屈毓晓师长西席通过研究更进一步认为的“盩山厔水应指终南一带的山水形状,这里山高水深,水流湾湾,堪配‘二曲’之义”等论。个中,县志办原副主任纪德新老师撰写的《诸盩、盩师与盩厔——盩厔县名考释》一文,客不雅观地剖析了一些不同不雅观点。
随后,一些学者不断印证,又说盩厔县名的含义肯定与周先公“公叔祖类”之名诸盩有关,这里经历了由人名到地名的一系列推演过程,有些粉丝又更加确信了此等说法。
下边,仅选几位颇具代表性的师长西席论文及其不雅观点予以赘叙,权充简评之数。
张鹏卜教授认为:“盩厔”一词可看作是盩庙、盩室,是古公亶父及周人、当地人对付诸盩的纪念和思念。盩庙的利用,使得周文王在组建六师时,自然而然地考虑到其命名的概括性、准确性及地域性,如:豳地,建豳师;盩地,建盩师。因此,盩厔县名最初当与周先公“诸盩”有关,即地名源于人名,“盩厔”源于敬拜。
此说法单刀直入,方向性光鲜,划出了县名来历的范围区域,启示性强,只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趋于纯挚,需在论据上连续夯实。
他从古学者文著中悄然创造:段玉裁师长西席在《说文解字注》中对“盩厔”之义有了进一步的阐明,称此“即周旋、折旋字之假借也。”而清代学者王先谦师长西席也释注:“盩厔与周折同音。周旋中规,折旋中矩。”根据文意可知:“盩”、“厔”二字形容环抱、环绕的不同路线形式,即“盩”指无角度的圆形环绕;而“厔”则指有角度的弯曲环绕,简称为“盩圆厔曲”。
我以为:此说侧重于从字义上解读成因,自然而然,让人更易理解“山曲曰盩,水曲曰厔”之本义及其差异,增长了此语的说服力。加之师长西席的文章文化内涵丰富,深刻自然,此据当不失落为一种能站得住脚的好说法。
薛俊武师长西席进一步认为:“盩”字在甲骨文中就有,许慎在《说文》中按小篆形体阐明为:“引击也。从幸,从攴,见血也。”或皿或血,皆是“击打以器皿接血”之意,“攴”是击打,而“引”指牵引,“引击”即“束诸其物,施以击打”之意。而“厔”字,在《说文》中又释之为“室”字,说:“室者实也”,当有实践、落实之义。于是,“盩厔”之意为:“将罪隶束绑起来击打之,并取其血用以敬拜”。在这里,许慎之解中,人祭也即“血祭”,古称为“歃血为盟”。
而“诸盩”则是一种古代名流(英武豪杰)的谥号,是朝廷按其生前功德修为所赐之名。从前的“盩先王宗室”,则既是敬拜先王诸盩的场所,也是古公亶父、季历、文王、武王祖孙四代人的署衙,声名大震。《簋》铭文中的“称盩先王宗室”一句,则是记载周厉王用第一人称所写敬拜盩先王(诸盩)的祭文中的定论。经查,发生在厉王十二年(前871年)的敬拜仪式属实。当时,刚毅刚烈式登基不久的厉王率文臣武将、社会贤达等,到盩先王宗室搞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敬拜活动。以是,这里推出的“盩厔”之名来源依据,按说应无悬念,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现今创造的记载在宗室敬拜盩先王仪式的《簋》铭器,却是在扶风县法门镇的齐村落出土的。细思倒也无奇,由于60公斤重的物件,毕竟不难移动,更况移之不远,也能说得过去。
事实上,西周灭亡前夕,盩师之驻地青化一带正处于战乱中。盩师为了保卫盩庙及其所置彝器等免于危难,遂派兵速带物器向北方相对安全之地转移,并分两次将包括《簋》在内的103件随品转出原址;这时,诸盩祖庙也有迁移迹象。
在《礼记·曲礼》中,因有“三十曰壮,有室”的记载,可见,此处之“室”当指家室,夫以妇为室,即家。而家乃酝酿希望、和谐生息的社会细胞,则此“室”当有“天地合和、氤氲涵濡”之意,个中的“氤氲”指“烟云弥漫的样子,形容喷鼻香气不绝”;而“涵濡”则为“滋润津润、沉浸”之意。
到了战国时期,这里成了秦国属地,局部战乱时有发生。秦昭王执政期,将“厔”变更为“室”字,“室”可能是指箭矢落地后所置的处所。于是,“室”字又与战事相联系,其内涵、外延随之扩大,以至于用“室”作为地名、地域名甚或县治之名,也当在认可之列。
总之,薛老探究从古公亶父南迁到厉王拜祖这一期间之历史,认为此处天地涵合,人神共振,英雄辈出,文化复兴,是“盩厔”二字最早源头:“盩”与“周”近似,是英彦贤烈之尊称,厔与室同义,是英彦涵和之所寓;盩,表示的是英彦(漂亮之士,才智卓越的人)卓尔(精良卓绝,高高直立的样子);厔,则突出的是恩典膏泽涵濡。故定义为:“英彦曰盩,涵濡曰厔”。
我以为:薛老的研究深入细致,全面严密,表示出深厚的古笔墨功底和历史涵盖面,给人一种居高临下、逻辑严密、环环相扣、出奇制胜之感,但此阐明有些抽象难懂,又和“击打血祭” 之“盩”义在一定联系上稍显勉强,有一点点美中不敷。
西北大学的袁勘省教授和西安博物院的葛天馆员经由深入研讨,合写了一篇论文,把盩厔“二曲说”的不雅观测点定在了周至县竹峪台原一带,认为:秦汉期间的盩厔山就位于此地,南接秦岭,原沟相间,曲水萦绕,物华天宝;强调说,诸盩是先周公叔祖类庙的讳称,台原这一带曾有过“盩先王宗庙”。盩人可能是一个族群,生活在包括本日周至县在内的渭河以南地区,与周人同祖,一度隔渭河而并行发展,终极融为一体。
其详细剖析思路比较清晰,大致为:周至在1964年之前称“盩厔”,为专有地名,从起名至简化改字止,共约2102年历史;而简化后改字距今,也不过虚龄60载而已!
“盩厔”二字的含义,至唐代涌现“二曲”解后方被后人知晓,历代沿用。虽说近年来涌现了一些质疑者,但并未从根本上彻底撼动“二曲说”之地位。有人将本日周至县境置于周代进行研讨,但个别地方之推理稍欠严密;有人供应的文献考证资料较详,但陈说的结论却不甚空想。于是,两位师长西席同等认同了“盩厔即盩庙”的不雅观点,并在此根本之上,增加了一些新史料,进一步探求“二曲说”及“盩厔即盩庙”不雅观点的合理性。
作者分立小论,征采联系,层层剥笋,点面结合,不断增强说服力,先从张衡《西京赋》中的“右极盩厔,并卷酆鄠”句入手,引用薛综“盩厔,山名,因县名”的注释,印证了“盩厔山”的存在;又通过剖析指出:盩厔山的位置不应是南部秦岭的终南山一带,也不是本日仍称“北原坡”的北邙山、“西原坡”的小西岳,而是关中民众古时称原坡为山的今县西部的黄土台塬地。后因此地域毕竟不是真高山,以是逐渐被后人遗忘。
这一“盩厔山”说法新颖独到,让人线人一新;但细一沉思,却创造“盩厔县因盩厔山而得名”一句可能有失落偏颇。由于生于张衡之后的三国东吴名臣薛综的“因县名”一句,与唐代李吉甫释周至原名时后人加的“因以县名”意思不同,是否应译为“由盩厔县名而命名”呢?此可与师长西席们再行商榷。
若果如此,那么,在西汉武帝设置盩厔县之前,该当尚无“盩厔山”之名。由于,作为东汉著名天文学家、文学家的张衡,只有知道盩厔县名后才有可能写出“西极盩厔”这一名句的,而随后的薛综也才能轻松地为之作注了。退一步说,纵然先有盩厔山,后有盩厔县,那也只能表现出县名的大略来历,并不能解释县名之内涵意义;更况,张衡写赋、薛综作注之时已有“盩厔县”名,再无必要用山名为之命名了;再说,既然盩厔山存在,现又在何处?再小的山也不可能溘然消逝!
若此山从属于秦岭北麓,更不可能只在秦汉期间才溘然涌现,应早已矗立了千万年。
至于盩厔为“二曲”源地之说的剖析,则较为精辟。由于周至县从古至今无论若何划分,皆是秦岭在南,水流往北,发源于秦岭北麓的河流的确较多,且尽弯曲注入渭河。难能名贵的是:作者将以前志趣相同者考证岀的两个不雅观测立足点比拟剖析,思路更加清晰。文章中,先指出“二曲说”形成前依照不雅观测点剖析的推理过程,再解释该说形成后本日的一些研究者为何要转移不雅观测点的道理,让人一览无余。
其推理为:当时的县城,肯定适宜较大规模人口的聚拢,一定会坐落在秦岭的终南山沿线台原与关中平原过渡地带的枢纽处。而周至县西南部的竹峪一带台原地区刚好散居村落民较多,且有沟壑连绵、弯曲山势的局部地形,也有泥峪河、沙河、阳化河、仰天河等河水弯曲北流的客不雅观面貌,符合“二曲说”的基本条件。但是,汉武帝建县时却将刚起名的盩厔县府设在了当时的终南古城,辖区在黑河以东、涝河以西地区,南仰秦岭,北越渭水,与当时西边的武功为邻,统归右扶风所管。能起此名,肯定是参考了此处的干系特色而为,认为这里更符合“二曲说”之条件,而绝非空穴来风。
至于到了唐代,宰相李吉甫一针见血地用“二曲说”阐释盩厔之涵义,距西汉建县已近千年。虽说当时的实际源地范畴已有一定改变,不雅观测点亦变,但万变不离个中。李吉甫释名时肯定参考过当年建县时的实际状况:若无把握,必定经不住磨练,他决不会拿自己的一世英名轻易去冒此小险。
本日的周至县,从属陕西省西安市统领,地处关中西部,东依白马河中央线与鄠邑区为邻;南依秦岭主脉与佛坪县、宁陕县交界;西有界碑与宝鸡市眉县、太白县接壤;北凭渭河与武功县、兴平市和杨凌区相望。境内沿秦岭北麓有大小峪口52个,较大的峪口人称“九口十八峪”,地域更广,曲貌更多。我们以此视角再来不雅观察盩山厔水,创造暗合道妙,更能自作掩饰。
再从词义上考证盩厔,除了《说文解字》中对“盩”的“引击”阐明外,《史记》中《世本》又载有“太公组绀诸盩”之语,指出组绀诸盩为叔类公祖,解释“诸盩”是周人的先祖之一。
他生了古公亶父,亶父又生季历,季历生文王,文王才生武王。按《周礼》哀求,显考以下之亲庙要搞月祭。周武王时,先祖“诸盩”供奉于“王立七庙”中之显考庙。诸盩作为周武王的高祖父,是公叔祖类庙的讳称。建立沣京往后,周人在沣京新建宗庙,而将以前作为政治中央的漆水河流域所建宗庙予以保留。因周武王去世后立了新庙,其高祖父诸盩的庙就需迁移。作为西周王朝建立后首个要迁的庙,诸盩庙不管迁到那里的远庙址,都能确定:在先周、西周期间,诸盩是周武王高祖父庙的称呼,可以简称为“盩庙”。
而“厔”呢,在古籍中也作“庢”,是“室”的异体字。在周代,室、庙、宫有互通征象,故盩室便是盩庙。可能是为了突显周王先祖宗庙的神圣性,才将“室”变为“庢”,即“厔”字。因此,“盩厔”二字的最初由来理应莫过于此。
1978年5月,扶风县齐村落出土的作于周厉王十二年的《簋》上“爯(称)盩先王宗室”等铭文,又印证了古籍的记载。
我以为:“盩先王宗庙”建于何处,既牵扯到何处是周城的问题,又关系到盩厔地名考证的问题。只有宗庙建于竹峪台原一带,才能在县名确义上和“二曲说”、“盩庙说”联系起来。
但是,感情不能替代佐证。既然盩厔山之有无因证据不敷尚难定论,就不能将推测出的此山和已考的“盩先王宗室”联系起来。不过,根据记载及考古推论,也不能打消盩庙曾建于竹峪台塬一带的说法。大概早就建立,并与渭河以北的宗庙并存,但可能是犬戎部落曾进攻过西周的缘故吧,渭河以北的宗庙尚有过迁移的迹象。
周至县竹峪一带有个最主要的西峪遗址,在2013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十年来,当地出土过西周半圆素面瓦当、秦代葵纹瓦当、汉代云纹瓦当、回纹砖、乳钉砖、陶水管等文物,其附近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有西周早期的此母觯、父丁爵、饕餮纹爵,西周中后期的太师簋,西周中晚期的窃曲纹鼎,西周晚期的作姜氏尊簋等。2006年以来,“盩先王宗庙”与西峪遗址的关系,更受到一些学者的热切关注。
两位师长西席于是大胆推论:盩庙可能当时就建在或迁在周至县竹峪台塬一带。由于,周至县在先周期间是周人的核心活动地域之一,周人开山祖师后稷在武功县的漆水河谷一带生息过相称长一段韶光,城邑为周城。当时,周塬位于漆水河下贱,间隔渭河颇近。漆渭之会正对着周至县竹峪一带。
史籍记载:西周时,“岐沣之域”为西周核心地带,个中心还包括盩厔县渭河南塬一带。由于周人从岐严密丰镐,必过渭河,其渡口当常在周至、眉县接壤一带水量较小的渭河南北岸之地(越往下贱越不易渡河),而河之南往东行也成为周人的活动核心区;但因离岸近处地下水位高,水源丰富,低平的地方不易住行;而竹峪一带的台塬阵势,则比其东面、北面的渭河平原一带都要高,且排水便利,于是,竹峪一带便成为主要的暂住城邑,乃至一度还建有“盩先王宗庙”,乃至长期休养生息。这对当地居民的大领悟也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促进浸染。
上述议论鞭析入理,互为因果,深入浅出,颇有见地,值得肯定!
但因对命名说的两种不雅观点皆投了附和票,彷佛主题看似光鲜而核心却尚欠一点突出。
人文社会科学专家王博太师长西席认为:周至县名的研究,应挖掘周秦根文化精华,糅合周至(盩厔)县名来历的旧说与新论。此发起颇有见地。周至县古名在西汉建县时涌现后,可查出其县制故城在今周至县终南镇一带,且其地理范围西至黑河而东到涝河,却并未将今周至西南塬区一带涵盖在内。要考证有关周至设县之初的历史和设县时的地域大小,理应结合同时期的周边县史进行剖析。而当时的西南塬区,则包含太白山下的今属眉县一些塬区及周至县境内的塬区,且当时皆归武功县统领,后来各辖区又因故几经变迁。这个史实对付讲求周至(盩厔)县名的真实来历及其涵义,又增长了一个打破口。
综上所述,莫衷一是,众说纷纭,各有千秋。秦人古有用“山”称塬坡的传统,当时若确有“盩厔山”且该山真指周至县竹峪台塬一带的原地,也无必要以此再命县名;何况此山至今仍不见详踪,更难圆其说。而“诸盩”既是先周公叔祖类庙的讳称,且周至县竹峪台塬一带也确曾有过“盩先王宗庙”,那么,“盩厔为盩庙”之说则肯定行得通。这种考证精神难能名贵,结论无可厚非。
根据史实和情理等,能挖掘出一些富有含金量的新不雅观点,实属不易,只可鼓励,不能求全责备。否则,假定当年给县域命名之人又横空出世,讲出原形,而你还多疑少信,那就失落去了刨根问底筛选真正答案的核心目的及意义,倒成了一段笔墨游戏了!
鉴于此,深入挖掘有关周至县南塬保存的先周历史资源,追溯寻求县名与先周历史发展之间奇妙关系之比重,就具有了相称主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人几经综合剖析认为:“二曲说”传承历史,相符时貌,根深蒂固,颇具威信。纵然“山曲曰盩”的不雅观测点在周至县竹峪台塬一带而“水曲曰厔”的不雅观测点却在黑河以东浩瀚弯弯曲曲的溪流之上,那也未离开大周至的统一版图,以此命名仍为精确;虽然“二曲说”之命名未涵盖人文、历史等方面的意义,但也不失落为一种雅俗共赏、利于周至旅游奇迹发展的合理结论。
而“周庙说”之研究赞许者亦不少,也确有人文历史可寻,并且当地尚有直接出土文物之有力佐证,对提高竹峪台塬地区的有名度、打造周城一带旅游景点皆大有裨益,值得肯定!
根据古代初设县时地域和本日周至县地域的不全相同,我不妨推测如下:西汉建县时以“盩厔”作名,肯定有其固定涵义及道理,只是当时未及时将来历涵义等传承下来,故不一定是此“二曲”说,但并不能打消此已有定论之不雅观点。“盩厔”因当时地域在黑河与涝河之间,在不少人的认知中,不雅观测点由竹峪台塬一带转移到了周至县东部的终南一带。这里发源于秦岭注入渭河的溪流的确更多,纵横交错,川流不息,且有首阳拔高、九峰聚众、鹰嘴迎宾、楼不雅观隐圣,到处峰回路转,曲径通幽,更显山水环抱、出类拔萃之奇,故更配“二曲”之说;而我辈研讨之“盩厔”历史,也已越秦连周,尽显忠实,侧重于从历史的角度通过字义和古迹引经据典,来磋商本日周至县境内的西南塬区状况,亦颇有收成。因此而得出的“盩庙说”及“英彦曰盩,涵濡曰厔”等结论,也不无道理。
事实上,有争议是件好事,理不辩不明。只有百花齐放,才能彰显出满园春色中虫鸟竞相鸣舞的勃勃活气!
愿能有更多的专家、学者、教授等地名爱好者投身个中,大显技艺,尽展睿智,连续深入挖掘盩厔命名的原形,以图更好地珍惜人文真迹,还原历史原貌,为周至历史的认祖传承、人文古迹的见证整理和地貌脉络的对号入座做出新颖可靠而又切实完全的突出贡献!
特于此与您共勉。
乔映威:笔名乔茂昌,1958年8月生,西安市周至集贤人,中共党员,毕业于陕西师大中文系。属高中语文高等西席,从事教诲传授教化事情38年,前任职于周至六中,现已退休。系中国当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字画院高等研究员、西安市教诲学会会员、西安市《数风骚》丛书编辑部副主任、周至县当代文学研究院副院长、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副秘书长、楼不雅观台道文化研究会研究员。
先后在《西席报》《唐都学刋》《数风骚》《咸阳文萃》《周至文史》等平台上揭橥有诗歌、散文、随笔等作品上百篇,尤以韵文形式见长。出版有《韵声载道》《 化性歌》《 儒学经规韵解集》《快板解读<道德经>》《点玄通圣》等著作。个中有113首古诗词被《中华诗词大词典》《传世孤本》等八部国家级文籍收录;十一篇教诲传授教化专业论文得到国家级、省市级、县级不同褒奖并在一些名刋上揭橥;一些业绩被国学文化传承网在百度上作为“哲学大家”宣扬;近年入选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编撰的大型报告文学作品集《雕琢奋进新征程》《初心映照党旗红》。比较热衷于对一些国学历史文化的宣扬和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