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特邀作者任艳
清朝乾隆年间,生活着一位发出“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诗人”感叹的墨客——黄仲则。黄仲则是常州人,幼时丧父,少年丧兄,只留下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小小年纪的黄仲则一次又一次地体会到失落去亲人的痛楚,幸而,他碰着一位叫洪亮吉的朋友,收成了一份死心塌地的交情。
黄仲则曾题诗赠洪亮吉:“君家云溪南,我家云溪北。唤渡时过从,两小便相识。”两人的家隔着白云溪,相去不远。有时相识后,两人常聚在一起嬉戏,更少不了读书、作诗。相仿的年纪,附近的爱好,让两人很快成为好友。
黄仲则酷爱作诗,常躲在被窝里思虑佳句,有一次作得一首诗,心中颇为得意,不顾好友正在睡觉,一把摇醒洪亮吉,两人抵头吟咏,共同欣赏。二人形影相随,一起参加乡试,结伴远足。他们斗志昂扬,评论辩论着往后建功立业的豪迈空想。有了洪亮吉的陪伴,黄仲则的少年纪月多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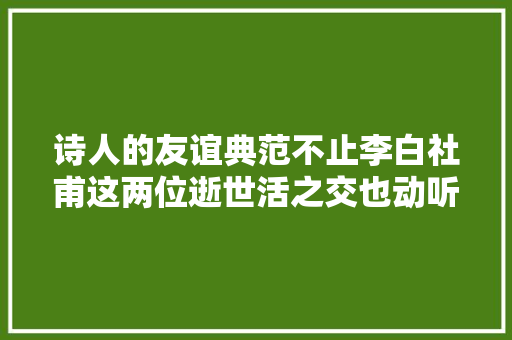
惬意的光阴总是短暂。才华出众、童子试第一的黄仲则,乡试却屡试不中,生活也随之陷入困境。现实与空想的落差,让孤高自大的他不禁产生怀才不遇之感,所作诗词全是一派抑塞悲惨之气,诸如“每放登高恸,浮云为惨凄”,又如:“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
洪亮吉理解黄仲则的愁苦。为了帮朋友改进困顿的局势,他拉着黄仲则一同前往安徽,投到安徽学政朱筠门下,帮朱订正文章,做些秘书事情。两人逐日一起勤奋事情,夜幕四合之时,更是钻进一个被窝里青灯黄卷,评论辩论诗词。
日子稍有改进,又有好友相伴,黄仲则烦闷的心情有所好转。他更加爱做诗,常常挥笔而就。他的诗才,犹如他身上白袷衣在太阳下发出的亮光,闪瞎了所有人的眼,众人纷纭为之惊叹,争相模拟他的诗。黄仲则一时名声大噪。
为了钻营更好的发展,黄仲则思来想去,决定去京城闯荡,他惜别好友洪亮吉,一个人踏上了北漂的路途。
然而,北漂的生活艰辛不易。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参加乾隆东巡召试,应二等,赐武英殿书签官。可这样一个芝麻小官看不到任何未来,根本无力支撑一家人的日常开支,也丝毫无法旋转穷寒生活的轨迹,黄仲则的生活难以为继。“百口都在风声里,玄月衣裳未剪裁”,如此困难度日的环境,被赶来京城的洪亮吉看在眼里。
好友的悲惨处境深深触痛了洪亮吉的心,洪亮吉倾尽全力,再次伸出援手,一边出资帮黄仲则把家人清偿常州,一边将他举荐给陕西巡抚毕沅。所幸,毕沅对黄仲则的才华十分倾慕,接待之后,还声援他为县丞,回北京等待任官。可身体孱弱又贫寒交加的黄仲则,终于没能等到走立时任的那一天。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四月,途经解州时,黄仲则终于一病不起。他挣扎着给好友洪亮吉写信,请托身后之事。洪亮吉一收到信件,就昼夜兼程,马一直蹄地赶往解州,却只看到好友枯槁的尸身和几张飘零的诗稿。
想到老友才华横溢,却生平不得志,如今竟至病去世异域,洪亮吉涕泗互换,他决定,不管多难,一定要带好友还乡!
于是,洪亮吉和一匹拉着棺材的白马,行进在波折山路中。棺材内躺着一代诗才黄仲则,白马边行走着洪亮吉,曾经的石友,如今阴阳两隔,却无法阻断他们的情意。山河迢递,死活相依,从山西到常州,千里漫漫长途,洪亮吉陪伴黄仲则走完末了的行程。一如洪亮吉所言:“噩耗到三更,老母寡妻惟我托;炎天走千里,素车白马伴君归。”
不计付出,不问回报,洪亮吉总是在朋友最须要他的时候,当仁不让地给予最温情的声援。不管世态如何淡漠,人情如何薄凉,这世上曾有那样一种叫洪亮吉的交情,温暖着人们的内心。黄仲则短暂的生平贫乏坎坷,是其不幸;然而他结交到这样一位“素车白马伴君归”的去世党洪亮吉,他又是何其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