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从县城回来途经,我以为口渴,母亲便带我去庵里要水喝。随着大路西侧一条小径,来到泥墙上一扇木门前,门扉虚掩,母亲轻轻推开,几位尼姑在对面檐下用饭,院子里青菜长得绿油油。穿青灰长袍的她们,瞥见我们都笑着呼唤,个中一位走上前来,手里还端着饭碗,碗里是汤面,和我们在家吃的一样。
那尼姑慈眉善目,和我母亲差不多年纪,叫我们进去用饭,十分激情亲切,我很想吃吃她们的饭,可是母亲回绝了。记得喝水时,母亲问她家在哪儿,她答从前是某村落的,我没听过,纳闷她为什么要出家,但虽是小孩子也知道不可以问,只觉这样问很无礼,而且看她那般安详,彷佛也不必问了。
——《坡上有个尼姑庵》三书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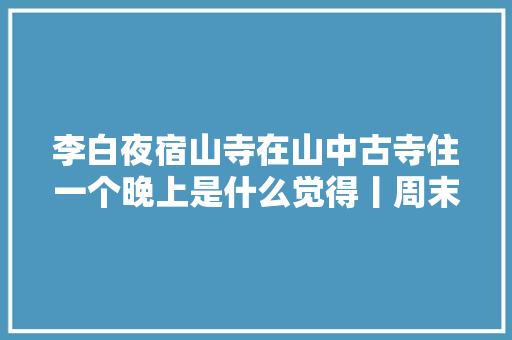
夜宿山寺是什么觉得
明 佚名《山寺问道图立轴》
《夜宿山寺》
(唐)李白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不敢年夜声语,胆怯天上人。
这首绝句入选小学语文教材,不知出于何种缘故原由,也不知城里的小学生读了是何觉得,他们可大都住在高楼里呢。小区里有个幼儿园,下午放学韶光,女老师领着五六个孩子从楼下手拉手走过,边走边背古诗,都是五言绝句,个中就有这首,孩子们声音脆亮,吐字如炒豆,背得那么愉快,我坐在楼上如听春莺百啭,一片艳阳天。
我也住在高楼里,像山顶洞人,某晚很好的玉轮,我一时兴起,乘电梯上到28层楼顶,高则高矣,却没以为离天空更近,反而天空朝四野垂下去,天上疏星七八颗,亦不觉举手可摘,切实其实没有想要去摘。周围三面是小区的楼群,夜色中像一群阴郁的巨人,西南方朝向村落落和果园,远处一脉山脊线横亘天边,断裂处通过一条高速公路,夜静中车声隆隆轰响。我可以年夜声语,可以大喊几声,但声音还没出来,就已消隐在空气中。
李白这首《夜宿山寺》,如题所示,写他某夜宿于山寺,寥寥数语,似无多少深意,不过细味之,那样的夜晚也真有趣,于今几不可得。就拿题目来说,夜宿山寺这件事,你生平能经历几次,可曾经历过?
唐代墨客与山僧交往甚多,李白写他访问羽士和僧人的诗不计其数,比如《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谈玄论道,说空说有,洋洋洒洒费许多话,但都不及这首《夜宿山寺》,无意为诗,信口四句,便通报出那个夜晚的静,犹如大音希声。
想必那寺庙是在山顶,李白登上的高楼,当然没有现在的摩天算夜楼高,但因在山顶,野无人杂,以是觉得高及天宇,仿佛伸手即可摘到星辰。又彷佛离开人间很远,已比邻天上,乃至不敢年夜声语,恐怕一出声会惊动天上的神仙。
我疑惑李白吟出这首诗时,自己也吃了一惊,就彷佛一欠妥心叫出了寂静的乳名。摘星星也好,天上人也好,皆因山寺之高与夜晚之静。有人疑惑这首诗的作者不是李白,而是某某墨客,但考证并无结果,实在何必呢,这首诗的作者当然不是李白,也不是某某人,而是无名,或许便是那大音希声,所谓文章本天成。墨客曼德尔施塔姆在诗中这样论诗:“仿佛一块石头从天外陨落,一行诗,出生不明,被黜至此。”
2
夜宿云门寺,梦与白云游
清 钱维城《豫省白云寺图》(局部)
《宿云门寺阁》
(唐)孙逖
喷鼻香阁东山下,烟花象外幽。
悬灯千障夕,卷幔五湖秋。
画壁飞鸿雁,纱窗宿斗牛。
更疑天路近,梦与白云游。
云门寺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境内的云门山,别号东山,始建于东晋安帝时。《舆地纪胜》卷八记载,昔王子敬居此,有五色祥云,诏建寺,号云门。云门寺自南朝起即是一处隐居胜地,梁代处士何胤、唐代名僧智永都曾于此栖隐。
是夜,孙逖宿于寺阁,有感而作。诗中叙山寺夜景,颇有次第,首联了望烟景,幽趣超然象外,颔联到达宿处,即喷鼻香阁,瞑色四合,山峰嵬峨如樊篱,明灯高悬,拉开窗幔,五湖秋色尽收眼底。古以洞庭、彭蠡、太湖、巢湖、鉴湖为五湖,此处指的是鉴湖。
颈联写卧床环顾,上句看阁内壁画,“画壁飞鸿雁”,“飞”字令鸿雁形象维妙维肖,下句隔窗见斗牛二星宿,“纱窗宿斗牛”,“宿”字见星辰之残酷,有如停在窗前。尾联写眠后所梦,由实入虚,“更疑天路近,梦与白云游。”唐诗里涌现的白云,多来自《庄子·天地》篇描述的瑶池,“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此处化用,境界开阔,有浩然无尽之意。
云门山精舍甚多,《水经注·渐水》曰:“又有玉笋、竹林、云门、天柱精舍,并疏山创基,架林裁宇,割涧延流,尽泉石之好。”渐水,即浙江,浙的古音读斩,与渐一音之转,是古代越语的汉译。
夜宿深山古寺,其景其情,可从诗中大抵想象。我曾在少林寺景区住过,白天游客熙攘不必说,夜晚虽静,月照嵩山,却因在景区里,连自然也变得人工,又武馆林立,黎明即起,一队一队跑步练功,山里全无古刹的清幽。亦曾夜宿武当山,住在道不雅观旁一户田舍,熄灯躺在床上,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静,静原来不是静,而是静得山崩地坼,又听见胸膛里咚咚心跳声,对自己的身体好不陌生,后半夜被寒意逼醒,愕见白灰墙上一条似蛇似蚯蚓的虫,再不敢熄灯,唯惴惴以待天明。
3
一篇诗体游记
清 董邦达《霜林萧寺图》(局部)
《山石》
(唐)韩愈
山石荦确行为微,薄暮到寺蝙蝠飞。
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
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
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
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
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
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若在韩愈诗集中选一首代表作或成名作,该当便是这首《山石》吧。早在入选《唐诗三百首》之前,此诗已被宋、元、明、清的墨客、诗评家广为称道,历来好评如潮。苏轼与朋侪游南溪,解衣濯足,朗诵《山石》,慨然知其以是乐,因依照原韵,作诗和之。
诗题为“山石”,并非咏山石,实乃一篇诗体游记,取诗的开头二字为题,此是旧诗标题常规,唐诗时或延用之,比如杜甫怀念李白的诗《不见》,题目即取自首句的“不见李生久”。
这首诗的好处无需多言,读者只管自己去读,去感想熏染措辞的气势,文采的壮美,跟随诗句,想象其景,如展开画图,触目在眼。全诗十韵,二十句,在唐诗中算是长篇,但读着不以为累,反觉过瘾,因其笔力提神,使人振奋。除却末了四句,前十六句全用赋体,一句一境,如在山阴道上行,花烂映发,令人应接不暇。
韩愈主见以文为诗,此真是高见,诗中的好句,实则是散文,写得太有诗味的句子,多数在虚张声势。对付诗的措辞,他也明确主见“陈言之务去”,《山石》即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其文意幽奇,有倚天拔地之势。且看他写景的前四句:“山石荦确行为微,薄暮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荦(luò)确,即山石险要不平。四句中每个词都极具质感,每个句子都能量充足,尤其是“芭蕉叶大栀子肥”!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个中一首曰:“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同写雨后花木,前两句是秦不雅观《春雨》诗中的句子,非不工巧,然嫌其太过柔弱,故曰女郎诗。而拈出来比拟的,便是这句“芭蕉叶大栀子肥”。我们知道,诗句的气质反响出来的,乃是作者的心灵意见意义。
这里引出一个有趣的征象,即作者与作品的性别特色,男性作者可以写女性觉得的作品,如秦少游的诗,反过来,女性作者也可以写男性觉得的作品,如李清照的词。即便小说,女性作家可以写男性角色的故事,且男性角色的视角并不一定即是男性视角,因此有女性男作家与男性女作家之说。常被大众媒体定性为女性主义作家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强调,她既不迷信男性视角,也不迷信女性视角。
读韩愈这首诗,觉得其笔力高古,写景句多浓丽,即事句出以淡语,通篇浓淡相间,纯任自然。美中不敷在末了四句,附此议论实属多余,且陈词谰言反令气势衰杀,最多以“人生”两句收束,末二句删去可也。
一样平常认为此诗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七月,韩愈离开徐州赴洛阳途中,游历投宿的是洛阳北面的惠林寺,同游者有李景兴、侯喜、尉迟汾,“嗟哉吾党二三子”即是说的他们。如是则末二句不过应景说说,韩愈自己也未必真的想隐居在山里,却是连累了一首好诗。
撰文/三书
编辑/刘亚光
校正/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