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自出身以来,一贯受到历代读者的喜好,唐诗研究也一贯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据不完备统计,1978年至今,以唐诗研究为主题的论文有11000余篇,1996年至今,干系硕博论文有2900余篇,临近学科涉及唐诗的论文约8000篇,合计超过20000篇。另据尚永亮《近20年唐诗研究述论》统计,1978-2018年唐诗研究的成果多达34930项。当然,唐诗研究的繁荣,不仅表示在成果数量的几何式增长上,更表示在质量的明显提高上。改革开放新期间以来,唐诗研究有如下突出特点:
鉴赏热。新期间之初,百废待兴,广大读者热切期待真正探索唐诗艺术奥秘的著作。由此,引领唐诗鉴赏风气的作品应运而生,较具代表性的成果有:刘逸生《唐诗小札》、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而尤往后者影响为大。沈祖棻是当代著名词人,其《涉江词》《涉江诗》在抗战时名誉鹊起,同时她又是著名学者,以墨客之心解析诗词,别有会心。《唐人七绝诗浅释》从作品本身出发进行剖析鉴赏,其方法是先精讲一首七绝,然后列举多少首题材、风格附近或相反的作品,加以比较,每每有举一反三之效。此书与其《宋词赏析》,是20世纪80年代初最盛行的诗词鉴赏类图书。而真正的唐诗鉴赏热,还是在《唐诗鉴赏辞典》出版之后。《唐诗鉴赏辞典》作者达百余人,均为从事唐诗研究、传授教化的学者,代表了当时的研究水平和学术眼力。该书发行数百万册,推动唐诗名篇走进千家万户,深入民气。公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唐诗鉴赏集》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前者选材较广,后者赏析较精。中心公民广播电台的“阅读与欣赏”节目,常常播出唐诗鉴赏节目,且将笔墨稿汇编成书出版。此外,唐诗选本的出版也盛极一时。清人孙洙所编《唐诗三百首》一版重版;公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唐诗选》及李白、杜甫、王维、高适、岑参、韩愈、元稹、白居易、李商隐、杜牧诸人的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一批唐代主要文人的“选集”。这些都为广大读者欣赏、阅读唐诗,供应了优质的文本。周啸天主编的《唐诗鉴赏辞典补编》则进一步推动了唐诗的鉴赏热。近年来兴起的电视讲坛节目及诗词大会等,因其雅俗共赏、老少咸宜,也对推广中华精良传统文化起到了积极浸染。刘学锴的《唐诗选注评鉴》则是近年出版的唐诗鉴赏佳作。该书分“选”“注”“评”“鉴”四部分,共鉴赏唐诗近700首,选目与《唐诗鉴赏辞典》有较大不同。鉴赏方面,既博采众长又独具慧眼,对李白、王维、李贺、李商隐诗的解析、鉴赏尤其深刻。数十年来,唐诗鉴赏的热度不减,在促进唐诗遍及的同时,也提升了民众的文学教化。
大墨客研究热。唐代大墨客研究,近几十年来成果丰硕,如王梵志、寒山、拾得、杨炯、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张说、张九龄、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白居易、张籍、王建、刘禹锡、孟郊、贾岛、贯休、皮日休、陆龟蒙、韩偓等,均有创始性的注释本。而李白、王维、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温庭筠、杜牧等,则有接管旧注之长、后出转精的新注本问世,且呈现出综合研究的趋势。如白居易研究,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首次对白居易集作了笺释与订正,用力甚勤,收成亦多。其《白居易年谱》与《笺校》相辅相成。此后,谢思炜出版了《白居易诗集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谢注的一大特色是采录了日本金泽文库等数种白居易集,扩大了订正的范围,丰富、充足了白居易诗文注释的内容。青年学者陈才智整理出版的《白居易资料新编》,共搜集了中唐至近代3200余位作家的8000多则评论资料,参考书本3500余种,其字数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的20倍旁边。经由老中青三代学者不懈努力,白居易研究的成果已粲然大备,也大大打破了过去只重其讽喻诗、只谈论其公民性的局势,取得了多方面进展。再如李白诗集,宋人杨齐贤、元人萧士赟、清人王琦先后为其作注。当代李白研究的大家首推詹锳,其《李白诗文系年》《李白诗论丛》虽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但真正产生影响是在80年代之后。这两本书是当代李白研究的奠基之作,而他在此根本上主编完成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则是一部集李白诗歌校注之大成的著作。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接管了《李白诗文系年》的成果精髓。安旗主编的《李白全集编年笺注》、郁贤皓的《李白丛考》《李太白全集校注》亦多创获。周勋初的《李白评传》《诗仙李白之谜》,内容十分精彩。裴斐等人主编的《李白资料汇编》,为李白研究供应了丰富资料。刘学锴、余恕诚毕生从事李商隐研究,他们的《李商隐诗歌集解》集古今李商隐诗歌表明之大成,《李商隐文编年校注》《李商隐资料汇编》则为新创,另著有《李商隐诗歌研究》《李商隐传论》《李商隐诗歌接管史》等。有学者认为,刘、余二位的李商隐研究,改变了中国文学史的格局,使得李商隐由原来文学史的一节,变成了现在的一章。
文化学研究热。超出单一的文学研究,从文化学的角度谈论唐诗,也是唐诗研究的热点之一。陈寅恪创“以诗证史”之法,并在其《元白诗笺证稿》中有充分展示。其研究着重探索隐蔽于文学背后的历史秘闻,对学界深有启示。袁行霈、丁放《盛唐诗坛研究》谈论了盛唐政治与诗坛的关系,如论述唐玄宗崇信道家思想与迷信玄门方术对诗坛带来的影响;玉真公主对墨客的提携于诗歌发展的积极浸染;盛唐贤相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对盛唐诗歌的正面推进浸染;李林甫、杨氏兄妹专权跋扈对盛唐诗坛的侵害等,均从文史结合的维度作了自己的解读。邓小军的《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诗史释证》《古诗考释》等书,自觉利用陈寅恪的方法,对唐诗研究的多少问题提出了精到见地。傅璇琮、陈尚君、胡可先等学者,则由史学入手,探寻唐诗的历史背景,既从正史、野史条记出发,更重视敦煌文献、地下文献、域外文献等,使唐诗研究扎根在历史的沃土中。尚永亮关注墨客贬谪与创作的关系,李浩系统稽核地域、士族与诗歌的关系,戴伟华关注唐代使府与文学的关系,也有系列论著问世。孙昌武、陈允吉及李小荣、张勇等,致力于研究佛教与唐诗之关系。如陈允吉的《唐音佛教辨思录》《佛教中国文学溯论稿》论佛寺壁画与唐诗之关系,论王维、韩愈、李贺诗歌与佛教之分缘;而对付玄门、儒学与唐诗之关系的稽核,孙昌武的《玄门与唐代文学》、葛兆光的《想象力的天下——玄门与唐代文学》、刘顺的《中唐文儒的思想与文学》,都是较为主要的研究成果。任半塘首创的、以《唐声诗》为代表的唐诗与音乐研究,为其弟子们传承并发扬光大;袁行霈、陶文鹏关注绘画艺术与唐诗之交集,《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唐宋诗美学与艺术论》中均有精彩论述。将唐诗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对唐诗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大有益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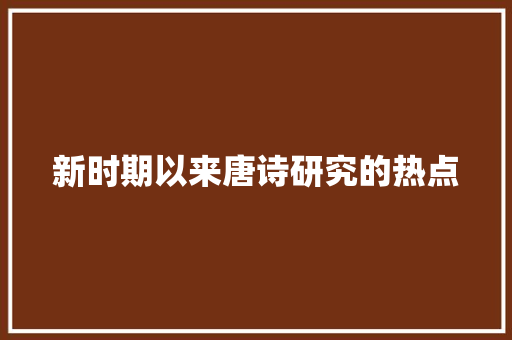
新方法热。“老三论”“新三论”、符号美学、新批评、阐释学、接管美学等新方法、新理论,对唐诗研究也有较大影响。这对付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有一定积极意义。如董乃斌的《李商隐诗的语象—符号系统剖析》、陈伯海的《意象艺术与唐诗》均用新方法解析唐诗;叶嘉莹用新批评派的“文本细读法”研讨杜诗;傅道彬的《晚唐钟声》借鉴原型批评方法。但新理论的利用,一定要与中国传统理论及唐诗创作实践相结合,否则就会成为两张皮,这是要深以为戒的。近年来,用接管美学理论研究唐诗,也涌现了较多成果,如陈文忠的《中国古典诗歌接管史研究》,从理念与方法、经典作品阐释史、创作影响史等方面,对接管美学理论的中国化,作了有益磋商,并对《黄鹤楼》等唐诗名篇的接管史进行个案研究。以唐代大墨客接管史为研究工具的著作或博士论文,数量亦较为可不雅观。而域外汉籍的唐诗辑佚及其研究,近年来也颇为生动。如东亚各国,自古以来就与中国交往密切,大量汉籍早已传入这些国家,有些是中土已失落传的文献,有些则与中土版天职歧,足资比较与参考。这些国家的墨客、学者研究或者模拟唐诗的成果,有的也有较高水平,至少有文献代价。欧美诸国则因各类缘故原由,保存了不少我国大陆稀见的唐诗资料,充分利用这些材料,也有助于唐诗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总之,新期间以来的唐诗研究对“文学本位”的认识尚待加强,艺术研究亦嫌薄弱。我们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确辅导下,充分利用我国古典诗学理论,适当借鉴西方理论中的合理部分,推陈出新,使唐诗研究迈向新的高峰。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07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