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所读过的辽代诗歌中,我最喜好欧阳修的一首七绝《奉使契丹回出上京立时作》和另一首《奉使契丹道中五言长韵》。由于它使我感到读诗如读史,诗、史相互印证,让我们更加进一步的感想熏染到诗、史所记真实可信,理解到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风土人情。
这两首诗是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欧阳修充贺辽道宗登基的国信使,出使契丹,受到辽道宗殊礼相待,赐御宴时特派尚父燕王萧孝友等四位重臣作陪,回程途中所作。墨客通过对契丹族独特的地域特色进行了描写,在展现他乡风情和民族特点有着独特之处。这两首诗皆气势磅礴,流畅自然,抒发了墨客丰富的情绪天下和畅达的民族、政治思想情怀。
契丹民族所生活的地区边陲辽阔,放眼望去天地相接,夏季河流宽广、水草丰茂,冬节却朔风凛冽、寒气逼人。春秋两季雪、沙飞扬,遮天蔽日。顽强的契丹民族在此地区繁衍生息,形成了以勇悍尚武为紧张特色的渔猎文化。墨客文笔雄浑,构思奥妙,意境空灵,再现了契丹民族所生活的塞外沙漠草原风光和北方游牧民族独占的游牧佃猎的生活办法,尽显契丹地域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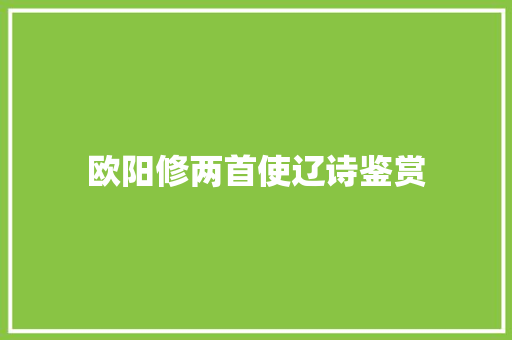
《奉使契丹道中五言长韵》中的“儿童能走马,妇女亦腰弓”,展现了契丹民族无论老幼、妇儒都具备的勇武性情与豪迈气质。同时也佐证了史乘所载的契丹人在渔猎捺钵时妇女儿童相随行的史实。
“白草经春在,黄沙尽日蒙”从这句可以看出沙尘暴自古就有。在这个春意渐浓的时节,南国该是春意盎然,活气吐露,可辽国的腹地依旧春寒料峭,与冬天没有太大的差异,就象欧阳修亲眼见到的一样,野外里没有一丝绿意,只能看到去年干枯的白草(亦作败草)及遮天蔽日的沙尘。“经”、“尽”,“在”、“蒙”不是浓墨图画,却是细笔点染,轻俏间已带出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特点。
“松壑寒逾响,冰溪咽复通。”长满松树的山谷寒风猛地吹响,结冰的溪水下面却水流淙淙,直接表示北方独特的地理环境。“响”“咽”突出了松林与冰溪的特点,只听见风声与水流,反衬出环境的宁静与气氛的冷咧,实为空灵之笔。
“合围飞走尽,移帐水泉空”、“斫冰烧酒赤,冰脍缕霜红”展现了北方民族特有的游猎、游牧的生活习气,“尽”与“空”都因此夸年夜的笔触描述了契丹人的“猎”与 “渔”情景。并不是真的把鸟兽、鱼介网罗一空。《辽代契丹习俗史》云:契丹人“围猎规模较大,少则几十人,多者逾千人”。出使辽国的苏颂曾经见过契丹人围猎的场面。它记载说:“北人(契丹人)以百人飞放谓之罗草,终日方获兔数枚,颇有愧色,顾谓余曰道次小围不敷不雅观,常以千人以上为大围,则所获甚多,其乐无涯也”。苏颂还有一首《不雅观北人围猎》诗更生动的描写出契丹人围猎情景:“莽莽寒郊昼起尘,翩翩戎骑小围分。引弓高下人鸣镝,罗草纵横兽轶群”。千人以上的合围,将野兽赶到一起围而歼之。镝鸣声、人喊声、兽叫声交织在一起,看到野兽纷纭带下,人们的精神哪能不冲动,哪能不愉快,哪能不感到“其乐无涯也”。由于科技的制约,没有当时的图像资料,但是清代有表现围猎场景的传世画作,那把整座山都围拢起来的情状的确让人感到震荡。(图)都知道清朝满族人是女真人后裔,史载女真人的很多习俗相沿契丹人,看到清代的围猎图也就看到辽代的围猎状况。契丹人长于在春季凿冰捕鱼,对此,宋人程大昌在其著作《演繁露》中有详细记载。《辽史营·卫志》也有契丹人在春捺钵时“卓账冰上,凿冰取鱼”的记载。“合围飞走尽,移帐水泉空”,并不是真的合围就将飞禽走兽捕获一尽,同时泉水也不会冰冻绝底,否则,鱼介怎能生存?既然如此,也断然不是把水源饮尽用光,再迁徙营帐去探求新的水源;而是用“尽”与“空”二字来形容经由一次大型围猎后,猎物稀少了而须要转换围场。“赤”与“红”是突出色调描写,把契丹人破冰捕鱼、点燃篝火烧酒,细切冻肉准备餐宴的过程逐一展现,这种大胆的修辞和表现手腕真是妙极。
“山深闻唤鹿”、“轻禽出海东”。契丹人为求生存而挣扎的恶劣生存条件除了练就其粗犷顽强的性情外也磨练得更加聪明,像“唤鹿”,是辽人射鹿的一种方法。《辽史国语解》、《辽史营卫志》都有记载,讲的比较详细的是《辽史拾遗补》所载清人查慎行的《人诲记》:“哨鹿之说,《辽史》已有之,每岁于白露后三日,猎者衣鹿皮,戴鹿头,天未明伏于草中,吹木筒作声,牡鹿闻之,以为求偶也,遂踊跃而至,至则利镞加焉,无得脱者”。诗中的“海东”是用来捕猎天鹅的海东青(鹰),契丹驯服这种猛禽,使之成为帮忙打猎的工具,《辽史拾遗》引《燕山丛录》记载了用海东青捕猎天鹅的情形:“海东青……即纵,直上青冥,几不可见,俟天鹅至半空,欻自上而下,以爪攫其首,天鹅惊鸣,相持陨地”。“ 轻禽出海东”进一步表现出契丹民族所独具的他乡风情及民族风貌。这首诗也间接地佐证了《辽史营卫志》所记载的契丹人居地环境景象的恶劣:“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的生活状况。
《七绝》中的前两句“紫貂裘暖朔风惊,潢水冰光射日明”紫色貂皮是裘皮中的上品,宋庄绰《鸡肋编》云当时人们穿着裘皮:“贵者披貂裘,貂以黑紫色为贵,青者次之,又有银鼠,尤洁白。贱者披貂毛、羊、鼠、沙狐裘”。欧阳修身着贵重的紫貂裘骑马从辽上京南门出来,潢水的冰折射着刺目耀眼的日光。“潢水”,学者葛华亭师长西席撰专文论述沙里河亦名“潢水”,当时在学术界哗然,后来在王家沟出土了辽大安三年的《故守太子太保,西北路招讨使,三十万都统军萧兴言墓志铭》,志文记载萧薨于职所守地:“妻氏郡主夫人等自塞下辇其尸之西楼潢水北三十里”葬之。王家沟距辽上京恰好三十里,方位、间隔与今辽上京遗址皆符合,此出土文献佐证了上京在辽代的别称,辽上京即“西楼”,沙里河即“潢水”这一史实。沙里河绕城南而过,因此可知欧一行离上京时走的是南门。后两句“笑语同来向公子,马头今日向南行”表达了作者这次成功出使契丹因喜悦而变得阳光的心情,而《五言》结尾两句“祗事须疆力,嗟予乃病翁。深惭汉苏武,归国不论功”则直抒胸臆,是以次充当和平青鸟使深入不雅观察和体验辽地的风土人情而引发了一些感慨:为使者者当身体力行,自己却体弱朽迈。想到曾经出使匈奴的苏武心觉得惭愧,返国后一定不会邀功请赏,表达了作者谦善豁达的肚量胸襟。
欧阳修的这两首诗意境雄浑、风格纯朴,用精练的措辞描述出契丹民族逐水草畜牧,以鞍马车帐为家的契丹景致与习俗,及分外的地域所授予契丹人豪迈之情。全诗声韵、用词都臻于完美,直抒胸臆,请辞真切,既雄豪旷达,又蕴藉委婉。让我品之又品,有味;读之再读,有情。
奉使契丹回出上京立时作
欧阳修
紫貂裘暖朔风惊,潢水冰光射日明。
笑语同来向公子,马头今日向南行。
奉使契丹道中五言长韵
欧阳修
初旭瑞霞烘,都门祖帐供。
亲持青鸟使节,晓出大明宫。
城阙青烟起,楼台白雾中。
绣鞯骄跃跃,貂袖紫蒙蒙。
朔野惊飙惨,边城画角雄。
过桥分一水,回道羡南鸿。
地理山川隔,天文日月同。
儿童能走马,妇女亦腰弓。
度险行愁失落,盘高路欲穷。
山深闻唤鹿,林黑自生风。
松壑寒逾响,冰溪咽复通。
望平愁驿迥,野旷觉天穹。
骏足来山北,轻禽出海东。
合围飞走尽,移帐水泉空。
讲信邻方睦,尊贤礼亦隆。
斫冰烧酒赤,冻脍缕霜红。
白草经春在,黄沙尽日濛。
新年风渐变,归路雪初融。
祗事须强力,嗟予乃病翁。
深惭汉苏武,归国不论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