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根据我们的生理特点和兴趣爱好等选诗教诗,由易到难,循规蹈矩。一二年级多为民歌、谣谚,还有一些有趣的打油诗。比如那首写雪的著名打油诗:“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通篇写雪,但不见一个“雪”字,十分有趣。到了三四年级时,父亲开始教我们一些五言、七言律诗和比较好懂的小令、中调,再之后才是一些长诗。
几年的背诗过程,父亲没有“威逼”,却有“困惑”——答应我们熟背之后,会买一些好吃的或好玩的。有时,父亲让我与妹妹比赛,看谁背得又快又准。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杜甫的“三吏三别”、柳永的《雨霖铃》,这些比较长的诗词彷佛也没费多大的力气就背了下来。
春花秋果、渔樵稼穑、季候节气、不雅观荷赏雪……父亲每每根据当时的情境和事宜,教给我们与之匹配的诗歌。他生动深刻的讲解在我们幼小的心灵埋下了一颗种子——“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读大学时老师让我们体会这几句诗的妙处,我便回顾起在荷塘边看鱼儿摇摆着尾巴倏忽游弋的样子。
后来,父亲还从古代诗词中摘一些句子让我们来对句。先是意思随意马虎理解的短句子,然后是长的、难的。父亲出“雨中黄叶树”,我对“风里绿竹竿”,妹妹对“雪里红梅花”,父亲说这是“去世对”,而且对仗不工。他见告我们这是唐代墨客司空曙的诗句,原句是“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通过比较,我们对“去世对”有了认识,对诗歌中人与景物的关系处理也有了粗浅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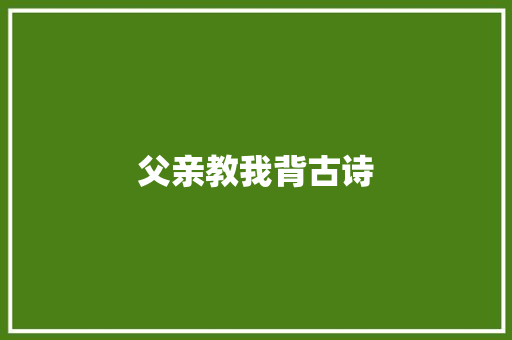
父亲又把他精减的《笠翁对韵》拿来教我们诵读:“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当时只以为顺口好玩,却为中学阶段写作文积累了丰富新颖的词汇。在父亲的辅导下,我们逐渐能对出一些让他颔首微笑的对句了。正是在考虑和比较中,我们逐渐养成了润色打磨措辞的习气。
毕业后,我和妹妹先后做了小学语文西席,也算“子承父业”。祖母常说,我们是“鸭儿没有不会凫水的”——是的,这是父亲影响的结果,也是自小濡染古典诗词带来的职业选择。
现在,我正在用当年父亲勾引我们的思路和方法,辅导学生诵读和积累古代诗歌。看着学生用天籁般的声音诵读一首首幽美动人的诗歌,我彷佛又回到了充足美好的童年,向学生投以倾慕和幸福的目光,一如当年父亲看着我们读诗、背诗时的眼神。
(作者单位系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中国西席报》2019年10月30日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