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名之与实①,犹形之与影②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姝丽,则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上士忘名,中士扬名,下士窃名。忘名者,体道③合德,享鬼神之福佑,非以是求名也;扬名者,修身慎行,惧荣光之不显,非以是让名也;窃名者,厚貌深奸,干浮华之虚称,非以是得名也。
【注释】
①名:名声。实:本色,实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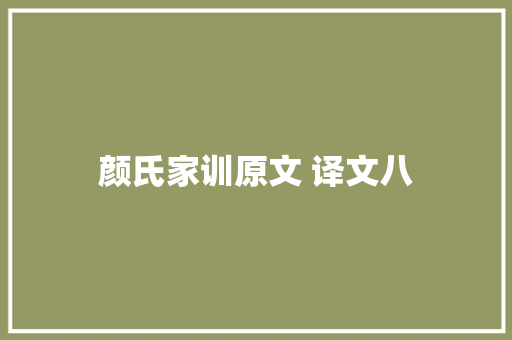
②影:指从镜子等反射物中反响出来的物体的形象。
③道:道理,规律。
【译文】
名声与实际的关系,就犹如形体与影像的关系一样。一个人的德行才干全面深厚,则名声一定美好;一个人的边幅颜色俊秀,则影像也一定俏丽。现在某些人不看重教化身心,却企求美好的名声外扬于社会,就好比容貌很丑陋却哀求俊秀的影像涌如今镜子中一样。上等德行的人已经忘掉了名声,中等德行的人努力树立名声,下等德行的人竭力盗取名声。忘掉名声的人,可以体察事物的规律,使言行符合道德的规范,因而享受鬼神的赐福、保佑,因此他们用不着去求取名声;树立名声的人,努力提高风致教化,慎重对待自己的行动,常常担心自己的名誉不能显现,因此他们对名声是不会谦让的;盗取名声的人,貌似虔诚而心怀大奸,求取浮华的浮名,以是他们是不会得到好名声的。
【原文】
人足所履,不过数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颠蹶①于崖岸,拱把之梁②,每沉溺于川谷者,何哉?为其旁无馀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诚之言,人未能信,至洁之行,物③或致疑,皆由言行声名,无馀地也。吾每为人所毁,常以此自责。若能开方轨④之路,广造舟⑤之航,则仲由之言信,重于登坛之盟,赵熹之降城,贤于折冲之将矣。
【注释】
①颠蹶:颠仆、跌倒。
②拱把之梁:即很小的独木桥。两手合围曰拱,只手所握曰把。
③物:即人。
④方轨:车辆并行。此处指平坦的大道。
⑤造舟:连船为桥,即今之浮桥。
【译文】
人的脚所踩踏的地方,面积只不过有几寸,然而在咫尺宽的山路上行走,一定会从山崖上摔下去;从碗口粗细的独木桥上过河,也每每会淹去世在河中,这是为什么呢?是由于人的脚阁下没有余地的缘故。君子要在社会上立足,也是这个道理。最老实的话,别人是不会随意马虎相信;最高洁的行为,别人每每会产生疑惑,都是由于这类辞吐、行动的名声太好,没有留余地造成的。我每当被别人诋毁的时候,就常常以此自责。你们如果能开辟平坦的大道,加宽渡河的浮桥,那么你们就能犹如子路那样,说话真实可信,胜似诸侯登坛缔盟的誓约;犹如赵熹那样,招降对方盘踞的城池,赛过却敌致胜的将军。
【原文】
吾见众人,清名登而金贝①入,信誉显而然诺亏,不知后之矛戟,毁前之干橹②也。宓子贱③云:“诚于此者形于彼④。”人之虚实真伪在乎心,无不见乎迹,但察之未熟耳。一为察之所鉴,巧伪不如拙诚,承之以羞大矣。白石让卿⑤,王莽辞政⑥,当于尔时,自以巧密;后人书之,留传万代,可谓骨寒毛竖也。近有大贵,以孝著声,前后居丧,哀毁⑦逾制,亦足以高于人矣。而尝于苫块⑧之中,以巴豆涂脸⑨,遂使成疮,表哭泣之过。旁边童竖,不能掩之,益使外人谓其住所饮食,皆为不信。以一伪丧百诚者,乃贪名不已故也。
【注释】
①金贝:指货币。
②干橹(lǔ):指盾牌。
③宓(mì)子贱:春秋末期鲁国人,名不齐。孔子学生。曾为单父宰。
④诚于此者形于彼:意思是在这件事上态度老实,就给另一件事树立了榜样。
⑤伯石让卿:指春秋时郑国的伯石假意推辞对自己的任命一事。
⑥王莽辞政:指东汉末王莽假意推辞不当大司马事。
⑦哀毁:居丧时因悲哀过度而危害身体。后常用作居丧尽礼之词。
⑧苫(shān)块:“寝苫枕块”的略称。古人居父母之丧,以草垫为席,土块为枕。
⑨巴豆:植物名。因产于巴蜀而形如菽豆,故名。
【译文】
我看世上有些人,在明净的名声树立之后,就把金钱财宝弄来装入腰包;在信誉显扬之后,就不再去信守诺言,不知道自己说的话自相抵牾。宓子贱说:“诚于此者形于彼。”人的虚实真伪本于内心,但不能不从他的形迹中显露出来,只是人们没有深入稽核罢了。一旦通过稽核来鉴别,那么,巧伪的人就不如拙诚的人,他遭受的羞辱就大了。春秋时期的伯石曾经三次推却卿的册封,汉朝的王莽也曾几次再三推却大司马的任命,在那个时候,他们都自以为事情做得机巧严密。后人把他俩的言行记载下来,留传万代,让人读后为之不寒而栗。最近有位大官,以孝顺有名,在居丧时,他悲哀非常超过了丧礼的哀求,其孝心可说是超乎凡人了。但他曾经在居丧期间,用巴豆涂抹脸部,从而使脸上长出了疮疤,以此表示他哭泣得多么厉害。他身边的童仆,却没有能够替他遮盖这件事,事情外扬出去,更使得外人对他在住所饮食诸方面所表露的孝心,都不相信了。由于一件事情作假而使得一百件老实的事情也失落去别人信赖,这便是由于贪求名声不知知足的缘故原由啊!
【原文】
有一士族,读书不过二三百卷,天才钝拙,而家世殷厚,雅自自持,多以酒犊珍玩,交诸绅士,甘其饵①者,递共吹嘘。朝廷以为文华,亦尝出境聘②。东莱王韩晋明笃好文学③,疑彼制作,多非心裁④,遂设宴言⑤,面相讨试。竟日欢谐,辞人满席,属音赋韵,命笔为诗,彼唐突⑥即成,了非向韵⑦。众客各自沉吟,遂无觉者。韩退叹曰:“果如所量!
”韩又尝问曰:“玉珽⑧杼上终葵首,当作何形?”乃答云:“珽头曲圜,势如葵叶⑨耳。”韩既有学,忍笑为吾说之。
【注释】
①饵:以困惑人。
②聘:旧时国与国之间通问修睦。
③韩晋明:北齐人。袭父爵,后改封东莱王。
④心裁(zhù):织布机,用以比喻诗文创作中构思和布局的新巧。
⑤宴言:指宴饮言谈。
⑥唐突:仓促,匆忙。
⑦韵:这里指文学作品的风格。
⑧玉珽(tǐng):即玉笏,为旧时天子所持的玉制手板。
⑨葵叶:指终葵的叶子。这里之终葵为草名。
【译文】
有位士家的子弟,读的书不过二三百卷,又天性迟缓笨拙,但他家世殷实富有,很有些骄矜自大。他时常拿出美酒、牛肉及宝贵的玩赏物来困惑结交绅士,凡是得到他好处的人,就争相吹捧他。朝廷也认为他才华过人,曾经派他作为使节出国访问。东莱王韩晋明,十分爱好文学,疑惑这位士族写的东西大都不是出自他自己的命意构思,就设宴同他交谈,打算当面试试他。宴会那天,气氛欢快和谐,文人才子们聚拢一堂,大家挥毫弄墨,赋诗唱和。这位士族也是拿起笔来一挥而就,但那诗歌却完备不是过去的风格韵味。众来宾都各清闲专心地低声吟味,就没有一个创造这篇诗歌有什么非常的。韩晋明退席后感叹道:“果真如我猜想的那样!
”韩晋明又曾经问他说:“玉珽杼上终葵首,那该当是什么样子?”他却回答说:“玉珽的头部波折圆转,那样子就像葵叶一样。”韩晋明是有学问的人,忍着笑对我说了这件事。
【原文】
指示子弟文章,以为声价,大弊事也。一则不可常继,终露其情;二则学者有凭,益不精励。
【译文】
帮助子弟修正修饰文章,以此抬高他们的声名,这是特殊糟糕的事。一则由于你不可能持续不断地替他们修正修饰文章,终归有露出真情的时候;二则由于初学者一见有了依赖,就加倍不去努力勤奋研讨了。
【原文】
邺下有一少年,出为襄国①令,颇为勉笃。公事经怀②,每加抚恤,以求荣誉。凡遣兵役,握手送离,或赍③梨枣饼饵,大家赠别,云:“上命相烦,情所不忍;道路饥渴,以此见思。”民庶称之,不容于口。及迁为泗州别驾④,此费日广,不可常周,一有伪情,触涂难继,功绩遂损败矣。
【注释】
①襄国:旧县名。公元前206年,项羽改信都县置,以赵襄子谥为名。
②经怀:经心。
③赍(jī):以物送人。
④别驾:官名。汉置别驾从事史,为刺史的佐吏,刺史巡视辖境时,别驾乘驿车随行,故名。
【译文】
邺下有一位年轻人,外放任襄国县令,他非常勤奋踏实,办公事尽心尽意,对下属体恤爱护,心愿以此博取好名声。凡碰上叮嘱消磨本地男丁去服兵役,他都要亲自前去握手送别,又向服役的人赠予梨子、枣子、饼干等食品,并对每个人揭橥临别赠言说:“上级的命令,有劳各位了,心中实在不忍心。你们路上饥渴,特备这点薄礼略表思念之情。”百姓们因此都很称颂他,对他赞不绝口。等到他升任泗州别驾,这类用度就一天多似一天,他不可能事事都做得面面俱到,一旦表现出虚情假意,就处处难以连续下去,过去建树的功业、劳绩也就随之被抹杀了。
【原文】
或问曰:“夫神灭形消,遗声馀价,亦犹蝉壳蛇皮,兽迒①鸟迹耳,何预于去世者,而贤人以为名教②乎?”对曰:“劝也,劝其扬名,则获实在。且劝一伯夷③,而千万人立清风矣;劝一季札④,而千万人立仁风矣;劝一柳下惠⑤,而千万人立贞风矣;劝一史鱼⑥,而千万人立直风矣。故贤人欲其鱼鳞凤翼,杂沓参差⑦,不绝于世,岂不弘哉?四海悠悠,皆慕名者,盖因其情而致其善耳。抑又论之,祖考⑧之嘉名美誉,亦子孙之冕服⑨墙宇也,自古及今,获其荫庇者亦众矣。夫修善扬名者,亦犹筑室树果,生则获其利,去世则遗其泽。世之汲汲⑩者,不达此意,若其与魂爽俱升,松柏偕茂者,惑矣哉!
”
【注释】
①迒(háng):兽迹。
②名教:指以正定名分为主的封建礼教。
③伯夷:商末孤竹君宗子。
④季札:又称公子札。春秋时吴国贵族。多次推让君位。
⑤柳下惠:即展禽。春秋时鲁国大夫。展氏,名获,字禽。食邑在柳下,谥惠。
⑥史鱼:一作史盪。春秋时卫国大夫,以正派敢谏著名。
⑦故贤人欲其鱼鳞凤翼,杂沓参差:意思是贤人希望天下之民,不论其资质禀赋的差异,都纷纭起而仿效伯夷诸人。鱼鳞,鱼的鳞片。此处形容密集相从。杂沓,浩瀚凌乱貌。参差,不齐貌。
⑧祖考:先人。生曰父,去世曰考。
⑨冕服:旧时统治者举行吉礼时所用的礼服。
⑩汲汲:心情迫切的样子。
魂爽:即魂魄。
【译文】
有人问道:“一个人的灵魂泯没,形体消逝之后,他遗留在世上的名声,也就像犹如蝉蜕下的壳,蛇蜕掉的皮以及鸟兽留下的足迹一样了,那名声与去世者有什么关系,而贤人要把它作为教养的内容来对待呢?”我回答他说:“那是为了勉励大家啊,勉励一个人去树立好的名声,就能够指望他的实际行动可以与名声符合。况且我们勉励人们向伯夷学习,成千上万的人就能够树立起明净的风气了;勉励人们向季札学习,成千上万的人就能够树立起仁爱的风气了;勉励人们向柳下惠学习,成千上万的人就能够树立起刚毅的风气了;勉励人们向史鱼学习,成千上万的人就可以树立起刚直的风气了。因此贤人希望世上芸芸众生,不论其资质禀赋的差异,都纷纭起而仿效伯夷等人,使这种风气连绵不绝,这难道不是一件大事吗?这天下上浩瀚的普通百姓,都是爱慕名声的,该当根据他们的这种感情而勾引他们达到美好的境界。或许还可以这样说:祖父辈的美好名声和名誉,也犹如是子孙们的礼冠衣饰和高墙大厦,从古到今,得到它的荫庇的人也够多了。那些广修善事以树立名声的人,就犹如是建筑房屋栽种果树,活着时能得到好处,去世后也可把恩典膏泽施及子孙。那些急急忙忙只知道追逐实利的人,就不睬解这个道理。他们去世后,如果他们的名声能够与魂魄一道仙游,能够同松柏一样长青不衰的话,那便是怪事了!
”
【评析】
《名实》篇紧张讲的是名不副实的问题。古代哲学家们曾经有过名与实的关系的谈论,也便是磋商事物的名称与客不雅观实在关系的问题。颜之推在这里谈论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干系的问题。他认为好的名声是由自己的“德艺周厚”、“修身慎行”而得来的,这是名副实在的好;而那些沽名钓誉者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浮名,是名不副实的,而且虚假的东西终归要败露的。
卷四 涉务第十一
【原文】
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①,以费人君禄位也。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②,经纶③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绝有谋,强干习事④;四则藩屏⑤之臣,取其明廉⑥风尚,明净爱民;五则义务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⑦节费,开略⑧有术,此则皆勤学守行⑨者所能辨也。人性有是非,岂责⑩具美于六涂哉?但当皆晓指趣,能守一职,便无愧耳。
【注释】
①左琴右书:弹琴读书。
②治体:指管理国家的系统编制、法度。
③经纶:此指处理国家大事。
④强干习事:精明强干,熟习事物。
⑤藩屏:藩篱屏蔽,比喻藩国。
⑥明练:明白清楚。
⑦程功:打算、考察工程的进度。
⑧开略:思路开阔。
⑨守行:品行端正,保持好的品行。
⑩责:强求。
【译文】
君子立身处世,贵在能够对旁人有益处,不能光是高谈阔论,弹琴读书,以此耗费君主的俸禄官爵。国家利用的人才,大概不外六种:一是朝廷之臣,为他们能通达政治法度,方案处理国家大事,学问广博,风致高尚;二是文史之臣,为他们能撰述典章,阐释彰明古人治乱兴革之由,使今人不忘前代的履历教训;三是军旅之臣,为他们能多谋善断,刁悍干练,熟习战阵之事;四是藩屏之臣,为他们能通达当地民风民俗,为政清廉,爱护百姓;五是义务之臣,为他们能洞察情形变革,择善而从,不辜负国君交付的外交义务;六是兴造之臣,为他们能计量功效,节约用度,首创方案很有办法。以上各类,都是勤于学习、保持操行的人所能办到的。人的资质各有高下,哪能强求一个人把以上“六事”都办得尽善尽美呢?只不过大家都该当明白其要旨,能够在某个职位上尽自己的任务,也就可以无愧于心了。
【原文】
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①古今,若指诸掌②,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③之下,不知有战陈④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⑤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晋朝南渡⑥,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⑦,有才干者,擢为令⑧仆已下尚书郎中书舍人已上,典章机要。别的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纤微过失落,又惜行捶楚,以是处于清高,盖护其短也。至于台阁令史⑨,主书监帅⑩,诸王签省,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须,纵有小人之态,皆可鞭杖肃督,故多见委使,盖用其长也。人每不自量,全球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丈,此亦眼不能见其睫耳。
【注释】
①品藻:鉴定等级。
②若指诸掌:像指示掌中之物一样,比喻道理浅近易明。
③庙堂:宗庙明堂,旧时帝王议事之处,故也指朝廷。
④战阵:作战的阵法。陈,“阵”的本字。
⑤肆:踞。
⑥晋朝南渡:指西晋被灭后,晋元帝于建武元年(317)南渡,在建康立东晋事。
⑦冠带:官吏或士大夫的代称,以其戴冠束带,因得称。
⑧令:即尚书令,为尚书省的主座。
⑨台阁:指尚书省。令史:尚书省属下的官员。
⑩主书:尚书省属下官员。监帅:监督军务的官员。
省:指省事、尚书省属官。
梁武帝父子:指南朝梁的君主梁武帝萧衍和他的儿子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
【译文】
我看世上那些弄文学的诗人,批驳古今,倒像是指示掌中之物一样平常明白,等到要用他们去干一些实事,却大都不能胜任了。他们生活在社会安定的时期,不知道会有丧国乱民的灾害;在朝中做官,不睬解战役攻伐的急迫;有可靠的俸禄收入,不理解耕种庄稼的辛劳;高踞于吏民之上,不明白劳役的艰辛,因此难得用他们去顺应时世,处理公务。晋朝南渡后,朝廷优待士族,因此江南的官吏,凡有才干的,都提拔他们担当尚书令、尚书仆射以下,尚书郎、中书舍人以上的官职,让他们掌管机要大事,剩下那些空谈文章的诗人,大都迂阔傲慢、华而不实,不打仗实际事务;纵然有一些小小过失落,也不好对他们施加杖责,因此只能给他们名声清高的职位,以此来掩饰笼罩他们的弱点。至于尚书省的令史、主书、监帅,诸王身边的签帅、省事,担当这类职务的都是熟习官吏事务、能够履行职责的人,个中有些人纵有不良表现,都可施以鞭打杖击的惩罚,严加监督,以是这些人多被任用,大略是用其所长吧。人每每不知自量,当时大家都埋怨梁武帝父子亲近小人而疏远士大夫,这也就好比自己的眼珠子看不见自己的眼睫毛一样,是没有自知之明的表现。
【原文】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①,大冠高履②,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③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④,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⑤。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⑥,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去世仓猝者,每每而然。建康⑦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喷陆梁⑧,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尚至此。
【注释】
①褒衣博带:宽大的袍子和衣带。
②高履:即高齿屐。
③周弘正:字思行,南朝学者,在梁、陈都做过官。
④果下马:在当时视为珍品的一种小马,只有三尺高,能在果树下行走,故名。
⑤放达:放肆不拘礼法。
⑥侯景之乱: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北朝降将侯景叛乱,攻破建康,梁武帝被困而去世。
⑦建康:即今南京。本名金陵,吴为建业,晋避愍帝讳,故改为建康。
⑧陆梁:跳跃。
【译文】
梁朝的士大夫,都爱好宽袍大带、大帽高履,外出乘坐车舆,回家凭靠童仆伺候,在城郊以内,就没见有哪个士大夫骑马的。周弘正这人被宣城王宠爱,得到一匹果下马,常常骑着它外出,满朝官员都认为他甚是放肆。至于像尚书郎这样的官员骑马,就会被人检举弹劾。到侯景之乱发生时,这些士大夫肌肤薄弱、筋骨柔嫩,受不了步辇儿;身体瘦弱、气血不敷,耐不得寒暑,在仓猝变乱中坐以待毙的,每每便是这些人。建康令王复,性情既温文尔雅,又从未骑过马,一看到马嘶叫腾跃,总是感到震荡害怕,对别人说:“这正是老虎,为什么要把它称作马呢?”那时的风气竟到了这耕田地。
【原文】
古人欲知稼穑①之困难,斯盖贵谷务本②之道也。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③,父子不能相存④。耕种之,盭⑤纣之,刈获之,载积之,打拂之,簸扬之,凡几涉手,而入仓埔,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江南朝士,因晋复兴⑥,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⑦僮仆为之,未尝目光起一盳⑧土,耕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馀物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⑨,皆优闲之过也。
【注释】
①稼穑:指农事。
②本:与下文之“末业”相对,本指农业,末指商业。
③粒:以谷米为食。
④存:惦记、省问。
⑤盭(lì):同“薅”,除草。
⑥复兴:西晋亡后,东晋又建国于江南,故称复兴。
⑦信:依赖。
⑧盳(máng):耕地时一耦所翻起的土。
⑨办:管理。
【译文】
古人打算理解农事的困难,这大约表示了重视粮食、以农为本的思想。用饭是民生第一件大事,老百姓没有粮食就不会生存,三天不用饭,恐怕父子之间也顾不得相互问候了。种一季庄稼,须要耕地、播种、除草、松土、收割、运载、脱粒、簸扬,经由多次工序,粮食才能够入仓,怎么可以轻视农业而看重商业呢?江南朝廷的士大夫们,是由于晋朝的复兴,渡江南来,末了客居异域的,到如今已过了八九代了,还从来没有下力气种过田,全靠俸禄生活。纵然有点田地的,都是靠童仆们耕种,自己从没有亲眼瞥见翻一尺土,薅一株苗;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播种,什么时候该收割,这样哪能懂得社会上的其他事务呢?因此他们做官不明吏道,理家不会经营,这都是生活清闲造成的差错啊。
【评析】
《涉务》篇阐述了要专心致力于事务,便是要办实事的意思。南朝的后期,门阀制度在南方已日趋没落,士族子弟险些都是金玉其外,败絮个中,没有几个能办实事的,因此朝廷不得不借庶族寒士来处理事务。士族出身的颜之推,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并对不办实事、形同废物的士族子弟进行了训斥。他旗帜光鲜地提出了士大夫处世要有益于社会的不雅观点,主见抛弃清高,求真务实,只有如此,于国于己才有好处。
喜好请转发点关注!
免责声明:文章素材和图片均来源于网络,同时文章仅代表本人不雅观点,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