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风莉
对付中国人来说,唐诗是无比瑰丽的艺术宝库,是无法企及的文化顶峰,是渴望自由与飞行的灵魂歌吟。
唐诗让我们忧伤,唐诗更让我们深刻。在一首首唐诗里,我们欣赏了山川与自然,品味了世情与悲欢。
唐诗,是汩汩奔流在中原文明中的新鲜血液;唐诗,是每一个炎黄子孙自然携带的遗传基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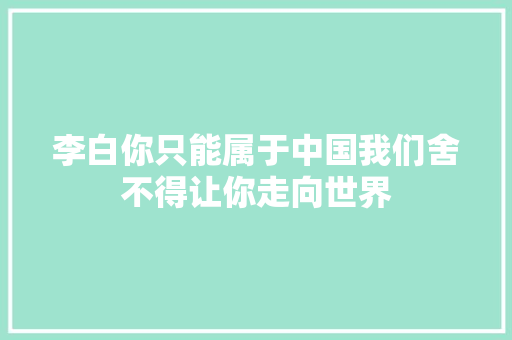
在浸淫唐诗的过程中,我们的内心在不断清醒。我们恍然惊觉,原来历史的纵深之处,蕴蓄着那么多光阴的柔情。
大江之水,终会东去;残酷唐诗,永不泯没。
如果要为光华夺目、物象万千的唐诗,保举一个形象代言人,他,只能是李白。
浪漫诗仙,原来是太白星下凡公元701年,李白出身。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一贯有多家之争。现在普遍认为,李白出生在唐时西域的碎叶城,即现在吉尔吉斯坦的托克马克。
至于李白一家为什么会到了西域,李白的族叔李阳冰的《草堂集序》记载:“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
李白的出生,还伴随着美好的传说。《新唐书》中记载:“白之生,母梦长庚星,因以命之。”
由此可见,李白之以是成为诗仙,是由于他本来就不是俗子凡胎。他是宇宙中最晶莹剔透的那颗太白星,一欠妥心陨落到了人间。
李白五岁的那一年,武则天去世。家人带着他从碎叶城回到了蜀地,定居在昌隆(今四川江油)的青莲乡。
唐时西域的碎叶,与龟兹、疏勒、于阗并称大唐的安西四镇。那块神异之地,不仅有吴钩霜雪,银鞍照马,还有星辰入梦。它们在西部流沙中彼此勾连呼应,演绎着浓浓的西域风情。
西域是旷达的,龟兹舞和西凉乐孕育了李白的艺术细胞;西域是自由的,没有任何东西来束缚你的身心;西域更是苍茫辽阔的,它能极大地引发一个人的想象力。
由于出生之地的影响,李白的脾气,自由来去,天马行空。他永久做不到勾留和稳定,他天生就有一颗不羁的心。
李白的生平,没有逼仄,没有局促,他的格局和视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明净、阔大与高远。
脚踏着西域的千里冰雪,脸拂着碎叶的万里长风,幼年的李白,从欧亚大陆的腹地走来,一步步走向了他的大唐母国。
白衣少年的心里,住着一个侠客
李白或许从未想过,他这辈子要成为一名精彩的墨客。由于他天生便是墨客,他具有天纵的才思,他根本不须要刻意地去学习写诗。
在家乡匡山,李白曾有过一段读书生活。但是他从朋侪学的多是纵横术,“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纵横家和侠客,习剑是必须的。李白不是自己在家里随便比比划划,他拜了天下最好的老师来学习剑术,他的师父是唐代第一剑客、人称“剑圣”的裴旻。
李白终极的击剑水平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对年夜方悲歌的侠客,心中的倾慕之情是不容置疑的。
笑尽一杯酒,杀人都邑中。
羞道易水寒,从令日贯虹。
——李白《结客少年场行》
最能表现李白的侠义情结的,则是他的《侠客行》一诗。这首诗曾被金庸作为他的长篇小说《侠客行》的开篇诗: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李白对侠客的神往称颂,不是由于他天性中的躁动与不安分,而是出于他对拯危救难、轻生重义、不图名利的侠客精神的无比景仰,以是他才在《侠客行》的结尾大赞曰:
纵去世侠骨喷鼻香,不惭世上英。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李白的这种侠义情怀,既来源于先秦的墨家思想,更受到了唐朝游侠之风的影响。
唐朝是一个甚有胡人气的朝代,连天子李渊都有胡人的血统。李世民的长孙皇后,也是鲜卑人,以是唐朝的很多热血男儿,心里都有一个仗剑行走天涯的梦。
而李白,做这个梦只是比别人更负责一点。
行吟江湖,用生命拥抱山水和自然
大凡墨客,没有谁能够像李白,对自然和山水那般热爱。在李白眼里,山水才是他永恒的爱人。得意时,山水陪伴着他;失落意时,山水亦陪伴着他。他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他应如是。
724年,李白二十四岁,他怀着“奋其智能,愿为首相,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入世思想,由家乡出发,开始漫游祖国,浪迹天涯。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李白《峨眉山月歌》
李白刚刚踏上远游的征程,看到峨眉山上升起的那轮明月,便不禁开始思念家乡。
和朋侪行至荆门,面前一片开阔。高山逐渐远去,江水奔流不息,月似明镜,云海变幻。在这个离去的夜晚,李白写下了《渡荆门送别》: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当行至江西,看到庐山瀑布水雾氤氲,景象奇伟,李白的心中激情澎湃,他的想象急速开始驰骋:
日照喷鼻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李白《望庐山瀑布》
当那轻巧的小船驶至天门山,看到碧水青山、白帆红日的绚丽画面,李白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雄奇壮阔深深震荡: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李白《望天门山》
742年,李白来到了长安,当他感想熏染了蜀道不可凌越的磅礴气势,他才知道了什么叫峥嵘突兀,什么叫刁悍波折。他也才知道,祖国的山水,原来不但是一种风格,惟其如此,才更显大唐江山的绮丽。
蜀道之难,难于上上苍,使人听此凋朱颜!
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
——李白《蜀道难》
当行至祁连山脚下,苍茫云海之间,一轮明月冉冉升起,李白想到了古时边防将士的防守之苦。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李白《关山月》
744年,李白遭受诬陷、被迫离开长安。长期的流落生活,使李白饱尝了世间的炎凉与酸楚,他的心中愈加增长了孤独落寞之感。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李白《独坐敬亭山》
李白的旷世孤独从来无人理解,他只好悄悄地凝望着敬亭山。由于他的心曲,只有大自然才会谛听,只有那永恒的山水才是他的知音。
在李白的生平中,没有人知道他到底翻了多少山,涉了多少水。我们只知道,李白一贯在路上。
如果没有看过这些风景,没有行过这些路途,李白便不会有一个阔大的生理空间,他的诗歌,便不会包罗万象,思接千里。
在摇荡多姿的山水里,李白照见了宇宙;而我们在李白的山水诗里,照见的是一颗高标于世、不染尘埃的灵魂。
两次求仕,皆是命运的捉弄
742年,李白终于等来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机遇。
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交口夸奖,唐玄宗不禁对李白发生了兴趣,便敕令召李白进宫。李白进宫那天,玄宗亲自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于前,并亲手调羹。
但是进宫之后,玄宗彷佛没有重用李白之意。他只是在嬉戏宴饮之时,须要李白陪侍在侧,随时记下他们的欢快时候。
一开始,李白对御用诗歌的创作是颇为上心的,他极尽才情,在玄宗面前表现。
云想衣裳花想容,东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李白《清平调·其一》
写着写着,李白发现不对劲了。原来玄宗只是把他当做一个高等文人,让他写诗逗他们愉快的。如果他写得好,玄宗有可能让他昔时夜唐的作协主席,但玄宗可能从来没想过,让李白昔时夜唐的宰相。
而李白偏偏对宰相有兴趣,却无意于作协主席。
于是,李白逐渐对写诗的事情懈怠了,玄宗在兴头上,常常找不到李白的人影。几次三番,玄宗便对李白失落去了耐心,他说:“此人固穷苦相,非廊庙器也”。
高力士和杨国忠等人,由于看不惯李白的特立独行,在玄宗面前不断地进谗言,李白以为呆在京城越来越没劲了。
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
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
——李白《忆东山二首》
李白想归去,他不知昔日种在东山的蔷薇又开过几次花,那堂前的明月又落入了谁家?
744年,李白上书傲娇裸辞,玄宗赞许赐金放还。
虽然看似从长安风光撤退,但初次求仕受挫,李白的心中,还是积满了压抑愤懑,他一口气写下了三首《行路难》。
行路难!
行路难!
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在《行路难》中,李白感叹了官场之阴郁,仕途之困难,以及自己的怀才不遇。但短暂的忧郁过后,李白的心头立时阳光残酷。他在大声地见告天下,我不会沉沦,我要连续扬帆出海,乘风破浪!
如果说李白第一次的求仕,是光荣的失落败,那么李白第二次对仕途的追逐,却差点儿丢了性命。
安史之乱爆发往后,唐明皇仓皇出逃,太子李亨登基。杜甫选择了追逐唐肃宗李亨,但“抚剑夜吟啸,年夜志日千里”的李白,选择了追随永王。
事实证明,李白这次是真的站错了队。当永王被唐肃宗打败,李白也因此开罪,被判流放夜郎。幸运的是,肃宗因立太子和大旱而大赦天下,李白遇赦得归。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李白《早发白帝城》
虽然这次政治的决议有惊无险,但李白终归是李白,当重获自由,他急速忘了先前的贬谪和打击,而是轻舟千里,豪情万丈。
即义务运屡次捉弄李白,但李白全不在乎。他依然高唱凯歌,一起向前,转头再向命运做一个鬼脸。
有什么能击碎一个天才的内心?那个天上的诗仙,人间若之奈何?
访道求仙,生平最爱老庄
作为诗仙的李白,和作为诗圣的杜甫有着根本的不同。杜甫从小接管的便是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诲,并且这种教诲已深入到杜甫的骨髓,成为他生平的追求。
来自胡地的李白,出身富商,由于家风和社会习俗的濡染,使他自幼崇尚道家,加上李白又有习剑任侠、学习纵横家的经历,以是李白的思想形态极其驳杂,有时乃至相互冲突和斗殴。
李白曾自言:“五岁诵六甲,十岁不雅观百家”,由此可知,李白对阴阳法术、诸子百家都甚有研究。但他最感兴趣、坚持终生的崇奉,只有道家。
玄门提倡洒脱出尘,鼓吹神仙天下,这种思想恰好迎合了李白热爱自由、不受羁束的性情。而现实生活中,又有那么多的阴郁与邋遢,这使得李白,更加强烈地舆想和追求一个美好的仙界。
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
五岳寻仙不辞远,生平好入名山游。
——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在崇信玄门的过程中,李白的身心不断地从尘凡俗世中拔离。他愈来愈脱去身上俗人的气质,而修炼了一身的风致高傲瘦骨如柴。
李白生平傲睨权贵,他唾弃封建等级制度,追求个性自由,他的这种狂放不羁的精神,紧张受了庄子叛逆思想的影响。
玄门还极其明显地影响了李白的诗歌创作风格。玄门为李白插上了精骛八极、神游四方的想象的翅膀,以是李白的诗歌具有一种恍惚高远、光怪陆离的神异色彩,形成了后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浪漫主义风格。
虽然李白崇奉玄门,深爱老庄,但李白中年期间曾“移家东鲁”,在鲁地先后“定居”二十年。鲁地乃儒家文化发祥之地,李白无疑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
以是,李白在崇奉玄门的同时,心中也怀着“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空想。只是他“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
屡次挫败之后,李白不得不躲到他的缥缈天下,寻求心灵的的平衡与超脱。
诗仙的日常标配,怎能少了美酒
“没有诗的人生是寂寞的,没有酒的诗歌是干涩的”。如果没有酒,李白的诗情就不会飞扬;如果没有酒,李白的笔下,就不会涌现盛唐的高华气候。
李白天资绝高,性情清奇,嗜酒如命。李白的粉丝杜甫在《饮中八仙歌》里这样写道: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李白认为,连天和地都爱酒,他自己嗜酒,有什么可责怪厚非的呢?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
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
——李白《月下独酌四首》
对诗才如仙的李白来说,酒是愉悦,酒是麻醉,酒是心灵最好的抚慰。
孤独到极点时,李白一个人饮酒,陪伴他的只有玉轮和他的影子。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季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看似李白在月下花前自斟自饮,及时行乐,但是仔细读来,我们读出的分明是万千寂寞。原来诗仙喝的不是酒,而是无法排解的孤独!
当然,李白也有快意称心之时,这时诗仙自然要狂歌痛饮: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故意抱琴来。
要说李白饮酒对写诗有什么好处,用李白自己的话来说,“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州。”
借助酒力,李白销愁壮胆,解脱了世俗礼法的束缚,冲破了常规的精神状态。“于畅怀通智、幻觉狂舞之际,思绪飘忽于天地之间,出入于古往今来,从而达到一种诗酒与生命激荡交融的境界”。
我们为什么痴爱着李白
一千多年以来,江山兴废万变,但李白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却从未改变。
自贺知章当年在长安见到李白,称李白为“谪神仙”的那一刻起,李白在世民气目中的形象就已经定型了。
作为诗仙和酒仙,李白的诗歌创作带有强烈的主不雅观色彩。从古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墨客像李白那样,在诗歌中强烈地表现和塑造自我,极力突出抒怀主人公的独特个性。
只有李白,尽情挥洒,从无遮饰;喜怒爱憎,形于笔端;纯洁任性,一派自然。
看到劳动人民的艰费力作,李白“一唱都护歌,心摧泪如雨”;看到权贵势要的跋扈屈曲,李白“手持一枝菊,谐谑二千石”;看到社稷倾覆、民生涂炭,李白“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
当年听到唐玄宗宣召,李白得意的“仰天算夜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被奸臣排挤出京,李白“乍向草中耿介去世,不求黄金笼下生”;面对“人生涯着不称意”,李白决定“明朝散发弄扁舟”!
不论处境和世事如何,李白终是那样的狂放,又是那样的本真。他认为做人紧张的是媚谄自己,以是他“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愉快颜”!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论及墨客与诗歌的关系时说:“墨客愈富诗性,其言说就愈自由。”由于个性的落拓不羁,李白的诗歌创作从来为所欲为,其作品自然而然地表现出,一种平凡墨客无法企及的境界和高度。
李白,才是那个最富诗性的墨客。
与李白比较,我们很多成年人都是堕落的儿童。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末了都活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样子,成熟却丑陋,但李白至去世还是那个纯洁可爱的样子容貌。
李白是时期的骄子,是盛世的歌手,是盛唐文化孕育的天才作家。“他以其独立的人格,非凡的自傲,豪放洒脱的气度和自由创造的浪漫情怀,充分表示了盛唐墨客的时期性情和精神风貌。”
李白的生平,便是盛唐的缩影;李白的魅力,便是盛唐的魅力。
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李白是乡愁的符号,李白是浪漫的代表。李白的身体在人间,灵魂却一贯在天上。无论我们若何踮起脚尖仰望,他高得我们永久够不着。
李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童年影象,他伴随了我们全体的生命发展。李白的生平,是一部天才的狂想曲,也是最自由、最出色、最宝贵的生命范本。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们都是李白的传人。李白,你是那样可爱,你只能属于中国,我们舍不得让你走向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