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杨万里的《宿新市徐公店》: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绿未成阴。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截图为部编版小学四年级《语文》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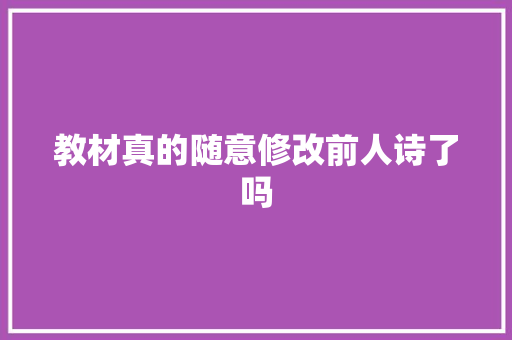
有的人就说,我明明记得是: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截图源自古诗文网
又比如说,李白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截图为部编《语文》七年级上册
有的人就说,我明明记得是: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截图为宋刻本《李太白集》
于是乎,就有人议论了:
截图为部分网友评论
截图为部分网友评论
然后问题就来了:到底是教材编写专家们随意纂改古人诗,还是当代人的误记,或者说是当代人的传统文化素养降落了呢?
我们先看第一首,杨万里的《宿新市徐公店》。
四部丛刊景宋写本《诚斋集》即作: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绿未成阴。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截图为四部丛刊景宋写本《诚斋集》
而清代嘉庆宛委别藏本《千家诗选》则作: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先绿未成阴。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截图为清嘉庆宛委别藏本《千家诗选》
而中华书局出版的《杨万里集笺校》,则和四部丛刊景宋写本的《诚斋集》一样:
截图自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杨万里选集》,也未见异文:
截图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杨万里选集》
综上所述,杨万里的《宿新市徐公店》未见异文,教材编纂并未有任何缺点。这大约是网友的误记。
再说一说李白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宋刻本《李太白集》(截图见前)作:
扬州花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宋代祝穆著《方舆胜览》则作: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说龙标过五溪。
我亦甘心寄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截图自宋刻本《方舆胜览》
宋代潘自牧《记纂渊海》所载此诗一如《方舆胜览》:
截图自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记纂渊海》
换句话说,在宋代,李白的这首诗便是有不同的版本的,无论是李白的集子,还是其他的文献,所记载的,都和现在盛行的不同。
康熙年间,缪日芭翻刻《李太白文集》:
截图为缪日芭刻《李太白集》,源自国家图书馆网站
扬州花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缪刻《李太白集》保留了“杨花落尽子规啼”。
清代王琦撰《李太白集注》,则作: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截图为王琦《李太白集注》,源自文渊阁四库全书
王琦采纳的是宋刻本,但是也保留了该诗的异文。
教材明确解释,这首诗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李白集校注》(见前截图):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李白集校注》正文中采纳的是“随风直到夜郎西”,但也注明了干系的异文。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李白的这首《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一贯以来就没有定本。
从诗意讲,随君优于随风。我们虽然说月白风清,但是就此诗来说,我已将相思寄托于明月,自然因此月为媒介,与风无关涉。
诗歌异文方面的终极选择,有一个原则:底本与参校诸本有异而非误者,一样平常以底本为据,不轻改底本;当底本存在误字、阙字、衍文、倒文,以及其他明显讹误的,有参校本可供订正者,则择善而从,改正底本。而当我们无法确定底本与参校本的利害的时候,我们一样平常会根据较胜的原则,即考虑到合理性和流传度,慎重选择。
这首诗在异文方面的终极选择,实际上还有一个中学生的接管能力的考虑。
综上所述,部编本教材并没有什么缺点,只是读者将自己的误记或者是知识盲区用来作为发泄情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