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写信,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可它正在离我们远去。在漫长的历史中,手写信是一种最紧张的沟通路子。古诗十九首动情的讲“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函。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去。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杜甫也感叹“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一封信道尽了写信人的顾虑,被韶光逐步地拉长,等递到收件人手中,已连成了长长的思念。现在我们已经不再写信了,科技改变了这个天下,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办法,当我们出于须要写一封邮件时,彷佛并不大在意信件中的称呼和其他的一些细节,只求把事情讲明白了就好。其实在我们的文化中,信件中的细节是极有讲究和韵味的。
朱自清《如面谈》一文中说:
有人说,日记书信里,最能见出人的脾气来,由于日记只给自己看,信只给一个或几个朋友看,写来都不造作。“不造作”可不是“信笔所之”。日记真不准备给人看,大概还可以“信笔所之”一下;信究竟是给人看的,虽然不能像演说和作论,可也不能只顾自己高兴,真的“信笔”写下去。“如面谈”不是胡帝胡天的,总得有“一点礼貌””也便是一份客气。客气要大方,恰到好处,才是味儿,“如面谈”是须要火候的。
这里的火候便是一封让收信人看信时心情舒适的关键,包含的学问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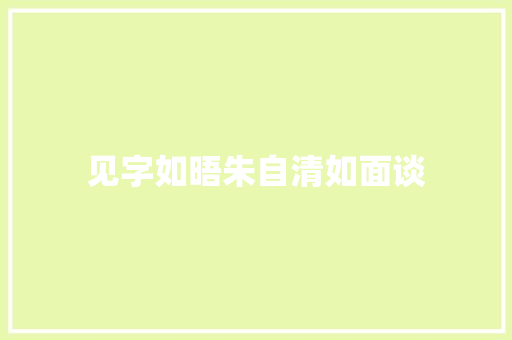
信件是写信人与收信人之间的私人发言,信件的格式决定了它的独特之处,没有了这种分外的格式,我们也就不能把它称之为信了。信件中最费心思的是头尾以及称呼。虽然现在口语文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书面语,但一些文言中的句子还是可以借用的。比如在信末的问候中:
如给父母去信,就须用“敬禀者”,“谨此”,“敬请福安”,给前辈去信,就须用“敬肃者”,“敬请道安”,给子弟去信,就须用“启者”,“专泐”,“顺问近佳”之类,用错了是会让人讥笑的——长者乃至于还会生气。
这些知识放在过去是一件微不足道又天经地义的事,可是在文言文已与我们十分生疏确当下,用的精确就成了一件锦上添花的事情。
其他的诸如结尾的称呼(写信人的自称),对女性的称呼,以及信件当中的领格,朱自清师长西席都在此文中逐一的谈到了。在不写信确当今时期,实在是补充了一些十分有趣又有用的知识。人与人之间的情绪是须要通过各种办法维系的,何妨去信一封以问安康呢?
原文节选:
五四运动后,有一段儿还很盛行称呼的西化。写口语信的人开头用“亲爱的某某师长西席”或“亲爱的某某”,结尾用“你的朋友某某”或“你的朴拙的朋友某某”,是常见的,近年来彷佛不大有了,纵然在青年人的信里。这一套大约是从英文信里抄袭来的。可是在英文里,口头的“亲爱的”和信上的“亲爱的”,亲爱的程度迥不一样。口头的得真亲爱的才用得上,人家并不轻易使唤这个词儿;信上的不论你是谁,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得来那么一个“亲爱的”用惯了,用滥了,完备成了个形式的敬语,像我们文言信里的“仁兄”似的。我们用“仁兄”,不管他“仁”不“仁”;他们用“亲爱的”,也不管他“亲爱的”不“亲爱的”。可是写成我们的笔墨,“亲爱的”便是不折不扣的亲爱的,在我们的措辞里,“亲爱”真是亲爱,一向是不折不扣的,因此看上去老有些碍眼,老觉着过火点儿;乃至还肉麻呢。再说“你的朋友”和“你的朴拙的朋友”。有人曾说“我的朋友”是标榜,那是用在公开的论文里的。我们虽然只谈不公开的信,虽然普通用“朋友”这词儿,并不能表示客气,也不能表示亲密,可是加上“你的”,大书特书,怕也免不了标榜气。至于“朴拙的”,也是从英文里搬来的。毛病正和“亲爱的”一样。当然,假如给真亲爱的人写信,怎么写也成,上面用“我的心肝”,下面用“你的宠爱的叭儿狗”,都无不可,不过本文是就一样平常程式而论,只能以大方为主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