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环球变暖的关系,你们有没有以为,秋日的存在感越来越低了。
每年秋日悄无声息地来,人们却浑然不觉,依旧我行我素地穿着单衣。
直到溘然有一天,凛冽的寒气逼迫人们裹上外衣,大家才意识到:
哎呀,是不是快立冬了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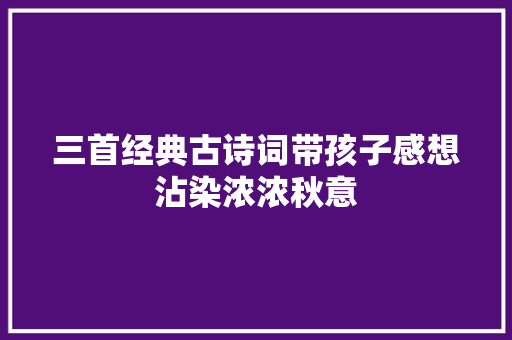
这样彷佛对秋日也太不公正了!
以是我本日特意挑选了三首有关秋日的经典古诗词:
张继《枫桥夜泊》
刘禹锡《秋词其一》
李白《秋登宣城谢脁北楼》
请大家带孩子一边读诗,一边感想熏染浓浓的秋意吧!
寓情于景可以说是古诗词最常用的手腕。
为什么呢?
由于古诗词讲究蕴藉、神韵,言有尽而意无穷,而寓情于景最能达到这种效果。
唐代墨客张继的这首《枫桥夜泊》便是寓情于景的典范。
枫桥夜泊
张继〔唐代〕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苏州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我们先看前两句: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玉轮已落下,乌鸦啼叫,寒霜满天,面对江边枫树与船上渔火,我忧闷难眠。
寓情于景的关键在于选择意象。
这首诗紧张写孤身一人流落的羁旅之愁,诗中的意象都是根据须要精心选取的。
我们来看前两句里的意象:
“月落”,月光本是清冷的色调,而当玉轮半沉,灰蒙蒙的光影,更给人一种寒冷、孤寂的觉得。
“乌啼”,一片安谧中数声刺耳的啼叫加倍显出夜的寂静。
“霜满天”,秋夜的寒意,从四面八方围向墨客,使他感到茫茫夜气中弥漫着满天霜华。
“江枫”,正如杨柳青青代表春天的活气,枫叶萧萧可代表秋日的肃杀,如白居易《琵琶行》诗云:枫叶荻花秋瑟瑟。
“渔火”,火本是温暖之物,但三三两两的渔火却更反衬出秋夜的凄清。
“对愁眠”,这三个字里也隐含一个意象,那便是不眠之人,所有这统统,都是一个失落眠的人的所见所闻。
为何失落眠?就落到了一个“愁”字上。
现在我们来看后两句:
苏州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苏州城外那寒山古寺,半夜里敲响的钟声传到了我乘坐的客船。
前两句诗写了六种意象,后两句诗却只写了一件事:夜半听到寒山寺的钟声。
这实在是一种动静结合的写法。
前两句中静态的的画面,溘然被夜半寒山寺的钟声掀动,整首诗也像画龙点睛一样活了起来。
在由静入动的一霎时,墨客的感想熏染变得非常尖锐。
钟声惊醒了墨客的心,原来压抑混沌的愁绪忽然变得清晰、不可躲避......
在这一刻,诗中的情与景完备交融。
中国的诗歌有漫长的传统,一门艺术韶光太长,就随意马虎僵化。
以是历代有追求的墨客都力争能打破古人的窠臼,写出自己的新意。
唐代墨客刘禹锡这首《秋词》便是个中的代表。
如果说张继的《枫桥夜泊》胜在韵,那么刘禹锡这首《秋词》就胜在力。
秋词其一
刘禹锡〔唐代〕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我们先来看前两句: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自古以来,文人墨客都悲叹秋日冷落,我却说秋日远远赛过春天。
“自古逢秋悲寂寥”,古诗有一个所谓的悲秋传统,这个传统可以一贯追溯到《楚辞》里宋玉的《九辩》:
悲哉,秋之为气也!
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由于有这个悲秋传统,古代墨客关于秋日的诗,难免一片惨惨戚戚之状。
刘禹锡偏偏一反常调,声称秋日远胜春天。
这两句诗大开大合,很有力量。
诗句怎么才能表现力量?
一个人扯着嗓子喊没有力量,力排众议、力挽狂澜才有力量。
力量要在对抗中展现。
比如岑参的边塞诗《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中有:
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
前两句渲染仇敌的强大,第三句“汉家大将西出师”,力量感一下就出来了。
现在看后两句: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秋日晴空万里,一只仙鹤排开云层平步青云,便引发我的诗情飞上云霄。
“晴空”“碧霄”,境界壮阔,“一鹤排云”,意象洒脱。
要特殊把稳“排云上”这三个字,这只鹤是排开云层的阻力飞上上苍的,一个“排”字,力量感就出来了。
这首诗是墨客被贬郎州后的作品,墨客借鹤自喻,表达自己面对困境的不屈与乐不雅观。
刘禹锡外号“诗豪”,果真不是浪得浮名。
古人写诗,非常讲究炼字。
所谓炼字,便是挑选最贴切的字来表情达意。
李白的五言律诗《秋登宣城谢脁北楼》便是炼字的绝佳示范。
这首诗作于天宝十三载,这年的秋日,李白从金陵再度来到宣城,登上了南朝墨客谢朓所建的北楼。
秋登宣城谢脁北楼
李白〔唐代〕
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
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
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
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
我们先来看首联:
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
江边的城池彷佛在画中一样俏丽,山色渐晚,我登上谢公楼远眺晴空。
王安石用“净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形容李白的诗,这两句就很有种这俊爽明快的觉得。
现在看颔联:
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
句溪和宛溪两条水,像明镜夹着宣城;凤凰桥和济川桥映着夕阳,好似彩虹一样落下。
这两句中的“夹”、“落”两个动词,便是在炼字了。
体会一下这两个动词带来的明快的画面感。
试想一下,如果改成“两水如明镜,双桥若彩虹”,就枯燥乏味了。
现在看颈联:
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
炊烟寒了橘柚,秋色老了梧桐。
我在译文里特意保留了诗句中的词类活用(形容词作动词),是不是有了一种方文山歌词的觉得:
你发如雪,凄美了离去......
有没有?实在方文山便是跟古诗词学的。
这两句是这首诗里的名句,个中的“寒”“老”更是古诗炼字的典范。
这种炼字手腕在古诗中比比皆是,如王安石的《泊船瓜洲》:
东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这句中的“绿”也是形容词活用作动词,是说“东风又吹绿了江南岸边景致”。
听说这句诗最早的版本是“东风又到江南岸”,王安石改了十几次,从“到”到“过”“入”“满”,才终极确定为“绿”,古人炼字时精益求精的精神可见一斑。
现在看尾联:
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
有谁知道我在这北楼上,迎着萧瑟的秋风,怀念谢公呢?
尾联点题,这北楼是谢脁所建造的,从登临到怀古,彷佛是照例的公式,看起来李白不过顺口说了句怀念古人的话罢了。
但是,请把稳“谁念”二字:有谁知道我在这里怀念谢公?
独自一人怀念谢朓,就跟端午节大家一起怀念屈原不同了。
当世没有心腹,我只好怀念古人,只有他与我遭遇相同、心意相通。
李白是在用怀古的办法,表达自己的怀才不遇的失落意惆怅。
EASTWEST
总结一下:
在这三首诗中,我提到了:
寓情于景是古诗常用的手腕。
写景时动静结合每每可以画龙点睛。
精彩的墨客总是在试图打破传统,写出新意。
诗句的力量感要在对抗中展现。
古人写诗讲究炼字,词类活用是常用的手腕。
这三首关于秋日的诗,你和孩子最喜好个中哪一首呢?
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互换~
文章图片:采集于网络,仅作学习互换利用,版权归图片作者所有,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