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期间,老北京城里有所谓的五子行,说白了便是供人们休闲找乐的地。何谓“五子”?便是戏园子、剃头挑子、澡塘子、窑子、饭铺子。
老年间这澡堂子给划进了五子行,按过去的说法儿,是“三教九流”中的下九流,社会地位低下。进澡堂子的人们除了个人卫生外,最紧张的是休闲和享受。在老北京的澡塘子就130多家儿。“金鸡未叫汤先热, 红日初升客满堂”便是大多数浴池门口挂的对联,您瞅够有多生动。
提及澡堂子的历史,《京都梦华录》中说,宋朝都城汴梁,甜水巷有浴堂。据史资料上说,北京最早的浴堂,在今西四附近,堂名为“涌泉堂”,开业于顺治年间(1660年前后),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再往远里说,屈原在《九歌·东皇太一》中就有“浴兰汤兮沐芳”的诗句,说的是在水里浸入兰草,入浴个中可以沐芳馨,可见当时沐浴已很讲究。唐玄宗在骊山造华清池,以沉喷鼻香在池中砌成假山,为贵妃杨玉环洗澡专享。不仅画家笔下有《出浴图》,大墨客白居易也写下了:“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典膏泽时……”可见这沐浴是一种清闲般梦幻的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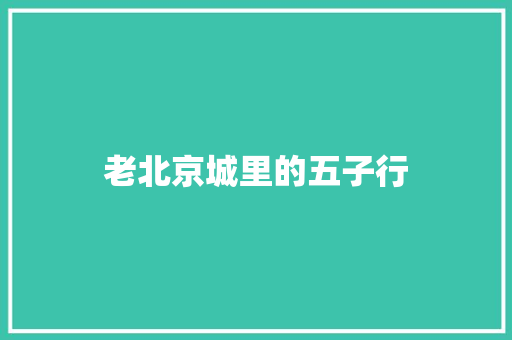
据老人们回顾,有个浴德堂是元代所建,堂东侧有一“弓”型曲廊,连接着换衣处和沐浴处,曲廊起到了暗藏和保温的双重浸染。换衣处原有一喷鼻香妃戎装画像。沐浴处系一砖构造的圆顶形建筑。墙身为方形,两米高以上为圆形,拱为半球型。曲廊的拱型圆顶窗上镶八块彩色玻璃,起着沐浴时采光照明的浸染。设计很风雅,无论是朝阳初升,还是夕阳将落,室内都可有阳光进入。在室内的东北处地面上有一排水口,为室内最低处,可将沐浴过的污水排净。北墙上有一贯径50毫米的进水管。墙外是一呈蒙古包型的烧水设备,外有保温层,水从井亭的水槽而来,在此加热后送入墙内,以供沐浴。
听说这浴德堂是乾隆天子诏封喷鼻香妃时所设立的。因喷鼻香妃信奉伊斯兰教,做星期需先沐浴净身,特在武英殿内设沐浴场所和星期场所,御赐为“浴德堂”。
从前间,老北京人管沐浴叫“泡澡堂子”。您进得澡堂子,操着河北口音的伙计便开始呼唤“呦,张爷,几位您”,“两位”,“张爷来了,里面请”、“您找刘二爷,怹里边儿泡着哪”。到澡堂子的主儿都先不忙洗,得找个地界儿落座宽衣,取出茶叶倒在壶中,叫伙计沏好先闷上,这才入池。
泡澡是一大享受,过去的澡堂子分池塘和盆堂,池塘又分温池、热池和特热池,论年纪喜好在不同的池子里泡着,小孩一样平常温池,特热的池子是给老年人预备的。而盆堂一样平常是有钱人享用,单独的房间,有伙计在一边儿奉养着。
北京的爷儿进澡塘子没有不泡澡的,泡过澡没有不搓澡的,搓完了没有不修脚的。您往池子里一泡,泡的全身大汗、遍体通红、蒸气绕体、神经松驰、筋骨伸展,再叫个搓澡师傅给您浑身高下那么一搓,既净洗净了身体又舒了筋活了血。临了,您再一冲,等回到小床要茶已沏好,那叫滋润津润!
到了中午再要点儿点心,睡个午觉切实其实悠哉游哉的入了瑶池。现在没有这个景儿了,就算是高等的洗澡中央,也没有了昔日的闲在和清闲。
现在能记得起来的澡堂子,鲜鱼口的兴华池、廊房头条劝业场的暗香圆儿、珠市口儿的清华池,虎仿桥路东的虎仿桥浴池,王府井北边儿八面曹的清华园。
从前间的澡堂子准备木拖鞋(也叫趿拉板)、丝瓜瓤子和搓脚石。伙计们之间说话用的是谁也听不懂的行话,如管理发叫“剪尖”,管帽子叫“顶天”,管腕表叫“转芯”,管刮脸叫“赶盘”,管热水叫“漂汤”,管温水叫“平汤”,管盆塘叫“小汤”
还有便是沐浴得先买澡票,我记得池堂沐浴是两毛六,盆堂是五毛五。卖澡票的小窗口里,还卖各种各样的洗漱用具,如果不愿意用澡堂的肥皂,花几毛钱买一小包洗头膏,但那个年代是绝没有浴液这等老什子的物件儿的。
澡票实在是块竹牌,竹牌上涂了一层光亮的清漆,竹牌上用羊毫写着些 “淋浴”、“盆塘”什么的字。竹牌的顶头儿用蓝、红漆,表示“慢洗”和“快洗”。慢洗会有一张床,一个带锁的衣柜。洗过之后也可以搓背、修脚。洗完了,您可以买一包茶叶叫做事员给您沏上一壶,然后您就四脚八叉的尽情的瞌睡儿、喝茶、看报、吸烟、谈天儿,什么时候您腻味了穿衣服回家。而“快洗”,也叫“脱筐”,快洗的主儿每人供应一个竹筐,用来装衣服而已,进去就脱,脱完就洗,洗完就走。我的影象里,快洗一样平常是周末或节日前沐浴的人多,须要排队的时候才会有。
北京人有句老话儿“澡堂子的拖鞋,没对儿”。这澡堂子里的拖鞋全是一顺边儿,便是怕被人顺手牵羊记得我去的最多的是王府井的清华园,花五毛五去洗盆堂,也是非常遐意的。
现而今,险些家家儿都有浴室,不济的也要在厕所里安个喷头,而街面儿上的澡堂子也都叫洗澡中央了,这些老事也就都成回顾了。
老北京有句口头语叫“饱沐浴、饿剃头”。从前间剃头的讲究儿挺多,除了刚说的“饱沐浴、饿剃头”,还有“正月里不能剃头”的禁忌。每到年前,这家里有舅舅的主,要不主动,要不就被家里人催着,赶紧头年儿把头剃了,放着舅舅的事承担不起不说,这要疯长一个月不成了长毛靼子了。以是每到头年儿,这京城圈子里的理发挑子、理发馆的师傅可就忙开了,师傅的手虽然剃的抽了筋,但心里却是乐开了花儿,头年儿您理发,我发财啊。
咱们再把话往长里说,在古代,这头发可不是随便剃的,老话说的好,《孝经》就说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后来朝代不同,推头的叫法儿也不同,明代叫“篦头”,明朝那起儿,有“篦头匠”,用块布包着工具,替人篦头。在皇宫内,则有专门的篦头房,“近侍十余员,专为皇子、皇女清发、留发、入囊、整容之事。”咱们现在说的“推头”是从清代开始这么叫的。
要提及剃头,这老北京自打清朝入关那起儿是免费的,不是有这么句话吗“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汉人个个都得按规矩把头剃了,留起发辫,要不您要舍不得头发,哪您就把脑袋放下。您说,头发又当不了饭吃,留着脑壳还喂食儿哪。以是清朝入关那会儿,剃头留辫子该当是个政治任务,听老人们说,那时剃头的地方叫官棚,剃头不要钱。
根据史料记载:清朝入关往后,敕令剃发梳辫,遭到汉民反对。直到入关一年往后,南京明弘光小朝廷覆灭,清政府为了统一全国公民的家冠装扮服装,于1645年8月(顺治二年七月)再敕令强制公民一律剃头梳辫,并限十天内全国公民全部剃头,违反或躲避者,杀无赦!
北京是都城,对这项命令实行得更严。摄政王多尔衮敕令派包衣三旗的剃发匠在地安门、东四、西四、正阳门等紧张路口,搭起席棚,内供清帝诏书牌,凡过往行人有留发者,便拉入棚内强行剃头,违反者当场杀去世,把人头悬在棚杆顶上示众。当时这种剃头棚,全是实行命令的官棚,不收用度。
要论起来,这京城推头的行当以顺义、武清、三河、喷鼻香河、宝坻人的最多。剃头挑子又分为了“下街挑子”和“桥头挑子”。下街的拿着“唤头”走街串巷,“桥头挑子”是在桥头放个摊子。
据资料记载,这剃头讲究挺多。什么梳、编、剃、刮、捏、拿、捶、按、掏、剪、剔、染、接、活、舒、补。学剃头的小徒弟儿,那得先在冬瓜上炼,用剃头的刀子,削冬瓜皮。
别小瞧这剃头,与它有关的俚语还真不老少,什么“剃头的骂街——头儿着的”;管领导叫“头儿”;“剃头的砸挑子——不给头儿干了”。“猪八戒剃头——道儿太多。”老年间的剃头挑子没有了,美容美发的发廊多了。这从前的事儿,也就剩下回顾了,大概这样才故意思吧。
再说说老北京的戏园子,清代是戏楼的壮盛期间,这与清朝历代帝王无不喜好戏剧有关。但在清朝,清政府明文规定"内城道近宫阙,例禁鼓噪",南城为盛,清末京师南城的12个戏园子是大栅栏内的:三庆园,同乐园,广德楼,庆乐园,庆和园,中和园,粮食店街的中和园,肉市口的广和楼,鲜鱼口的裕兴园,天乐园,杨梅竹斜街的庆春园,崇文门外的广兴园,宣武门内的庆顺园。
还有内城隆福寺的景泰园,东四牌楼的泰华园,西四牌楼的万兴园(杂耍),外城齐化门外的芳草园,隆和园,德胜门外的德胜园,平则门的阜城园,外城的四个是小戏院。
清乾隆年间,北京城有七家戏园子特殊有名,号称七大名园,位于大栅栏的三庆园便是个中之一。别的六家是肉市街的广和楼,大栅栏的广德楼、庆和园、同乐园、庆乐园和三庆园阁下的中和园。四大徽班进京后,只在这七家戏园子演出,因此这里可以说是京剧的发祥地。
老北京的戏园子与本日的戏院不同,最早是由茶园发展起来的。起初,人们在这里品茗为主,听戏为辅,因此茶园只收茶资,不卖戏票。可是随着京剧越来越火,人们变成了听戏为主,品茗为辅。茶园也就逐渐变成了戏园子。
老戏园子一样平常开在临街,门前竖个木制牌坊,坊额上写着某某园。戏台分正方形和长方形两种,面历年夜约五六十平方米。戏台三面有矮栏,四角有明柱支撑台顶,为了达到拢音效果,台顶一样平常都有藻井。
老戏台三面都设有座位,看台一样平常是两层。一楼正对着舞台的叫“池座”,舞台两侧叫“两厢”,“两厢”后面靠墙的高木凳叫“大墙”;楼上的座位叫“楼座”,前面为“包厢”,两侧叫“后楼”。与本日戏院不同的是,戏园子的“池座”并不正对舞台,而是与舞台垂直摆放。不雅观众两两相对,坐着边喝茶边听戏,要想看戏还得扭头。正因如此,从前间老北京人都说“听戏”,而非“看戏”。那时候,谁要说去“看戏”,还会被当成生手,遭人讥笑。
戏园子的兴起,带动了许多周边做事业。清末,戏园子演出动辄十个小时以上,不雅观众看到半截儿饿了,不少饭庄都有外卖送进包厢。包厢里的不雅观众大鱼大肉地大快朵颐,散座的不雅观众也可以从现场小贩手里买到包子凉糕等小吃,垫巴垫巴。最有老戏园子特色的做事则是高下翻飞的手巾把儿。夏天不雅观众们看得大汗淋漓,此时用热毛巾擦把脸最舒畅不过。打手巾把儿的洗好了一把10条毛巾,从一楼扔到二楼,上面有人接着,一接一个准,一边扔还得一边吆喝:“手巾把来喽!
”台上咿咿呀呀,台下人声鼎沸,此乃老戏园子的一大特色。不过,场面虽然热闹,却也严重影响了演员的演出和不雅观众的不雅观看效果,因此这些习俗随着新兴剧院的兴起,逐渐消逝了。
民国初年,位于西珠市口的“第一舞台”,率先冲破了老戏园子的格局。“第一舞台”在当时首创了好几个“第一”。第一个利用灯光布景;第一个演出晚场夜戏;第一个打破了男女分座的边界;第一个将不雅观众席正对舞台,变成了横排长条木椅;第一个没有台柱子;第一个利用幕布;第一个对号入座……第一舞台的诸多创举,令不雅观众们线人一新。它的涌现率先将老戏园子改造成了当代的戏院。第一舞台建成后,杨小楼、梅兰芳等许多名角争相在此登台献艺,一韶光风头无二。可惜的是,1937年一场大火将第一舞台付之一炬,再也没有复建。不过,第一舞台首创的风气,却影响了一大批老戏园子顺利转型。许多戏园子都效法第一舞台的格局,改扩建成当代戏院。三庆园、广德楼等传统名园,一贯将老格局保留到上世纪20年代,才不得不与时俱进,改变风格。
如今,许多老戏园子原址复建,规复了演出,同时,也复活了老北京兴盛一时的市井文化影象。
窑子是我国古代最直接最低下的性交易场所。每每是在一个破草屋内,交易的工具大多是社会最底层的男男女女,交易的凭借亦不过是几文钱、几斤米。
嫖客大多是穷诗人、小混混等一介草民因没有固定性工具而寻求少焉性的乐趣,也有生活腐败的阔少。窑姐大多为了养家糊口,坚持生存,她们别无选择。
逛窑子,指冶游。在古代,便是妓院 ,有钱人去玩的地方。 当代便是指 所谓的"发廊" 、洗头城。春秋期间的男人逛窑子,借口是相应"政府号召",由于齐国的国相管仲设立了"公娼",号召男人有事没事时都来走走,在财政上多多增援国家培植。到了唐宋期间,男人逛窑子的借口得到了进一步升华,更加具有文化色彩,更加重视情趣和品位。青楼的妓女为了迎合男人的这种升华,她们一改过去的没文化,在诗词歌赋、吹拉弹唱高下功夫,而且摒弃礼教束缚、脾气放荡,成了女人中的佼佼者,男人心目中最可爱的人。所谓文人爱妓女,正是这样的结果使然,并不是文人集体下贱,而是除了妓女有些文化、可以沟通之外,当时实在没有其他的女人可以与文人擦出火花。
提及老北京的妓院,人们首先会想到八大胡同。所谓八大胡同,并非某一条胡同的名称,而是由八条胡同组成的,位于前门外大栅栏附近,因妓馆密集而成一大销金窟。《京都胜迹》一书引用过当时的一首打油诗曰:
“八大胡同自古名,陕西百顺石头城(陕西巷口的百顺胡同、石头胡同)。韩家潭畔弦歌杂(韩家潭),王广斜街灯火明(王广福斜街)。万佛寺前车辐辏(万佛寺系一小横巷,西通陕西巷,东通石头胡同),二条营外路纵横(大外廊营、小外廊营)。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胭脂胡同)。”
评论辩论妓女,是比较敏感的话题。但在旧时期,妓女也包括在三教九流的范围之内,与贩夫走卒无异。因而我辈在梳理城市的往事时,彷佛大可不必刻意回避。
虽然唐宋的墨客(譬如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以及善于写“花间词”的柳永)与妓女的关系很密切,但妓女的影子仍旧很难登上大雅之堂,顶多属于“民间团体”罢了。到了元朝,取代柳永地位的是关汉卿,他作为当红的词曲作家出没于娼寮瓦肆之间,与媚眼频抛的歌伎舞女们打情骂俏。关汉卿成长于元大都,堪称正宗的“老北京”了,他在脂粉堆里一样能找到大腕的觉得。
对妓女的记载一样平常只能见之于野史之中。恐怕要算《马可·波罗游记》,较早先容了北京地区(时称元大都)妓女的规模与状况。马可·波罗说,新都城内和旧都(金中都)近郊操皮肉买卖的娼妓约二万五千人,每百名和每千名妓女各有一个特设的官吏监督,而这些官吏又服从总管的指挥。给人的觉得是,元大都对妓女也实施半军事化管理,而督察大员则相称于百夫长或千夫长,行之有效地统率着天子脚下的红粉军团。
妓女乃至进入了这个欧亚大帝国的外事(外交)领域:“每当外国专使来到大都,如果他们负有与大汗利益干系的任务,则他们照例是由皇家招待的。为了用最头等的礼貌接待他们,大汗特令总管给每位青鸟使每夜送去一个高档妓女,并且每次一换。派人管理她们的目的就在于此。”妓女的“觉悟”彷佛也挺高,“都认为这样的差事是自己对大汗应尽的一种责任,因此不收任何报酬”。不知马可·波罗统计的妓女数目是否有夸年夜的身分?个中是否包括未正式注册登记的暗娼?而“卖淫妇除了暗娼以外是不敢在城内业务的,她们只能在近郊附近拉客营生,无数贩子和其他乘客为京都所吸引,不断地往来,以是这样多的娼妓并没有供过于求”。看来那是一个“性解放”的时期。不过在当时,除了元大都之外,全天下恐怕没有第二座城市能养得起如此弘大的妓女军队。元大都的“客流量”真是太可不雅观了。
明朝的北京,红灯区又是什么样的呢?听说,导致吴三桂冲冠一怒的红颜陈圆圆,便是“三陪女”出身:“姓陈名沅,为太原故家女,善诗画,工琴曲,遭乱被掳,沦为玉峰歌伎,自树帜乐籍而后,艳名大著。凡买笑征歌之客,都唤她做沅姬。身价既高,凡侍一宴须五金,为度一曲者亦如之。走马王孙,坠鞭公子,如蚁附膻,大有车马盈门之势。即词人墨客,凡以诗词题赠沅姬的,亦不可偻指算。”后来,崇祯天子驾下西宫,国丈田畹,以千金购之,将其包养起来。再后来,吴大将军去田府串门,一见圆圆,惊为天人,爱得要去世要活。
明清两朝,天子都住在紫禁城里,妻妾成群。紫禁城俨然已成最大的“红灯区”。大红灯笼高高挂,只不过三千粉黛,都是为一个人做事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宫女无辜(虽然也会争风吃醋“抢买卖”),天子才是天底下最贪婪最无耻的“嫖客”。明帝大多短命,想是太沉溺于女色的缘故。而清帝中,乃至出过以为家花不如野花喷鼻香,微服私访去逛窑子的人物,个中闹得最出格的是同治帝,也便是那个葬送大清帝业的老佛爷慈禧的孩子,他脱下龙袍换上布衣,让小寺人扮作仆人,频频光顾八大胡同,跟上了瘾似的。结果染上梅毒,十八岁暴卒。既误国,又亡身,可见家教不严,德不配天。
在晚清,要说名妓当是赛金花了。赛金花绝对属于“另类”,她生于徽州,长于烟花巷陌,遇见大状元洪钧,就从良了。虽然只是妾,她却以夫人身份随洪钧出使德、俄、荷、奥四国,算是出过远门,见识了表面的十丈软红(乃至拜晤过维多利亚女王与威廉天子),很出风头的。自外洋归来,因洪钧已逝,家中断炊,就重操旧业。陈宗蕃《燕都丛考》记载:“自石头胡同而西曰陕西巷,光绪庚子时,名妓赛金花张艳帜于是。”以昔状元夫人及外交官夫人之身份倚门卖笑,本来就适宜作为花边新闻炒作,赛金花的“买卖”一定很不错,弄不好还能成为巴黎茶花女式的传奇。偏偏赛金花天生是盏不省油的灯,又卷入了更大的是是非非: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期间,她与德帅瓦德西闹了场满城风雨的“跨国之恋”,真不知她怎么想的。
民国后,袁世凯担当临时大总统,为八大胡同火上浇油。他脱手很“大方”,花高价收买参、众两院八百名议员(号称八百罗汉),每人月薪八百块现大洋。而国会的会址位于宣武门外象来街(今新华社)。“钱来得随意马虎也就花得高兴,南城一带产生了畸形的繁荣,许多商界、娼界的人士直至四十年代还津津有味地谈起‘八百罗汉’闹京城时的盛况。古有饱暖思淫欲之说。‘八百罗汉’酒足饭饱之后,当然不乏有些弄柳拈花的青楼之游。位于前门、宣武门之间的八大胡同是北京的红灯区,许多妓院竟然挂出了‘客满’的牌子。”这段笔墨,见之于方彪著《北京简史》。八大胡同,竟然“载入史册”了。
八大胡同曾是赛金花“重张艳帜”之处,但毕竟出了小凤仙那样真正的义妓。袁世凯复辟称帝期间,滇军首领蔡锷身陷虎穴,为摆脱监控,假装醉生梦去世,放荡不羁于八大胡同,因而结识了出污泥而不染的小凤仙。小凤仙胆识过人,掩护卧薪尝胆的蔡将军躲避了盗国大贼的伤害。“一九一六年,一个叫蔡松坡(蔡锷)的人,在云南举行了倒袁叛逆,打碎了袁世凯的称帝美梦。这位蔡锷的名字永存于北海西北角的松坡图书馆。面对蔡锷的叛逆,袁世凯方案已久的君主制度像一枕黄粱般破灭了”(林语堂语)蔡锷为中国的民主制度立下汗马功劳,个中似应有小凤仙的一份,多亏她助了一臂之力。古人常说英雄救美人,可这回却是沉沦腐化风尘的美人救落难的英雄。
根据《燕都往事》一书引用的资料:“民国六年(1917年),北平有妓院三百九十一家,妓女三千五百人;民国七年(1918年),妓院增至四百零六家,妓女三千八百八十人。民国六七年间,妓院之外私娼不下七千人。公私相加,妓女就在万人之上了。民国十六年(1927年),都城南迁,北平不如过去繁荣,妓院、妓女的数字也随之低落。民国十八年(1929年),北京头等妓院有四十五家,妓女三百二十八人;二等妓院(茶肆)有六十家,妓女五百二十八人;三等妓院(下处)一百九十家,妓女一千八百九十五人;四等妓院(小下处)三十四家,妓女三百零一人。以上共计妓院三百二十九家,妓女三千零五十二人。但实际上暗娼的数字很大,真正妓女的数字比这大得多。”听说妓院的房间很矮小拥挤,跟鸽子笼似的,只能放下一张床及一桌一椅。那里面收容着烟花女子们扭曲的人生。
妓院分三六九等,个中的头等者,硬件举动步伐要高档一些,乃至很豪华,可以想见其门前车马鼓噪的情景。而百顺胡同,便是精装修的头等妓院之集中点,专为上流社会供应做事的。譬如四十九号,是个四面环楼的院落(属于另类的四合院),“每面四间房,楼上共十六间,楼下也是十六间,每间房均十平方米大。有个楼梯通到楼上,楼梯还结实,楼上还有雕花的栏杆。看了这个头等妓院,可以想象从前这里妓女倚门卖笑,过着纸醉金迷生活的样子,从这里散发出来的污浊空气堕落着全体北京城。”
头等妓院除了经营“老本行”,额外还供应餐饮游乐,堪称全方位的做事。韩家潭二十七号,即叫做“清吟小班”的地方,“门口上面有个名叫李钟豫的人题了‘庆元春’三字,是这家妓院的名字。这里院子比较宽畅,只有南北两面有两层楼房,每面都是楼上四间,楼下四间,两面共十六间房,屋子比二等妓院要好一些,每间约有十平方米。这是富人们的销金窟,除了可以冶游外,吃得也不错,经由修理的楼梯上还钉着一块‘本庄寄售南腿’的木牌,证明从前这里的饮食水平。”连金华火腿都成为一大招牌了。只是,闻风而至的公子王孙,并非真的垂涎于此地之炊事,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在乎美人之玉腿。
值得一提的是,这花枝飘荡的韩家潭(今名韩家胡同),曾是闲散文人李渔的隐居之地。“他生于明清之际,进北京似在入清往后,请张南垣为他在韩家潭垒石蓄水,仍以他在金陵的别墅‘芥子园’为名,题楹联曰:十载藤花树,三春芥子园。”芥子园,恐怕可能是八大胡同地带惟一的文化遗迹。放荡不羁的李笠翁,纵然挟妓醉饮,也不会怎么酡颜的。他老人家并不在乎与八大胡同的秦楼楚馆为芳邻,不在乎后人说闲话。
自古言:饱暖思淫欲,孔役夫曾断言:食色性也。在老北京饭铺子也别有帝都的派头。北京的饭庄有约定俗成的规矩。叫堂的最大,所谓堂,是既可办宴会,又可以唱堂会,饭庄里不仅有桌椅,还有舞台和空场,很是派头。最早的堂一样平常都在皇城周围,比如金鱼胡同的隆福堂、东皇城根的聚宝堂、打磨厂的福寿堂、大栅栏的衍庆堂、北孝顺胡同的燕喜堂,以及东单不雅观音胡同的庆惠堂和前门外樱桃斜街的东麟堂两家冷饭庄,无一不是如此。
比堂略小的才叫庄,再次之的叫居。它们与堂很大的差异在于只办宴席,不办堂会,是一样平常官员或进京赶考秀才落脚之地。清末民初号称北京八大居,即是如此。八大居包括:前门外的福兴居、万兴居、同兴居、东兴居(此四家又称"四大兴”),大栅栏的万福居、菜市口北半截胡同的广和居、西四的同和居、西单的砂锅居。 个中福兴居的鸡丝面颇有名,光绪天子每次逛八大胡同,必去那里吃鸡丝面。砂锅居专用通县张家湾的小猪,做出的白肉有66样品种,地小人多,只卖半天,过去老北京有句俚语:沙锅居的幌子,过午不候,说的便是它的兴隆。广和居是鲁迅师长西席邀朋聚友常去的地方。广和居是道光年间专为南方人开设的南味馆,个中南炒腰花、酱豆腐、潘氏清蒸鱼、清蒸干贝、蒸山药泥,都驰名一时。北京最早的粤菜馆叫醉琼林,至光绪年间红火的粤菜馆要数陕西巷的奇园和月波楼两家。陕西巷即八大胡同之一,自南而北的走向,这两家粤菜馆在南端热闹之处。
大约除了丰泽园、晋阳饭庄、沙锅居为数不多的几家还在,别的早已风骚散去。听说还有一处在这几年规复老牌子的致美斋。北京城所谓斋都是原来的点心铺进而升格晋级办成的饭庄。论档次和规模是逊于堂、庄、居的。致美斋是同治年间开办的,它的一鱼四吃、红烧鱼头和萝卜丝饼,最享盛名。
老北京的饭庄最初紧张以经营鲁菜为主,只有很少的几家经营淮扬菜。由于当时上至天子,下至王公大臣,都对鲁菜情有独钟,而御膳房、寿膳房的御厨,险些都来自山东,因此鲁菜风靡一时。到了民国之后,北洋政府的官员、议员、总长等,很多都来自江浙地区,他们喜食家乡菜。当时,民国确当局机关大都集中在西长安街附近,于是,一些商人为了迎合他们的口味,相继在西长安街上开设了淮扬口味的饭庄。例如,教诲部就设在西单路口往南,有资料记载,鲁迅曾经就职于此,每逢有客人或者同乡来京,鲁迅就在西长安街就近招待,他最喜好去的饭庄便是大陆春饭庄。
老北京是天子脚下、全国都城,各阶层人士杂处,对付餐饮的消费需求量大、种别多。
因此,历史上就有浩瀚的饭庄,尤以清末民初形成的几个“八大”出名。八,在中国是个吉利数字,谐“发”之音之意,故各种事物都爱凑个八。这样一来,就有了老北京的几个“八大”。
北京八大饭庄
丰泽园饭庄、晋阳饭庄、正阳楼、功德林、鸿宾楼、梅府家宴、四川饭店、仿膳。
北京八大堂
会贤堂、同福堂、惠丰堂、聚贤堂、聚寿堂、天福堂、燕寿堂、庆和堂。
北京八大楼
东兴楼、泰丰楼、致美楼、鸿兴楼、鸿庆楼、萃华楼、新丰楼、安福楼。
北京八大居
福兴居、万兴居、同兴居、东兴居、万福居、广和居、同和居、沙锅居、还有个柳泉居。
北京八大春
八大春:指上世纪三十开设在西长安街的八家淮扬菜馆儿,一说为芳湖春、东亚春、庆林春、淮阳春、新陆春、大陆春、春园、同春园,一说为庆林春、方壶春、东亚春、大陆春、新陆春、鹿鸣春、四如春、同春园。同春园和淮扬春一贯坚持,分别在新外大街和月坛南街开设。此外还有长安十二春的说法,即上述后八大春加上宣南春、万家春、玉壶春和淮扬春。
八大堂:北京的王公府第、阔人宅门不似南方世家各有名庖,他们差不多都讲究吃庄子、吃馆子,无论是喜庆大事还是家庭小宴,都愿在庄馆举行。庄馆包办了统统筵席、铺陈、戏剧,使店主满意,因而带有戏台的大型饭庄便应运而生了。这类饭庄的最大特点是没有散座,不应零点,乃至没有常年做事的厨师和堂倌儿,须要时必须预约,老板或经理临时去雇厨师和做事职员,故俗称“冷庄子”。“八大堂”,一说为金鱼胡同的福寿堂、东皇城根的隆丰堂、西单报子街的聚贤堂、东四钱粮胡同的聚寿堂、总布胡同的燕寿堂、地安门外大街的庆和堂、什刹海北岸的会贤堂、前门外打磨厂的福寿堂等。一说为惠丰堂、聚贤堂、福寿堂、天福堂、会贤堂、福庆堂、同和堂、庆和堂。这些饭庄一样平常要有两三进四合院,几十间房屋,同时能摆开八人一桌五六十桌席面。房间陈设要文雅,餐具讲求,菜品精美,此外还设有戏台。但是堂字号的饭庄买卖做得很死板,价钱贵,也不设散座,不适应时期变革,到后来终被经营灵巧的“居”字号、“楼”字号饭庄所替代。
人们总认为吃喝的天下不存在“江湖”,实在不然,“切二斤牛肉下酒!”连武松打虎前都要饮酒吃肉,盖世英雄也是要小菜垫底儿,别以为一句话只是点菜,实在我们是侠肝义胆地“报菜名”。
那么在北京,如何能有“侠气”的平趟北京馆子?不妨学学这些老北京的馆子中的“行话”。首先,餐厅用饭,我们叫:下馆子,再或者说:“走,搓一顿去”。这都属于“小菜一碟儿”的最根本。其次您要认准北京的老字号:八大居,八大楼,广和居、同和居、和顺居、恩承居、福兴居、春华楼、安福楼、正阳楼、致美楼等。这16家饭铺中鲁菜馆就有13家之多,在烹饪上讲究爆、炸、扒、烧、熘。除此北京隧道的一个词儿:“汆儿”,羊肉汆丸子,羊肉汆儿。京味菜中属清真菜最有风味儿了,在对待牛羊肉上制作上,回民真是风生水起。八大菜、八小碗、十六碟,样样风雅。高中低档俱全了都。分外的名子,以前老北京平民饭铺子有分外的名子,叫“二荤铺”,就卖两种荤菜:猪肉或羊肉;或是肉与下水。汉民饭铺称“大教馆子”,回民饭铺称“隔教馆子”,便宜味美。
分外的叫法,话说回来,您如果不是在这个行当里您真不知道,油称“漫”,喷鼻香油即“喷鼻香漫”;糖称“勤”,红糖即“红勤”;酱油称“沫字”,黑酱油即“黑沫字”;盐称“海潮字”;纵然大略的数字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非用“日、月、南、苏、中、隆、星、华、弯”来代替,“嘿,师傅,买25条鱼”,要说:“混水字月中着”。不是“混”这道儿上的,您还真不知道!
做菜也有讲头儿,“漫大联儿游荡着点儿”-“炒这个菜油加大着点儿”;“漫大联沫着点儿”-“这个菜油小着点儿”;
“这个人可娄”-“这个人狗狗松松”,意思对这人要小心点儿;厨师若要大便了叫“吊桥”,小便叫“碎呼碎呼儿”。
这工种里也有说头儿:饮食行业——“勤行”,面点工——“面案”,还有专门切肉的——“红案”,专门擀面条的——“白案”。
在老北京,人一多,哥们儿姐们儿都在,这话就都跟上了,比如饮酒的时候,老北京人说饮酒,“一口闷、走一个,撅一瓶儿、吹一瓶儿”,二锅头——“二嘚子”,开水叫——“滚水”,饺子包子盒子——“馅儿”,面条怎么吃?——“锅挑儿” 或“过水儿”,拌料——“浇头儿”,还有一种“吃食”可不“好吃”,大耳帖子——巴掌,怂包蛋——怂人一个,菜包子——干什么什么弗成,老油条——调皮不厚道,毛兔子——不靠谱儿,拌蒜——走路不利索,废物点心——没用的东西,肉头——肉呼呼的。这些谚语生动活泼,既显示了地域文化的特色,有显得俏皮诙谐。
在老北京,饭桌上还有不少的规矩:
饭时不可说话。闷头吃!
别说话!
这就叫“食要静!
”
不可走着路用饭。在家里,规矩吃!
这就叫“食要席!
”
用饭不可换座位。固定座,安静吃!
这就叫“食要安!
”
用饭不可敲饭碗。盛好饭,再拿筷!
这就叫“食要文!
”
饭碗不可插筷子。吃时箸,停时放!
这就叫“食要矩!
”
饭碗要吃干吃净。吃完饭,不留粒!
这就叫“食要净!
”
用饭不可吧唧嘴。闭住嘴,不出声!
这就叫“食要相!
”
饭菜不可乱扒拉。吃近前,不挑食!
这就叫“食要礼!
”
“筷子不许立插在米饭中”、“盛饭不能只盛一勺”、“筷子和勺子不能同时拿在手上”。
说过了饭桌上的规矩,地处京畿之地的北京,在饮食上不得不说到满汉全席,清朝期间的宫廷盛宴。既有宫廷菜肴之特色,又有地方风味之精华;突出满与汉族菜点分外风味,烧烤、火锅、涮涮锅险些不可短缺的菜点,同时又展示了汉族烹调的特色,扒、炸、炒、熘、烧等兼备,实乃中华菜系文化的宝贝和最高境界。满汉全席原是清代宫廷中举办宴会时满人和汉人合做的一种全席。满汉全席上菜一样平常至少一百零八种(南菜54道和北菜54道),分三天吃完。满汉全席菜式有咸有甜,有荤有素,取材广泛,用料风雅,山珍海味无所不包。
满汉全席 菜点不仅精美,礼仪更为讲究,形成了引人瞩目的独特风格。入席前,先上二对喷鼻香,茶水和手碟;台面上有四鲜果、四干果、四看果和四蜜饯;入席后先上冷盘然后热炒菜、大菜,甜菜依次上桌。满汉全席,分为六宴,均以清宫著名大宴命名。搜集满汉浩瀚名馔,择取时鲜海味,征采山珍奇兽。全席计有冷荤热肴一百九十六品,点心茶食一百二十四品,计肴馔三百二十品。合用全套粉彩万寿餐具,配以银器,富贵华美,用餐环境古雅持重。席间专请名师奏古乐伴宴,沿典雅遗风,礼仪严谨持重,承传统美德,侍膳奉敬校宫廷之周,令客人乐不思蜀。全席食毕,可使您领略中华烹饪之博精,饮食文化之渊源,尽享万物之灵之至尊。
这些饮食文化,有的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并且升格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发扬光大。在民以食为天的国度,饮食的多元化和国际化在当下的北京得到充分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