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新史学》
有赖于陈寿简洁的写作风格,这一征象在《三国志》中表示得尤为明显,而在“国不置史,注记无官”的蜀汉政权中,昙花一现般的冷僻人物,涌现频率更是臻于高峰。
国不置史,注记无官,因此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蜀书 后主传》
《蜀书》中许多身登高位的冷僻人物,涌现得毫无征兆,消逝得天经地义,这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形。出于版本、誊录、订正等缘故原由,《三国志》中的诸多人物,在不同时期、不同政权的记载下存在明显的写法差异,便如《魏书》中的臧霸在韦曜《吴书》中被写作臧宣,《魏书》中的李肃在《九州春秋》中被写作李黑,如此各类,不一而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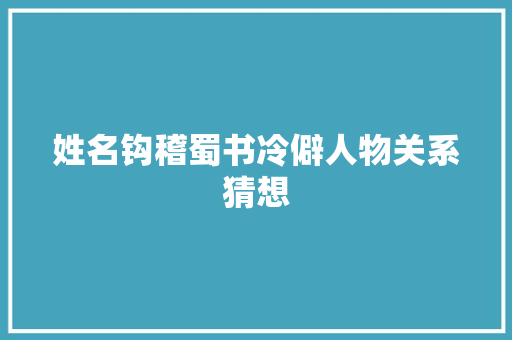
(赵)昱门户绝灭,及(张)紘在东部,遣主簿至琅邪设祭,并求亲戚为之后,以书属琅邪相臧宣(臧霸字宣高),宣以赵宗中五岁男奉昱祀。--韦曜《吴书》
(吕)布素使秦谊(秦宜禄)、陈卫、李黑(李肃)等伪作宫门卫士,持长戟。--《九州春秋》
本文想通过钩稽史籍中的吉光片羽,从姓名书写角度,磋商串联部分冷僻人物的业绩。能力所限,某些问题或有求之过深的嫌疑,权作发散思维,抛砖引玉之谈。
本文共 5400 字,阅读需 10 分钟
廖立与康立廖立是一个高开低走的人物,前半生深受刘备看重却弃城而逃;后半生因与诸葛亮不睦而遭免官废黜。荆楚良才,终极竟和刘封、李严、魏延等人一起入了《蜀书 卷十》,即罪臣传,可谓遗憾。
而在东晋学者常璩所撰《华阳国志》中,涌现过一个冷僻人物,即康立。有趣的是,康立与廖立不仅籍贯相同(均出身武陵郡),而且职务存在重合关系。
按《蜀书》,建安二十年(215)前后,廖立在弃(长沙)城而逃之后,被转授巴郡太守;按《华阳国志》,建安二十一年(216)康立出任固陵太守。
廖立字公渊,武陵临沅人……建安二十年,(孙)权遣吕蒙奄袭南三郡,(廖)立脱身走……(刘备)以(廖立)为巴郡太守。--《蜀书 廖立传》
建安二十一年,以朐忍、鱼服等六县为固陵郡,武陵康立为太守。--《华阳国志》
吕蒙奄袭南三郡,廖立脱身走
固陵与巴郡虽然并非同一行政区,但二者存在深厚的历史渊源。固陵属巴郡以东,乃是刘璋分巴郡而设,后改其名为巴东。建安末年,刘备复其旧名固陵,章武元年复称巴东。
以垫江以上为巴郡,河南庞羲为太守,治安汉;以江州至临江为永宁郡,朐忍至鱼复为固陵郡。巴(郡)遂分矣。建安六年,鱼复蹇胤白璋,争巴名。璋乃改永宁为巴郡,以固陵为巴东。--《华阳国志》
建安二十年(215)蜀汉政权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孙权遣吕蒙“奄袭南三郡(长沙、零陵、桂阳)”,导致长沙太守廖立亡入川蜀;其二是曹操遣张郃南徇三巴,导致巴东不复为刘备所有。
(张)郃别督诸军,降巴东、巴西二郡,徙其民于汉中。--《魏书 张郃传》
按廖立出任固陵太守时(215)巴东地区遭到张郃入侵,且固陵旧属巴郡,那么《蜀书》中的“巴郡太守”,与《华阳国志》中的“固陵太守(巴东太守)”隐喻当相同。
刘备称帝后(221)复固陵为巴东,此刻巴东郡守已是辅匡,这也和廖立的仕宦履历吻合——廖立在两年前(219)已结束外任,入成都为侍中。
章武元年,朐忍徐惠、鱼复蹇机以(固陵)失落巴名,上表自讼。先主听复为巴东,南郡辅匡为太守。--《华阳国志》
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征(廖)立为侍中。--《蜀书 廖立传》
结合籍贯出身与职务变迁,基本可以确定廖立与康立为同一人物,只是由于誊写问题为后世读者制造了些许误区。
简雍与刘备舍人简雍是刘备的涿郡同乡,仰仗主君宠信,“箕踞倾倚,威仪不肃”,行为近似于风趣俳优。由于其行迹放浪,言语轻佻,因此多被后世史家所腹诽,认为此人乃是东方朔之伦,不应与创业元勋合传。
《雍传》无甚建白,不过传其谏禁酿酒刑酒具一事,语近风趣而已。其谲谏之旨,以视汉东方曼倩(东方朔字曼倩)有所不逮,或附于他传可耳,陈寿特为立传,似可不必。--康发祥
在军政大事方面,简雍最出名的业绩即劝降刘璋——当然,刘璋归降的紧张缘故原由,乃是畏惧马超的军事威慑,简雍不过是顺势而为。诚如近代战役史上的名言:沙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会谈桌上也休想得到。
先主围成都,遣(简)雍往说(刘)璋,璋遂与雍同舆而载,出城归命。--《蜀书 简雍传》
先主遣人迎(马)超,超将兵径到(成都)城下。城中震怖,(刘)璋即稽首。--《蜀书 马超传》
刘备遣简雍往说刘璋,璋出城归命
《魏略》记载,刘备遣使与张鲁往来时,曾有一名“姓简”的“舍人”拜访汉中,还在此地意外创造了刘备失落散已久的儿子。由于这位“儿子”与刘禅的年事严重不符,因此后世学者对此记载多持非议态度,认为言不符实,语出虚诞。
初,(刘)禅与刘备相失落时,识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简者,及备得益州,而简为将军。备遣简到汉中,舍都邸。--《魏略》
以事相验,理不得然,此则《魏略》之妄说,乃至二百余言,异也!
--裴松之
然而结合《彭羕传》、《李恢传》可知刘备与刘璋征战期间,确曾多次叮嘱消磨外交职员远赴汉中与张鲁联结,《黄权传》记载的“(张)鲁走入巴中,先主以(黄)权为护军,率诸将迎鲁”也反响了这一问题。
(李恢)北诣先主,遇于绵竹。先主嘉之,从至雒城,遣恢至汉中交好马超,超遂从命。--《蜀书 李恢传》
鉴于简雍“常为谈客,往来义务”,可知他长期担当刘备集团的外交职员,因此其拜访汉中确有可能,只不过未必与刘禅有关。
“舍人”是一个带有人身寄托色彩的词汇,泛指亲信、门客一类。而“少与先主有旧,随从周旋”的简雍完备符合这一性子。
其余,《魏略》记载的“及(刘)备得益州,而简为将军”也和《简雍传》记载符合:简雍在刘备进入成都后受封昭德将军,一朝发迹,一人得道。
简雍字宪和,涿郡人也。少与先主有旧,随从周旋……先主拜雍为昭德将军。--《蜀书 简雍传》
结合诸多线索,基本可以断定“刘备舍人姓简者”即简雍无疑。
殷纯、阴纯与阴化《蒋琬传》与《邓芝传》中均涌现过一个冷僻人物,即阴化,然而此人业绩十分模糊,险些难以入手。
结合《先主传》与《华阳国志》,笔者疑惑阴化即殷纯。
刘备称帝时,劝进群臣中位居前列者有“大司马属殷纯”。大司马即刘备自相授受的伪职(源自刘璋的表荐)。汉末军阀多建立“军府”性子的幕府进行统治(如曹操的丞相府、刘备的左将军府),因此“大司马属”即刘备幕府的幕僚,按其劝进班次而论,应为高等幕僚。
大司马属殷纯、益州别驾从事赵莋、治中从事杨洪、从事祭酒何宗、议曹从事杜琼、劝学从事张爽、尹默、谯周等上言。--《蜀书 先主传》
(刘)璋推先主行大司马,领司隶校尉;先主亦推璋行镇西大将军,领益州牧。--《蜀书 先主传》
《华阳国志》记载刘备称帝事宜时,将殷纯写作“阴纯”。虽然不详孰正孰误,但这一记载供应了一个新思路,即阴纯是否可能为“阴化”的本名。
大司马属阴纯、别驾赵笮,治中杨洪、从事祭酒何宗、议曹从事杜琼、劝学从事张爽、尹默、谯周等上言。--《华阳国志》
繁体字中“纯(純)”与“化”的写法差异不大,可知确实存在传抄讹误的可能。另按孙权的评价:“丁厷掞张,阴化不尽,和合二国,唯有邓芝”,可知阴化该当长期担当高等外交官,且不止一次面见过孙权。
(孙)权与(诸葛)亮书曰:“丁厷掞张(指浮夸),阴化不尽(指能力有限);和合二国,唯有邓芝。”--《蜀书 邓芝传》
孙权:丁厷掞张,阴化不尽
按照吴蜀的往来记载看,青鸟使多为严畯(卫尉)、张温(太子太傅)、陈震(卫尉)、邓芝(尚书)、宗预(侍中、尚书)一类的清贵官僚,照此而论,阴化该当也属于同一类型。曾担当过大司马属、参与过劝进行动且详细功绩不详的阴纯(殷纯),在身份层面上十分符合这一特色。
权为吴王,及称尊号,畯尝为卫尉,使至蜀,蜀相诸葛亮深善之。--《吴书 严畯传》
拜议郎、选曹尚书,徙太子太傅,甚见信重。时年三十二,以辅义中郎将使蜀。--《吴书 张温传》
汉末阴氏多出身南阳新野,这一家族在东汉与皇室累世通婚(汉光武帝、汉和帝皇后皆为新野阴氏),见诸记载者不可胜数。按刘备曾镇守新野的履历,其麾下存在阴氏子弟比较符合逻辑。
阴识字次伯,南阳新野人也,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自齐适楚,为阴大夫,因而氏焉。秦、汉之际,始家新野。--《后汉书 阴识传》
而《三国志》中较为著名的殷氏子弟则多出身吴郡云阳,如殷礼、殷基父子,这一宗族舍近求远,投效刘备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假设常璩记载属实,即“阴纯”为殷纯之本名,那便不能打消阴化与阴纯为同一人物的可能性。
丁厷与丁立在孙权眼中与阴化(阴纯)同列的丁厷,也是《蜀书》中的冷僻人物,其涌现频率比阴化更低,仅在《邓芝传》中被提及一次。
丁厷掞张(指浮夸),阴化不尽(指能力有限);和合二国,唯有邓芝。--《蜀书 邓芝传》
按孙权与诸葛亮春联盟关系的重视程度来看,担当外交官的职员必是文武茂异,那么丁厷便绝不可能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人物。
(孙)权乃参分天下……造为盟曰:“……诸葛丞相德威远著,翼戴本国,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重复缔盟,广诚约誓,使东西士民咸共闻知。”--《吴书 吴主传》
从字形角度考虑,笔者疑惑丁厷即《后出师表》中的丁立,亦即杨戏《辅臣赞》中的丁君干。
丁立之业绩不详,其人在《后出师表》中与赵云并称,被归入“宿将”之列,应具备北伐经历。既出使过东吴、又具备北伐履历者,蜀汉又有宗预,其人在建兴年间曾为诸葛亮主簿,后迁参军、右中郎将。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后出师表》
建兴初,丞相亮以(宗预)为主簿,迁参军、右中郎将。--《蜀书 宗预传》
建兴初,诸葛亮以宗预为主簿
从外交待遇上看,孙权对具备戎行履历的蜀汉使者彷佛特殊看重,他曾赠予宗预“大珠一斛”,且“捉(宗)预手,涕泣而别”,爱崇之情,亲密之意显而易见。
(宗)预复东聘吴,孙权捉预手,涕泣而别曰:“君每衔命结二国之好。今君年长,孤亦朽迈,恐不复相见!
”遗预大珠一斛,乃还。--《蜀书 宗预传》
照此看来,丁立作为北伐将领,出使过东吴亦不敷怪。若丁立与丁厷实为一人,那么便能阐明为何孙权评价丁厷为“掞张”,即性情浮夸,其背后或许存在恃功自傲的成分。
另,清代学者钱大昕曾疑惑《辅臣赞》中的“丁君干”即丁立。诸葛亮曾将丁君干与王谋、杨洪、文恭等人并举,盛赞诸人德行操守,照此推断,性情“掞张”的丁立(丁厷)可能还是一名儒将。
(丁)君干,疑即《(后)出师表》所称丁立也。--钱大昕
(诸葛亮)于坐上与(杜微)书曰:“服闻德行,饥渴历时,清浊异流,无缘咨覯。王元泰、李伯仁、王文仪、杨季休、丁君干、李永南兄弟、文仲宝等,每叹高志,未见如旧。--《蜀书 杜微传》
鉴于记载的阙失落,对此二人关系尚不能完备确定,不过笔者仍方向二人存在重合的可能性。
向举、白攀与白寿《后出师表》中曾提及一名北伐将领白寿,这也是一个仅此一见的分外案例。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后出师表》
实际《三国志》中涉及白姓者极少,而《蜀书》中仅提到一例“凉州胡王”白虎文,且此人属于少数民族,姓氏当为音译。洪武雄搜求群书,在《蜀汉政治制度史考论》中也仅辑录入白寿、白虎文两例而已。
十年,凉州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率众降,卫将军姜维迎逆安抚,居之于繁县。--《蜀书 后主传》
因此,白寿作为与赵云等人并列的将领,在正史中不见记载便显得匪夷所思。结合《太平御览》,笔者疑惑白寿姓氏或为传抄讹误,其可能出自向氏。以下从《先主传》线索入手剖析。
刘备称帝时,领衔劝进的既不是张飞、马超、诸葛亮等重臣,也不是前文提到的“大司马属”殷纯,而是“阳泉侯刘豹、青衣侯向举”。
故议郎阳泉侯刘豹、青衣侯向举、偏将军张裔、黄权、大司马属殷纯……劝学从事张爽、尹默、谯周等上言。--《蜀书 先主传》
阳泉侯刘豹、青衣侯向举劝进刘备
刘豹、向举亦属唯此一见的人物。按照现存史料,刘备称帝前似未册封过臣下“县侯”级别的爵位(法正之“翼侯”情形分外,且为追谥),那么刘豹、向举的侯爵很可能沿袭自东汉,刘备乃是借用前朝遗老的劝进来自抬身价。
刘豹、向举二人在《太平御览》辑录的《蜀志》中被写作“刘毅”、“白攀”,按举(舉)、攀的繁体写法附近,可知当体系一人物。按白攀与向举的对应关系来看,可知其原来姓氏当为“向”无疑。
刘毅、白攀等上言:“建安二十二年,必有天子出其方。”--《太平御览》引《蜀志》
推此而论,《后出师表》中的白寿之名,便同样可能来自传抄讹误,其原来姓氏可能亦为“向”。
襄阳宜城向氏在蜀汉政权中跻身高位者浩瀚,向朗、向宠、向条、向充等人皆有业绩,兹不赘引。白寿若为向氏子弟,则可阐明其姓氏稀少(白姓罕见于《蜀书》)的问题。
小结历史的记录书写,在各种主客不雅观成分的相互浸染下,难免涌现扭曲失落真;不过得益于不同史料的互文见义,还是可以通过有限线索勾稽部分人物。
当然,史学离不开史料,也离不开考古事情的成果,眼下的诸多猜想终不免水月镜花的嫌疑。补充史籍空缺,还有赖于学者探究与考古创造,本文的只言片语,权作漫谈之论。
陈寿修撰《蜀书》的背景较为分外,出于各类缘故原由(包括个人好恶及时代背景,见《晋书 陈寿传》),他隐略了蜀汉的大量主要人物,诸如高翔、句扶、上官雝等名将或被片言带过,或干脆不见记载,为后世研究蜀汉历史凭空制造了许多困难,是为一憾。
本文虽属漫谈,但也希望能通过笔者的猜想,为喜好三国的读者朋友开拓些许思路,增长些许裨益。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阐发展开背后隐蔽的深意。
Thanks for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