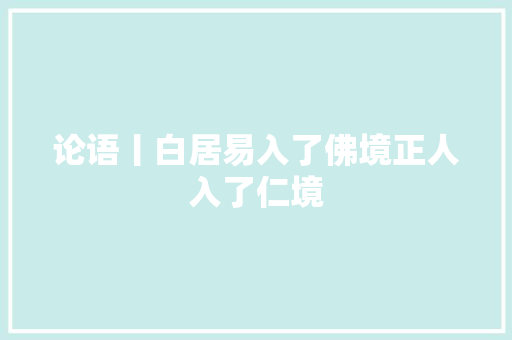白居易有一首诗,写他七十一岁时,行住坐卧都在念佛,诗中说:“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纵饶忙似箭,不废阿弥陀”。佛家书众念佛的这种执着精神与孔子空想中的君子追求仁的执着情怀,可谓是佛儒双璧。一声佛号,招引了多少古往今来心向彼岸;一枚仁字,更指引了无数志士仁人梦归圣仁!
仁,引领着人们完善人格、造诣君子,这是仁第二大益处亲睦事: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唐突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个中两个“不以其道得之”,每每让人不得真解!
我们把“不以其道得之”放到全章中去掂量:挣大钱、昔时夜官,这是人所希望的;但是,如果“不以其道得之”,就不接管这种富贵,"不处也"。“不以其道得之”,常常理解为不按正道得到的富贵,这样还算说得通。再往下来:没有钱、没有地位,这是人所厌恶的,又来了一个“不以其道得之”,并且要“不去也”——不丧失落这种贫贱。这个“不以其道得之”不好阐明,古今表明多多,但彷佛难以信从。我们选杨伯峻《论语译注》,看看他的解读:
“富与贵”可以说“得之”,“贫与贱”却不是大家想“得之”的。这里也讲“不以其道得之”,“得之”该当改为“去之”。译文只有这一整段的精神加以诠释,这里为什么也讲“得之”,可能古人的不经意处,我们不必在这上面做文章了。
对经典这样对待,有失落武断和臆造。我们先去看看个中的关键:道,是什么?"其道",指的又是什么?
杨伯峻、李泽厚都把"其道"看作"正当的方法",道是方法手段,这是主流解读。朱熹解“不以其道得之”为“不当得而得之”,钱穆解“其道”为“当得之道”,朱穆两人同等。道是规律、定律。
"当得之道",大概最符合本意,可惜没说破“当得之道”便是“因果之道”。
对付"因果之道",《尚书》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认为,人积善就该当得到吉祥得到富贵,做不善就该当得到不幸遭受贫贱。与孔子大有渊源关系的《周易·坤文言》说:"积德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些后来被狭隘理解为"因果报应"并带上些迷信色彩,粉饰了早期对因果之道、因果规律认识的理性光辉。
从这章来看,孔子是要辅导人们,想要完善人格,教化君子,追求安仁,就要从富贵贫贱的因果关系中把物质外物看破识破,才能真正奔向仁,以安于仁,与仁相伴。在他看来,富贵贫贱这个结果和状态,自有它必需的缘故原由和条件,有它的规律和定律。比如,你想要致富达贵,自身条件要好,还得选准方向路径,做对了做得当了,统统自身善因具足了,才有可能得到富贵,这是它的因果定律,这样得到的富贵就叫做“以其道得之”,是按照有其因得其果的因果定律来的,这里的“其道”便是指富贵的因果规律。
如果缘故原由条件变成了无善无德、无才无能,只用歪门斜道去挣钱求官,结果富贵,这就叫做“不以其道得之”,由于它不是按照富贵的因果定律来的,是自己乱来得来的。或者是,自己没想升官发财,也没有往这方面努力,溘然天上掉下了馅饼,意外地富贵了,这样的结果,也是“不以其道得之”,由于没去种富贵之因,却得到了富贵之果 。像这样“不以其道得之”的富贵,对付要造诣君子、追求仁的人来说,应该“不处也”——不要沾边儿!
贫贱也是这样。人如果一无所长、一身恶习、不务正业、求上进,等等,由于有这样的因,就理应得贫贱之果,这便是“以其道得之”。如果不是这样,本来想升官发财,统统善因也都具足,但怎么奋斗,终极只得了个贫贱,这便是“不以其道得之”,它没有前因后果的一定,是本人之外的比如大环境、运气等身外缘故原由。再比如,教化君子、追求安仁,齐心专心讲仁、求仁、行仁,理应得到富贵或安祥,但,却有颜渊那样的贫穷,更有孔子师徒流亡列国那样的困顿,这就叫“不以其道得之”,对此,孔子说:“不去也”——接管它,心安理得地与之相伴!
这种自身无因的富贵或贫贱之果,教化君子、追求安仁,最需面对和修炼:"不处"自身无来由的富贵,"不去"自身无来由的贫贱,能够心安于此,便是得到了仁的入门功夫。
接下来,孔子又讲:"君子去仁,恶乎成名?″教化君子,如果让富贵贫贱这些利益旁边了心地,这便是"去仁″——抛弃了仁,就不是君子。并且,君子应该"无终食之间违仁″,纵然吃一顿饭那么长的韶光或者闲着的时侯也不忘却和离开仁,是"唐突必于是",纵然怎么忙、仓促(唐突)也心在仁上;是"颠沛必于是",纵然如何困顿(颠沛)也心在仁上。这便是君子要教化的目标!
读完后半章,才知晓孔子关于教化君子、追求安仁的两大关口:
先要过"有物关",对付"不以其道得之"的富贵,要能够"不处"——不理它!
对付"不以其道得之"的贫贱,要能够"不去″——相伴它!在此根本上要过"无物关",超脱物质上的因果定律,根本就不觉乎富贵贫贱这些物质困惑,不觉乎永劫短时、闲时忙时等外界束缚,而只有一个仁与我自由清闲。
这种境界,正如文章开头白居易的诗那样:"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纵饶忙似箭,不废阿弥陀”。
不过,白居易入了佛境,君子入了仁境!
朋友,我是清如静如,力求按照"义理"全面系统地"照着说"《论语》,很高兴与你对坐经典!
(图片借用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