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人马已经准备就绪!
”
夜幕下,听着潺潺的流水声,赵充国双手背在身后,站在在江边悄悄地看着前方。溘然,耳边响起将士的报告声。
“让他们务必小心,切莫暴露行踪。”赵充国再三叮嘱,恐怕深夜渡黄河的计谋暴露,让全体布局功亏一篑。
这一年是神爵元年,汉武帝早已不在,是汉宣帝刘询的天下。匈奴鲜少涌现,边疆已经太平许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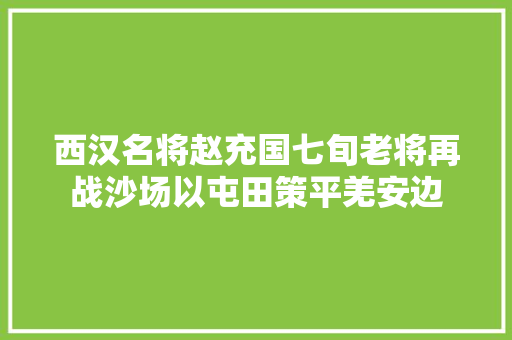
赵充国怎么也想不到,他在古来稀的年纪还要再战疆场。
只是此刻,贰心内心颇为沉着,比起年轻部将的热血沸腾,如今更多的是沉着自若。
赵充国面对的仇敌是羌族,一个滋扰边疆的少数部族之一。相较于匈奴,羌族的出镜率比较少,以至于其他人对羌族并不理解,以为要大举进兵才行。
唯有他知道要平定羌族叛乱不是靠兵力、计策兵法。
老将赵充国靠的是他那句“以德服人”。
汉成帝时,文学家杨雄曾夸奖他:“在汉复兴,充国作武,赳赳桓桓,亦绍厥后。”
烽烟起,羌族叛,老将出马
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羌族发生叛乱,先零种首领杨玉联合其他大种豪族,打败了汉朝派到西羌的骑都尉义渠安国,并且包围了金城郡(今兰州、西宁、海东一带)的令居县城。
传来,汉宣帝刘询可犯愁了,羌族叛乱,打是要打的,关键是找谁去打呢?
看来看去,只有快七十的赵充国了。从汉武帝刘彻算起,赵充国历经三任天子。当年打匈奴的时候,赵充国非常勇猛,之后也屡次出征,有不少战功。
问题是这把年纪的老将上沙场还行吗?
汉宣帝没美意思直接去问赵充国:你去打仗行弗成。他拐了个弯,就让御史大夫丙吉去。
丙吉一接到任务,就明白了汉宣帝的意思。赶紧找到赵充国,直接和他解释情形,表明陛下想知道出征西羌,派谁最得当。
赵充国底气十足,回话都不带犹豫:“没人比老夫更得当!
”
得到回答的汉宣帝见赵充国这么有信心,悬着的一颗心算是落地。光决定将领还弗成,还要准备人马呢。汉宣帝也是个好天子,转念就问赵充国要多少人马,有什么操持。
赵充国老神在在:“详细的情形要到前哨看过才知道,只要陛下相信我,羌族叛乱的事情陛下就无须担心了。”
到前哨后,赵充国提出了屯兵的策略,这又让汉宣帝犹豫不定,。
赵充国为什么不打,非要屯兵呢?
真是如此自傲?真是老当益壮?还是军事专家?又或者羌族不敷为患?
以上答案都对。
要理解羌族叛乱,就要理解汉宣帝那时这些少数部族的处境。
汉朝初期建国,匈奴还常常陵暴汉朝,时时时来打秋风,汉王室不仅要忍,还要让宗室公主去匈奴和亲。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候,彻底不忍了。汉武帝任用卫青、霍去病横扫漠南漠北,把匈奴打得落花流水,不敢轻易再来滋扰。
如果说北边的匈奴曾经让汉朝吃瘪,后来被汉武帝打跑了,那么西边的羌人便是从来也翻不起什么浪花的部族。
羌族本来也是农耕者,由于西北不易栽种,才逐步演化成游牧民族。
虽然羌族和匈奴都是游牧民族,崇尚武力,但羌族人的爆发力强,持久力弱,善于山地作战,平原奔驰就弗成了——大略说山上打仗是强项,平地就弗成。
其余,羌族没有匈奴那么强大,是由于他们以氏族部落的形式聚居,一个部族是一个“种”。大部族间相互争斗,小部族只能寄托,以是很永劫光,他们没能像匈奴那样涌现一个统一部族的人物。
以是说,羌族只要乖乖地就好,野心这种东西不太适宜他们。偏偏他们便是有野心。
汉武帝的时候,羌族有个大部落和匈奴联合攻打汉朝边疆。当然,毫无例外地被汉武帝弹压了。终极结果是汉武帝在河西开拓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个郡,把羌族和匈奴给隔开了——看你们怎么联合!
不去世心的羌族后来又一次和匈奴人勾结攻打金城郡,汉武帝一挥手十万大军压过黄河以西,把羌族赶出来湟水流域。基本上到这时,羌族人意识到汉朝不好惹,也就循分下来了。
可这次汉宣帝碰着的羌族叛乱,说白了却是挺乌龙的一件事情。
汉宣帝本来派出义渠人安抚羌族的,谁知,他跑去噼里啪啦把羌族的这些首领抓的抓杀的杀,这下羌族人以为大事不好,不反要没命了。
实际上,当时羌族真正有反心的人并不多。
就这样,原来可以安抚羌族避免的战事却坏在了义渠安国的安抚策略。
赵充国一眼就看穿了个中的玄机,随之就制订出相应的对战策略。
资历丰富的老将,深谙敌方套路
为什么赵充国的洞察力如此厉害呢?这与他丰富的资历分不开的。
赵充国出生于公元前137年,是陇西上邽(今甘肃省天水市)人。年少的时候,就非常仰慕那些大将军。为了将来也成为那样的人,不仅爱学兵法,还专门把稳边防事务。
可以参军的时候,他就以“良家子”的身份当了骑兵。由于骑射功夫好,进入了羽林军。
赵充国第一次出征是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一声令下要征讨匈奴。于是他以代理司马的身份,随着贰师将军李广利,去酒泉攻打匈奴右贤王。
当时李广利的军队被匈奴军队围困,李广利眼见被围也没想出什么办法。这时候,赵充国就向将军李广利自荐,说是能尽快脱困。
“匈奴只围不攻,是想逼迫我们在断粮的情形下屈膝降服佩服。我们只有两个办法。”赵充国伸出两个手指。
“什么办法?”
“要么屈膝降服佩服,要么突围。我愿带兵突围,解此危急!
”赵充国年夜声说道。
听到这里,李广利明白了。他思前想后,终极赞许赵充国的发起,让赵充国选拔一百多名精锐履行突围。
赵充国精心挑选跟随他开路的士兵,打头阵一起在前面厮杀,李广利率领大部队随后跟进。
匈奴军队看到汉朝军队想突围,立即上前堵截。
赵充国来一个砍一个,来一双杀一双。就这样双方不断拼杀,终极让赵充国杀出一条血路来,李广利的部队终极脱困。
等脱困后,赵充国才创造自己身上有二十多处伤口。
由于这次突围的表现,赵充国升为中郎,还受到汉武帝的特殊召见与褒扬。此后又升为车骑将军长史。
汉昭帝刘弗陵的时候,氐人在武都(今甘肃省西和西南)造反,赵充国奉命带兵征讨。那年冬天,匈奴率兵入侵,他带兵迎敌,捉住西祁王,并斩杀九千多人。
这次之后,他被任命为后将军,兼任水衡将军。
到了汉宣帝,赵充国参与大将军霍光拥立刘询有功,被封为营平侯。
公元前72年,匈奴联合车师国攻打乌孙国。乌孙国向汉朝求援。汉宣帝就派出赵充国,率领三万骑兵离开酒泉一千多里,到在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进攻匈奴,斩杀数百人。
不服气的匈奴人聚拢了十万多骑兵,做出入侵的姿态。赵充国绝不相让,率领四万骑兵,在北部九郡驻扎,防备匈奴人的进攻。
匈奴人一看汉朝边疆有所防备,就知道这是块硬骨头,只得撤兵。
赵充国算是资历丰富的老将,对边关少数民族心里的小九九十分清楚。
以策略取胜,以德服人
面对这次羌族的叛乱,赵充国一点也不慌。
他知道羌族不长于平地作战,以是除了步兵,他还向汉宣帝要来一万骑兵。
然而在这场战役中,紧张的问题是渡过黄河。
渡黄河的时候,最随意马虎被偷袭,一旦遭遇偷袭,全体部队的节奏打乱,轻则伤亡,重则全军覆没。以是怎么把大军开过黄河是一件要紧事。
赵充国想了个妙计,先让少量的人马趁着夜色渡过黄河,然后在河边安营扎寨,速率地建造了一座弘大的军营。
凭空涌现一座大军营,羌族人难道不会疑惑吗?他们非但不疑惑,还吓得不敢胆大妄为。他们以为汉朝大军一晚上就全部渡过了黄河,恐怕私下里还会惊叹汉朝大军的高效率。
这头的赵充国可不知道羌族人到底有没有上当,以是也不能立即派出后续大部队。这时候便是探子活动的韶光。很快,探子带来了好:羌族人压根不敢动兵。
赵充国这才带着部队大摇大摆地过了河。
缓过神来的羌族人,才创造他们上当了,错失落最好的下手机会。气炸了的羌族人要以牙还牙,就用个引蛇出洞的计谋来坑赵充国。
他们派了一队精锐骑兵到汉军前招摇,就差拿个旌旗摆荡,大喊:快来打我呀!
打仗嘛,不便是杀敌嘛。这一队人马,数量不多,上去就能一顿胖揍,这不是送上门的战功?赵充国部下将领急着请命出击。
赵充国冷着一张脸,统统都给谢绝。
“我们的目的是全歼仇敌。现在这支小军队是一支精锐,实力远不是你们带几十人能打败的。真要打起来,就须要动用大部队。想想我们才渡过黄河,军队还没休整好,精力还没规复,出动大部队去打不划算。这是羌族给我们下的陷阱,是个亏本买卖。”
一番话后,部下将领才意识到问题所在。
姜还是老的辣!
赵充国不理会羌族人叫阵,嘱咐将士们原地安歇,让这些叫阵的羌族骑兵连续为汉朝军队打气。
羌族骑兵叫了老久,也没人理会他们。只能又气呼呼地回去。
等到羌族骑兵离开,赵充国派侦察兵去探路,创造附近随意马虎安排伏兵的四望陿上没有羌族人军队。这是天赐良机,便连夜拔营赶到了黄河上游落都山。
到了落都,赵充国算是彻底放心了:这场仗稳赢。只要羌族没在四望陿安排伏兵,那么到了阵势平坦的落都,汉军就霸占了有利地形。
即便霸占有利地形,赵充国还是非常谨慎的,只要羌族人挑阵,他一律不应,只哀求部下士兵养精蓄锐。
不久,赵充国让儿子赵卬带一支军队去令居城,防止羌族人截断他们的粮道。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去策应清敌。不出赵充国所料,羌族人果真谋划截断粮道。
赵卬立即策应,重新疏通粮道,确保后勤补给。
粮道规复,战局却陷入胶着。羌族人内部开始产生了不同的声音,有的说屈膝降服佩服,有的说连续战。
实在早在赵充国出征前,就已经有开羌、罕羌(羌族的部落)的首领派人偷偷去给赵充国报信。报信的人被金城郡的都尉抓了,赵充国却让人给放了。他亲自安抚报信人,说他们报信是有功的,是对天子的忠实,大军征讨的是那些造反的人。当然,参与背叛也能将功赎罪。
正是赵充国这样的说辞,让原来就不想掺合进背叛里的羌族人看到了希望,谁不想好好过日子啊。打仗,那完备是个乌龙事宜,他们不想打哟。
对羌族的动向,赵充国很有把握,但汉宣帝不知道,他总以为赵充国这么个七十岁的老人家了,一人带兵去打仗估计还有点勉强。这么想着想着,他就动了心思,想再派点兵去。
汉宣帝这么想,也这么做了,一挥手陆陆续续调派了约六万兵马。贰心里乐呵呵,这么多人总能灭了羌族人吧。
对付这些增兵,赵充国哪能不知道汉宣帝的心思呢,不便是担心赵充国打不下来嘛。
定心丸是一定要给汉宣帝的,赵充国接连两次劝谏汉宣帝:先把背叛的先零羌就行了,开羌、罕羌本就没有背叛意愿,到时候看到先零羌败北,就不花一兵一卒拿下。
“背叛是先零羌主导的,开羌、罕羌开战以来没有反攻袭击。如果去攻打开羌、罕羌,这是对无罪的人履行惩罚。那到时候开羌、罕羌会加入背叛,引起对抗朝廷的心思。一旦形成这样的局势,战事两三年都不一定结束。”
“对待开羌、罕羌,该当用宽大的政策,赦免他们背叛,再派理解风尚的官员来管理安抚他们,这样既能降落士兵伤亡,也能担保胜利,让边疆长治久安。”
两颗定心丸下肚,汉宣帝放心了,收下赵充国的劝谏。
果真,犹如赵充国所料,很快羌族内部分裂,联合军气势散去,背叛之心早已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赵充国就在这样的形式下,逐步悠悠地追着先零羌,像逗小狗似的。缀着他们,既让先零羌知道有追兵,烦懑点逃就没命了,又不把先零羌逼得垂死挣扎,来个鱼去世网破。可怜先零羌就这么一起给逼到湟水边上。
办理先零羌后,赵充国就率兵开到开羌和罕羌的领地。这里的首领本就无意背叛,还派过青鸟使,以是看到赵充国一来,就利落地开城屈膝降服佩服。
汉宣帝屈服赵充国的谏言果真没有惩罚开羌和罕羌,反而给予优待。一看屈膝降服佩服非但没去世,还能有褒奖?这就动摇了剩下的其他小部落。很快,这些小部落纷纭屈膝降服佩服。
见到羌族人大规模地屈膝降服佩服,赵充国认为羌族人已经不成景象,加上他生病,计策上自然又要做新的变革。
“驻兵屯田”便是他的新计策,他认为留下一万步兵就可以,一边防守一边屯田,别的大军撤回去。
此时,汉宣帝却由于赵充国的病又开始担心。将领生病,这仗还能打下去吗?胜利在望了呀,不能就差这口气吧。
为了不影响这场征讨,汉宣帝下了进军的诏令,想让赵充国赶紧进军完成征讨。大略一句话:你老人家速战速决,打完了也好快点回来养病。
对这张诏令,儿子赵卬以为一定要屈服啊,不然触怒了天子,百口都活不成。于是他不断奉劝父亲屈服天子的诏令。
赵充国听儿子这么说,心里恼怒,他堂堂一个将领,忠君为国,可从来不会贪恐怕去世罔顾国家利益。对着儿子就一顿训斥:“这是一个忠臣该说的话吗?”
训完儿子,赵充国就上书汉宣帝:“兵者,是用明德除害的,因此用兵要谨慎。要想西羌长久稳定,要以德服人,那才是上策。用兵攻打只能是下策。撤军不仅能减少后勤用度,而且这里有无人耕种的田地两千顷,只留一万零两百八十一名步兵开荒屯田,可以自给自足。朝廷出的花费就很少了。”
一提用度这事,汉宣帝回过神来了,少费钱不好吗?打仗多费钱呐。汉宣帝心里痛快酣畅了,安心地采纳了赵充国的进谏。
终于,羌族叛乱平息,边陲终于进入了安稳期。
讲“德”的武将,位列麒麟阁十一元勋
赵充国在这场战往后,就解甲归田安心养病。
他去世后,进入“麒麟阁十一元勋”之列。
作为一名上沙场杀敌的将领,他不是梦想胜利的莽夫,也不是为了保一家性命屈服天子的臣子。
他有他的原则,是他为人为臣为将的根本立足点,乃至在给汉宣帝的上书反复强调这原则:以德服人是上策。
他开战是有底线的,从来就没有超出过他的原则:以德服人是根本,只打该打的人,不该打的就安抚。
开战如果不可避免,也须要用最少的代价获得胜利。可见赵充国不仅会打仗,明白不同期间要用不同策略,也非常体恤士兵。他深知沙场只是一时胜负,政治上却须要长久眼力。
让羌族不战而降也好,驻兵屯田也罢,都在最大程度低落低了伤亡,也是德行的一种表示。
这样一个将“德”字记在心里的将军,实在是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