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昂首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李白的这首《静夜思》是中国有名度最高的古诗之一,但大多数人大概不清楚,这个版本并非李白的原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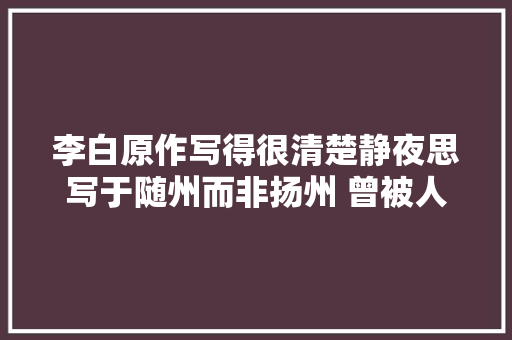
有人根据作者的创作年谱推算,此诗应写于开元十五年(727年)前后,究竟是哪一年?还不愿定。
还有一个问题也无定论,李白此诗是写于本日随州的广水,还是写于扬州的江都?
两个问题完备可以并案研究,搞清了创作地,就可以准确地判断出创作韶光,如果写于扬州,韶光只能是开元十四年秋;如果写于随州,韶光便是开元十五年往后。
实际上李白的原稿把创作地写得很清楚,本日为什么会有争议,完备是明清文人惹的祸。由于我们本日读到的《静夜思》是被明清两朝文人“润色”过的,诗稿源自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蘅塘退士所编的《唐诗三百首》,此前历朝历代的版本都不是这个样子。
改了好不好可以不辩论,但必须得把话说清楚,目前小学教科书上的《静夜思》绝对不是李白的原稿。
那么,李白的原稿长什么样呢?离唐朝最近的朝代是宋朝,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中的《静夜思》是这样20个字:
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
清朝康熙天子钦定的威信刊本《全唐诗》中的《静夜思》也是这样的,日本至今流传的版本仍是这个,据此可以断定,“山月”版的《静夜思》才是李白的原稿,或者说最靠近李白的原稿。
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到了明朝万历年间,有个叫赵宦光的文人,不科考不从政也不做生意,带着老婆隐居在苏州寒山,最大的爱好便是读书品书,有一天心血来潮了,要把古人作品中的瑕疵给改改,恰好另一个叫黄习远的人也有这想法,二人一拍即合,就把宋朝洪迈主编的《唐人万首绝句》拿来给改了一遍,换名《万首唐人绝句》重新刊印,于是,“举头望山月”就变成了“昂首望明月”,五个字改了两个,在学界开了一个不良的先例,《静夜思》也由“山月”时期进入到了“明月”时期。
唐时的文人创作中,喜好把玉轮分成各种类型,最常见的有“明月”“海月”和“山月”,“山月”除了点明地点之外,还可以陪衬环境的静寂无声,而《静夜思》追求的正是一个“静”字,用“山月”是再好不过了。李白出川之前,还写过《峨眉山月歌》,第一句便是“峨眉山月半轮秋”,这里的“山月”不是满月,估计两位先生长西席是受不了“半轮”的刺激,执意把“山月”改成了“明月”,让月光更亮一些。
到了乾隆年间,无聊的文人更多了,各种各样的版本纷纭出笼,末了被蘅塘退士搞成了这个样子。
比对“山月”版与“明月”版,诗稿统共被改了三个字,即“看”和“山”改成“明”,“抬”改成“举”。据有关专家点评,“看”字太俗,读音太重,又有“聚焦”的意思,与后面的“疑是”不太合拍,李白当时的状态该当是半梦半醒,才可能把月光误当霜,既然赵先生长西席已把“山月”改“明月”,“明月光”岂不是更能强化这种梦幻效果?“抬”字也很俗,与诗仙名号不相称,“举”字才配李白用。
依我俗人之见,“看”和“疑”是完备可以搭配的,无须引经据典,只要读读李白同期间作品《望庐山瀑布》就知道了,诗中就有“遥看瀑布挂前川”和“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句子,这可是在大白天里睁大眼睛“聚焦”啊!
该当不是“半梦半醒”状态,难道李白真把庐山瀑布误当银河落九天了吗?这也太小儿科了吧。
这话先就此打住,我们暂且不谈改的问题,关键是改过之后,创作的特定环境就不明显了,说它写于扬州可以,写于随州也行,如果诗句中还原了“山月”,那就可以认定是写于随州无疑了。由于李白在扬州时基本上住在江都的旅社里,而江都全境都是冲积平原,连个小土丘都没有,如何体验“举头望山月”?
两个版本的笔墨不同,但意境差异不大:寂静的深秋之夜,月光照到了床前,旅住他乡的李白踱到户外望月,触景生情,思念起身乡——环境是寂静的,思绪是无声的,作者心态也是沉着的,因此,才叫《静夜思》。
众所周知,李白是个很感情化的人,极随意马虎被环境影响,他在扬州待了大约半年的光阴,基本上是在忧郁中度过的,不太可能写出这样宁静的作品。
去扬州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远游,探求伯乐,求人赏识。但那时他还是一个标准的愤青,满脸都写着傲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便是“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既有颜值,又有才华,自以为会人见人爱,哪知第一次口试就被打脸了,渝州(今重庆市)太守李邕跟李白聊了一阵子,承认他才华,但也讨厌他的浮滑,便用两个“呵呵”把他送走了。
开元十三年(725年)秋,李白顺江流而下抵达金陵(今南京市),四处投送简历“谒见诸侯”,无奈“十谒豪门九不开”,只好于次年春辗转天下级大都邑扬州。
哪知扬州也没人搭理他,差不多被当成了空气,从春天到夏天,“伯乐”每天不上班。李白不能不“悲催”,写了一首《白田立时闻莺》:
黄鹂啄紫椹,五月鸣桑枝。
我行不记日,误作阳春时。
蚕老客未归,白田已缫丝。
驱马又前去,扪心空自悲。
从“误作阳春时”和“扪心空自悲”两句看,心里肯定有点烦。岂料“屋漏更遭连夜雨”,晦气的事儿一个接着一个来了。
那时既不能刷卡也不能移动支付,盘缠全靠自己背,他是范例的“富八代”,准备倒是挺充足,除了可直接花的“三十万金”之外,还背着比金子更值钱的祖传宝剑和裘衣。
李白是个豪迈之人,又好一口酒,酒劲一上来,脱手就大方,多给做事员一点小费倒无所谓,问题是此举特殊随意马虎招贼——那年头凡是繁华地带、高消费场所都有专业人士的眼线。
又是一个酒酣之夜,李白一觉醒来,钱袋子被人拎走了。
李白连气带急,很快就卧病在床,好在江都县的孟少府同情他,给他找了最好的郎中,稍有好转时,赶紧写了一首《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徵君蕤》,托人给四川的老友赵蕤捎去。本日读这首诗,怎么看都像是遗书,心情能沉着吗?诗中“良图俄弃置,衰疾乃绵剧”等句子,道出了他空想破灭、疾病缠身的人生窘境。他当时的心情正应了网上的一句话:人生就像一间茶坊,里面摆满了“杯具”……
这个阶段,李白也写过思乡题材的诗,并用到了“明月”,但味道却是完备不同的。品品《秋夕旅怀》就清楚了。
凉风度秋海,吹我乡思飞。
连山去无际,流水何时归。
目极浮云色,心断明月晖。
芳草歇柔艳,白露催寒衣。
梦长银汉落,觉罢天星稀。
含悲想旧国,泣下谁能挥。
“含悲想旧国,泣下谁能挥”,宝宝心里多苦啊!
而《静夜思》中表达的却是一种达人的情怀——还是那句话:李白在扬州写不出这样的诗。
李白一贯惦记司马相如笔下的云梦泽,巧合的是扬州的孟少府与安州的都督马正会有很深的交情,便鼓励李白去安州(今湖北安陆市),既可请马公举荐,又可做云梦之游。
李白离开扬州沿大运河北上,到淮河后一起向西,由河南入湖北襄阳,再南下去了安州。途经陈州(今河南周口店市)时,涌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此时,渝州的李邕已调任陈州太守,估计是不好意思让人看到他现在的样子,李白没去拜访,这不算奇怪,奇怪的是他在大街上挂出了一则广告,欲卖祖传宝剑和裘衣,以解燃眉之急。李邕闻讯大惊,立即差人送去了三千银两。
开元十五年(727年)春夏之际,李白到了心仪已久的安州,也便是本日的安陆市,一欠妥心,在这里实现了他人生的重大迁移转变。自大的李白碰了一圈的钉子之后,无意中把航船驶进了一处避风的港湾。
马都督倒是很欣赏李白的才华,但武官自己没有推举权,就带李白去拜见安州府长史李京,不料这李京不太喜好比他更有才的人,越说李白有才,贰心里越难熬痛苦,以是,荐举之事又“悲催”了。
经历过N多次挫折的李白,彷佛看破了一点点尘凡,内心终于强大起来,由躁动逐渐转为了安静。他在碧山(白兆山)桃花岩的一座小道不雅观安屯下来,除了云梦泽外,还去过临近的随州现光山、大洪山等道不雅观和寺庙,拜道长,访方丈,留下了不少的诗作,《山中问答》记录了他这段心途经程,也被收进了《全唐诗》。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与扬州期间的作品对照,切实其实判若两人,解释此时的李白已然超脱,再不那么多愁善感了。
在盛行早婚的古代中国,27周岁的李白应是超级“剩男”了,但除了能写诗,什么都没有,用本日的标准去评估,肯定算不上是成功人士,由于标志着成功男人的“位子、屋子、车子、票子、娘子”等五大指标一个都没实现。
幸运的是他被一个大户人家看中了,曾任高宗朝户部尚书的许圉师是安州人,有孙女许紫烟待嫁闺中,经随州的紫阳道长牵线搭桥,李白答应做许家的上门半子,但哀求保留独处的自由,可以带着老婆去安州城东北“淮南小寿山”的龟龄不雅观(今广水市境内)小住几天。
于是,这年的秋日,28岁的李白结束了单身狗的生活,在负氧离子爆表的山林中赏明月,饮美酒,拥娇妻,过了一段沉着安逸的生活,才会有沉着的心境写下千古名篇《静夜思》。
如果须要找旁证,他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是最得当的了,文中说:“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已,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乃虬蟠龟息,遁乎此山。”何等洒脱!
文末还写道:“亦遣清风扫门,明月侍坐。此乃养贤之心,实亦勤矣。”多么浪漫!
几年之后,许夫人产下一女一子,李白给女儿取名平阳,以纪念寿山所在地为“平林之阳”;给儿子取名为“明月奴”,意为“玉轮的孩子”,可见他对寿山明月的印象之深。
各类迹象表明,《静夜思》只会写于本日已划归随州统领的广水市寿山,不可能写于扬州。
希望广水、安陆、随州乃至湖北的朋友们共同给力,大声疾呼规复李白的原稿,纵然做不到,也可以让更多的人理解事实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