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恩焘(1865年—1954年),字凤舒,广东惠阳人,清末民初时曾先后任驻古巴、日本邦交际官。一度寓居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后定居喷鼻香港。
廖凤舒是革命先烈廖仲恺的大哥,他用粤语写诗早过霑叔多多声!
黄霑有《不文集》,廖恩焘有《嬉笑集》。廖恩焘的粤语诗专集《嬉笑集》,在嬉笑怒骂中,包含着巨大的社会内容。
民国初年,惯写广州方言诗的廖恩焘,有一首《漫兴》用粤语写的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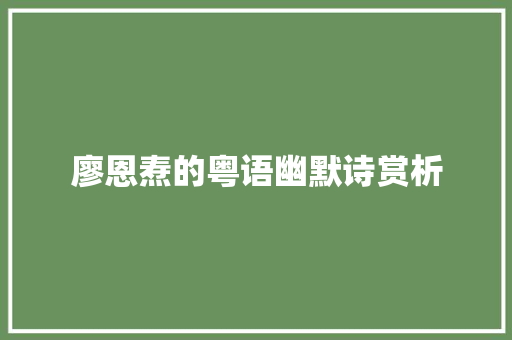
全城几十万捞家,唔够官嚟夹子扒。
大碌藕兼抬惯色,生虫蔗亦啜埋渣。
甲仍未饱偏轮乙,贼点能知重有爸。
似走马灯温咁转,炮台难怪叫车歪。
诗句讽刺贪官:“大碌藕兼抬惯色,生虫蔗仲啜埋渣”。
这里的“色”是指民间艺术活动中的“飘色”,指人们在特定的日子里,敲锣打鼓,抬着化妆成神话故事中的小孩,举办庆典活动。
这里用“抬惯色”来形容贪官招摇过市、追名逐利。“大碌藕兼抬惯色”即说贪官乱花钱还去世要面子;
“生虫蔗仲啜埋渣”,则是说他们捜刮钱财不择手段,连生虫的甘蔗也吃,仲(还)连蔗渣也啜干,十足“孤寒种”。
"大碌藕"则是形容费钱大手大脚的人。为什么形容费钱大手大脚叫"大碌藕?"据市井中人说,列入“泮塘五秀”的莲藕是珠三角百姓的日常蔬菜,又粗又大的莲藕其藕孔也大,洗的时候藏有很多水,人们惯拿着它甩完又甩,而费钱大手大脚者就似大甩银纸(钱),故把乱花钱者称为“大碌藕”。
其余还有一首:
盐都卖到咁多钱,无怪咸龙跳上天。
官府也收水货,贼公专劫落乡船。
剃刀刮耐门楣烂,赌棍扒多席面穿。
禾米食完麻雀散,留番光塔伴红棉。
当时广州通用港币,称为“咸龙”,做找换买卖的十三行银号被人称为“剃刀门楣”,盖因其“出又刮,入又刮”也。
光塔是广州名胜之一,红棉是广州市花。末了两句,颇有鲁迅杂文味道。(聂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