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自网络)
苏轼有一首以花影为题的写景小诗:“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唤童扫不开。刚被太阳整顿去,却教明月送将来。”有人认为这是一首讽刺诗。诗中利用比喻和象征的修辞手腕,讽刺那些倚仗靠山确当权小人层出不穷,像花影子一样,扫也扫不去。“瑶台”比喻高官显贵;“童儿”比喻纯朴忠实的大臣,他们虽然数次抗争,却只能妄然兴叹。“刚被”、“却教”,彷佛成了难以改变的历史规律。诗中既表达了墨客政管理想难以舒展的愤概,又流露出墨客对小人当权得势的无可奈何。
该当说,苏轼的这首《花影》写得非常有情趣,我初读这首诗,第一印象是,花影太可爱了,既顽皮又执着,她喜好美好的地方,追求美好的风光,不管这天间还是月夜,只要有光亮,她都要呆在“瑶台”上,听凭何人,都无法赶走她,可谓“性情倔强、意志武断”。以是,我倒认为,花影是一个明光或者光明的追随者,没有明光或光明,就没有她花影的存在,故而,花影为了自己的存在,听凭他人如何“肃清”和“驱赶”,便是不愿意也不可能“消逝”,除非太阳和明月先从自然界“消逝”!
由此,我想到了人,如果说人如花的话,那么人的思想便是花影了。人的思想向何处去呢?无疑,它该当神往“瑶台”,在阳光或明月的照临下,既要“重重叠叠”,又要“光怪陆离”,更要“光移而动”,要“因光而魅、借光而生”。一个人不能生活在阴郁中,其思想也不能生活在阴郁中,由于没有光亮或光明,连自己的存在都看不到,其思想也就无法现身了,那么所谓的“思想代价”也就无从谈起了。
对同一首小诗, 为什么我的解读或感想与别人不一样呢?实在道理也很大略,正如古人所说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为了证明这一点,非凡再拿“苏轼跟佛印比坐禅”的故事来说一下。一天,苏轼跟佛印比坐禅,坐完了,苏轼问佛印,你看我坐禅像什么?佛印说,像大佛佛。印问苏轼,你看我坐禅时像什么?苏轼说,像一堆大粪。回到家,苏轼得意地说与苏小妹听。苏小妹说,哥哥,人家是心中有佛,自然看你也像佛。你的心中有大粪,以是看人家佛印是大粪。这便是所谓“佛见佛性、人见人性”的道理。有人认为苏轼的这首《花影》诗是一首讽刺诗,而我认为这是一首非常有趣的励志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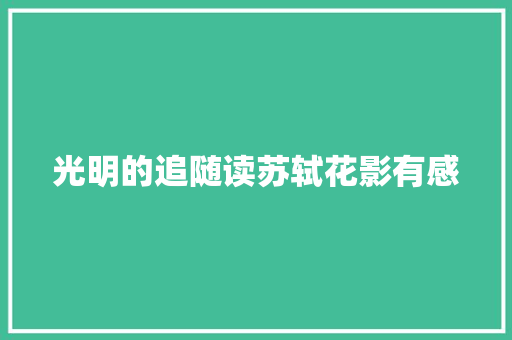
道理如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