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仁”,不仅我们好奇,孔子的学生们也非常好奇,常常追着孔子问到底什么是“仁”,个中,樊迟可能是最忧郁的弟子了。在《论语》里面,樊迟问了三次了孔子什么是“仁”,而孔子给出的答案都不太一样。
有一次,孔子说,仁便是“爱人”,有一次孔子说:“仁者先难而后获”,仁便是先把难的事情做好,然后再谈收成。有一次孔子又对樊迟说,“仁”便是平时的生活起居要端庄恭敬,办事情的时候严明负责,对待他人要忠实。即便到偏远地区去,也不要放弃这些原则。孔子每次说法都很不一样,搞得樊迟很忧郁。
不仅如此,孔子的弟子颜渊、仲弓、司马牛、子张都问过孔子什么是“仁”,而得到的答案都各不相同。孔子对颜渊说“克己复礼为仁”;孔子对子张说,拥有“恭、宽、信、敏、惠”这五种德行便是仁;孔子对仲弓说,出门办事就彷佛去接待嘉宾,叫人办事就彷佛去举行重大的敬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朝中无怨,在家里亦无怨,这便是仁。孔子对司马牛说:“仁者,其言也讱。”,仁便是说话不要那么慌张,轻微端庄点便是仁。
你读到这些,可能就很奇怪了,为什么这么主要的一个观点,在孔子这里彷佛非常随意?实在并不是,由于《论语》实在是一部孔子和弟子的对话集,是对话就有场景,以是,每次孔子回答不一样,是由于当时问话的人和场景不一样,这是孔子在因材施教。比如孔子见告司马牛说话要缓慢一点,是由于司马牛是一个直肚直肠的人,常常说话口无遮拦,以是孔子才说:“仁者,其言也讱。”,以是,实在孔子是在因材施教,并不是随便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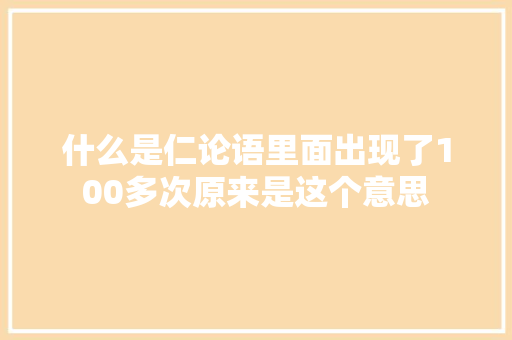
那究竟什么是“仁”呢?它有两个内涵。曾子说:“役夫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是孔子的弟子,也是孔子思想紧张的继续人,曾子参与体例了《论语》、撰写《大学》,以是,曾子对孔子核心思想的把握该当比较准确。如果说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仁的内核就两个字:“忠恕”。
什么是忠恕,宋代大儒朱熹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忠强调自我的任务和责任,做自己该当做的事情,恕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同时对待他人要用同理心,做到这样便是“仁”了,这便是“仁”的终极判断标准。
做自己该做的事,这是一种“代价判断”,而不是一种事实判断,它强调的是在某个场景下我们最该当做什么,而没有一个普遍确定的标准和原则,能适用于任何一个场景,以是每次孔子给出的答案都不一样。那我们是如何做出这种判断的呢?答案是:心。仁的判断来自于“心”,而不是“脑”,一个人的“心”才是”仁”的本体,这是后面孟子的一个突出贡献,孟子在孔子的“仁”的根本上,找到了仁的本体,那便是“心”,并扩展了孔子“仁”的理念。
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在孟子看来心才是一个人的真正主体,心不仅仅是仁义礼智这些道德品质的来源,而且心有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以是,我们说儒家思想是一种审美取向,他的判断不是由我们大脑做出的,不是基于理性和逻辑推理的,而是由民气做出的。就像我们去欣赏一幅画,欣赏艺术作品给我们带来的审美乐趣,是一种心身的愉悦感想熏染,而不是大脑理性做出的判断,什么是好的、善的、美的,我们的“心”有天然的直觉或者说一种判断能力。这是东西方哲学思想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良知和本心更靠近于一个人真实的自我,我们常常说“要追随你的内心”这是一种很高哀求,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按照你的本心良知干事还恰到好处,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