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史中的苏欧情意
杨万里的《诚斋诗话》里这样记载:\"大众欧公知贡举,得东坡之文惊喜,欲取为第一人。又疑为门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议,抑为第二。坡来谢,欧公问:\公众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见何书?\"大众坡曰:\"大众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大众欧阅之,无有。异日再问坡,坡云:\"大众曹操以袁熙妻赐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以妲已赐周公。'操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不雅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大众欧退而大惊曰:\"大众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异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公众可见欧阳修的气度,苏轼的学识。古代文人之间的交谈,每每见到,总是叹其风骚文雅。这两位大文豪从第一次见面便相互吸引,成为石友,不可不叹缘分之妙,他们必是为对方某一方面的才华所吸引。他们的相聚相知,在几千年后的既喜好苏轼又喜好欧阳修的我们的眼中又是若何触目惊心的欢畅。那样两个皎皎豁亮清明的两个人,我们喜好的人,他们也曾在光阴的某一个刻度里把酒言欢、以心换心。虽然相遇如此美好,却又不得不面对这份悲哀,一个人的脚步已走向孟婆忘川,另一个人的脚步却还在繁华尘世。面对曾经光景,苏轼怎能无动于衷,于是一首《西江月.平山堂》留下当时的心迹。
二、苏轼《西江月.平山堂》与欧阳修《朝中措》的渊源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东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苏轼《西江月.平山堂》平山堂始建于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当时任扬州太守的欧阳修,极其欣赏这里的清幽古朴,于此筑堂。《舆地纪胜》:\"大众负堂而望,江南诸山拱列檐下,故名。\"大众这是平山堂之所以为名的缘故原由。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刘敞迁右正言、知制诰。次年八月,出使契丹,在契丹一年。嘉祐元年(1056)出守扬州。刘敞与欧阳修关系密切,在得知这个后,欧阳修便写了一首词酬赠于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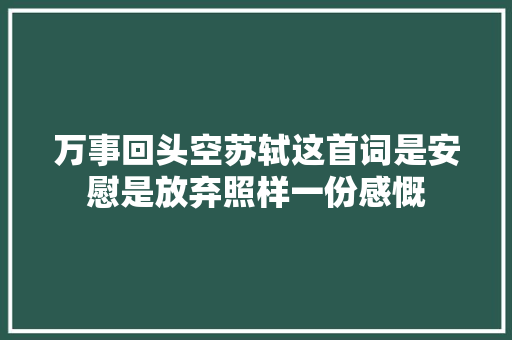
苏轼的这首词十分大略,却拥有极强的感发力量。它没有分外的手腕,像《词学十讲》中\"大众直是盘空硬语,一片神行,而层层推进,笔笔逆挽,真是'有大气真力斡运其间',却又泯却转、接、提、顿的痕迹\"大众所评价的《永遇乐》;亦无《江城子》\"大众十年死活两茫茫,不斟酌自难忘\"大众的深情。在这里,苏轼是奔波的游子,在外的宦客,镇静思考人生的智者。
三、苏轼《西江月.平山堂》之解读
上半片是\"大众兴\"大众,下片是有兴而感。\公众三过平山堂下\"大众,直到作此词为止,苏轼曾三次途经扬州。第一次,公元1071年(熙宁四年)由京赴杭州通判,南下经由维扬;第二次,公元1074年(熙宁七年)由杭州移知密州,北上途经维扬;第三次,公元1079年(元丰二年),从徐州移知湖州(今浙江吴兴)。\"大众三过\"大众浓缩了苏轼近十年间南迁北调的官场生涯,而此时的苏轼已经四十二岁了。\公众半生弹指声中\公众用夸年夜的比喻来表现光阴飞逝。\公众弹指\"大众佛教用语,比喻韶光的短暂。《翻译名义集》卷五《时分》:\"大众时极短者谓霎时也\"大众,\"大众壮士一弹指顷六十五霎时\"大众,又云\公众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为一弹指\公众。苏轼在熙宁四年于扬州谒见欧阳修,至此已经九年,十年举成数,故为\"大众十年不见老仙翁\"大众。\公众壁上龙蛇飞动\"大众是苏轼看到了欧阳修曾作扬州太守时在平山堂留下的墨迹给人的感想熏染。\公众文章太守,杨柳东风\公众是欧阳修《朝中措》中句词。在平山堂下,仍可以听到当年的歌,堂前垂柳依旧,太守何在?苏轼总是在不经意间思考自然永恒和人生短暂之间的抵牾。\"大众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大众,\公众游人寻我旧游处,但觅吴山横处来\"大众,黄楼依旧、吴山依旧,东坡何在,太守何在?白居易《自咏》:\"大众百年随手过,万事转头空。\"大众而苏轼则更进一层\"大众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公众,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六云:\"大众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公众追进一层,唤醒痴愚不少。\"大众\"大众欲吊\公众\"大众仍歌\"大众均采取原句,重现当时欧阳修风骚自赏之态,又有欧公手植杨柳、所题诗词存留世间,可堪抚慰。然再深想一层,和桓温说\"大众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大众,相似却又有更深的感慨。欧公早已离开人间,苏轼心中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苏轼与欧阳修亦师亦友,他们二人才华斐然、文人相倾。
\"大众万事转头空\"大众是安慰,是放弃,还是一份感慨。在战乱的年代,这种寂寞的声音便在世间回响。《古诗十九首》中\"大众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大众\"大众人生忽如寄\"大众;建安期间的年夜方凄凉,这是一种意识,在苍茫中看到了自己与天下的关系。苏轼可能是落寞的、压抑的。半生弹指而过,他肚量胸襟天下,想要治国平家,却一贬再贬。他说\公众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大众,人生涯着,也未尝不是幻梦一场。大概正是心怀此念,他才得以坦然的面对纷至沓来的政治打击。
笔墨真是一个很奇妙的事物,一旦变成笔墨,大概和作者有关系,大概就无关了,它已经自我完成了。读作品可以如孟子所说的\"大众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大众,如上文所说。更特殊的是读者可以进行再创造。即笔墨接管和读者批评,可谓\公众一千个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公众。只管说人间如梦,万事转头空。可是我们毕竟是处在梦中的人,梦中的欢笑和泪水都是真的,纵然是梦,我们也都真实的存在着,大概未来的某一天,当我被生活撞的头破血流,当我不得不放弃执念,当我不再年少浮滑,我会对自己说\"大众万事转头空\公众,不要空执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