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重晚晴”现在的意思是说,人们都比较尊重年纪比较大、德高望重的人,或者说,类似于夕阳红,人们比较重视老年人的情绪问题。
原来并没有这个说法,当李商隐写这首《晚晴》的时候呢,他才三十四岁,而当时心情还不错。
李商隐当时去郑亚幕府做幕僚,阔别中心的牛李党争,可能这让他松了一口气,算是他摸爬滚打生平中比较平稳的期间。这就像杜甫颠沛流离半辈子,仅仅在成都草堂过了几年安稳日子。以是杜甫那个期间的作品,不但有《戏为六绝句》这种诗词理论的出身,同时也有比较轻快的作品,如“黄四外家花满蹊”之类的,这种心态就很轻松。
李商隐在桂林时的心态就和杜甫在成都期间差不多,我们大概就知道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状况,也便是这首诗的创作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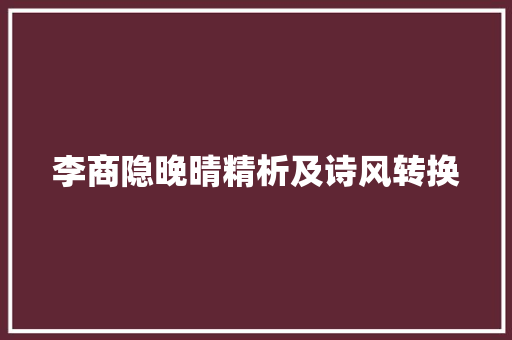
晚晴
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
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
这是一首平起入韵的五言律诗,押平水韵“八庚”部。晚唐格律诗的规则都已经很完善了,作为晚唐代表性的墨客,李商隐的作品少有出律,是非常完美的。因而读起来也是高低有致,音律豁亮清明。
李商隐诗的特色,便是用典精湛、构思新奇。他的作品首创了古诗中的朦胧派,以是他被北宋的西昆体尊为创始人。李商隐兼容并蓄了从南北朝到中唐墨客的所有艺术特色,在表现手腕中是最繁芜的。他属于这种集大成的墨客,爱情诗写的特殊缠绵悱恻、幽美动人,而且机关重重,让人有些猜不透,摸不清的觉得。代表作《锦瑟》,一贯到如今还有很多人在辩论,他到底写的是爱情还是交情还是境遇,都有各种预测。
实在我们要把握李商隐的诗,须要有一个观点。
读李商隐的诗,我们不须要去理解前因后果,由于他着重的是表现、布局一个情境,然后去书写这个情境,至于这种情境是从何而起,他并不想见告我们。大量阅读他的诗,就会创造李商隐和前期唐诗风格不同在于“情”的构建。
唐诗大多是寓情于景,那么就肯定是要通过写景致,或者写事情来表达墨客的感情。李商隐的不同在于他是塑造一种感情,便是集中力量写感情的形状,而不是通过景致来反响感情,如“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你以为这是写景吗?这是描写感情的样子。这就有点像北宋开始的造景说事,不过他还是根据自己的真实感情根本来塑造这种情境,以打动读者,并非像宋诗一样无中生有的捏造出各种景致,来达成自己的说教目的。
这是李商隐诗的主要特色,也是诗歌在发展过程中的艺术手腕不断呈现。
但是当李商隐不写自己不想说的爱情经历,或者在官场上不得志的时候,他的诗实在还是唐诗的那种比较清晰明白的风格,这首《晚晴》便是这样。
以是《晚晴》实在并不像李商隐有名于世的诗歌风格,这首诗很好懂。
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夹城便是两边都筑有高墙的通道。一个人深居简出的,住在一个城楼上,当时他是在郑亚幕府,那便是桂林城内了。身居高楼,俯视着城下的通道。春天已经由去了,夏天刚刚开始,这便是春夏交卸的日子,温度适宜,清和气爽。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这可能是老天爷也可怜那些宁静处的小草吧,终于放晴了。人们也很珍惜这傍晚时的晴天。这里晚晴便是傍晚的晴天,是最大略的本意。
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并”是“更”的意思,更加上这个楼又比较高,以是就看得远。“微注”,便是写晚景斜晖,光芒显得微弱,温顺。由于自己的楼很高,斜阳,透过小小的窗户,晒进来,让人觉得比较温暖。
这里就注入了感情。由于他在桂林过得还行,郑亚很信赖他,相处起来也比较有人情味。李商隐在官场受尽牛李党争的夹心气之后,在这里觉得统统都比较顺畅、合拍,以是才有这种“微注小窗明”——温暖的阳光照在身上的觉得。他当时的心情,该当确实是觉得比较轻松、比较舒适的状态。
他这里实际上还是在写景。这首五律,并没有遵守律诗的普遍文法。一样平常来说,是“起承转合”。首联写景,颔联细化铺陈,然后颈联发生迁移转变,转到其他方面去描写,为整首诗带来灵动变革的觉得。但是从中唐韩愈的散文入诗开始,这种格式逐步被冲破,当然后期大部分人还是遵守“起承转合”的普遍文法。不过到了李商隐这种对诗文有风雅构思的大墨客手上,就会发生变革。
这也是许可的,由于文法这个东西只要你写的好,只有大式,并无定式。
李商隐这首五律的颈联和尾联都是在写景,给人一种前朝墨客作品的觉得。
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越鸟便是南方的鸟。他现在是在桂林,用越鸟来指代他自己也是可以的。巢干便是越鸟的窝被晒干了。这里依然在写景,他开始写“人间重晚晴”,实在便是交代韶光是在雨后。雨后涌现了晴天,以是才会是“天意怜幽草”,老天爷也是可怜这些草一贯被雨水淋湿。
这个用来形容他在经由刘李党争两方受气的情形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份自己觉得还比较舒心的事情时的生理状态。这种比喻挺故意思,原来就像鸟儿一样,没有一个干燥的窝,被连绵不断的雨打湿了,湿湿哒哒的,肯定不舒畅。现在让晚晴给晒干了,鸟归巢的时候,飞行的体态就格外轻盈。
这是一种不雅观察细致的景物描写,同时融入了李商隐的个人想象。他这种通寓情于景,是可以明显觉得到的。我们平时在经由了一些事情之后,是不是也以为一身轻松啊?鸟窝被晒干,羽毛也晒干了,鸟儿飞起来非常轻灵,用来形容人这种生理放松的状态,是非常得当的。我们在对动态景物的想象中就读懂了他的这种心态,不须要过多的笔墨阐明和描述。
实在我在读到他这几句的时候,想起了陶渊明的“山气早晚佳,飞鸟相与还”那种轻松淡泊的生活状态,当然李商隐当时和陶渊明的隐居状态还是不同的,只不过我读出了这种觉得。陶渊明的那首诗,末了还有两句“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而李商隐的这首作品,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不再啰嗦。
这便是东晋诗和唐诗的差异。
唐诗写这些景致,目的也是见告你这个里面有真意,但是我也不明说,你自己就该当体会得到。而且都是通过比较大略的字词来写这种常见的景致,让人们去感想熏染,读懂墨客的创作心态,从而得到一种共鸣,形成读者和墨客的通感。
这首诗才能够真正的广为流传。
这便是一首比较轻松的表达自己心境的五言律诗。“人间重晚晴”,虽然说本日的意思和他原来的本意不一样了,但是并没有什么关系。个人以为这首诗中最有味道的还是后面四句,“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这是一种比较轻松舒适的心态,可能更适宜我们在本日引用。
《晚晴》和李商隐其他诗风格不一样,更类似于前唐,初唐盛唐期间的诗风,其背后的缘故原由便是他当时的心情和生平的悲哀、烦闷的不同,这种心态直接影响了他的创作。我们也可以从这首诗里看出唐诗的传承性,李商隐个人风格色彩的变革,以及对唐诗的全体变革趋势的影响。
李商隐是晚唐最主要的墨客,也是由于这一点。
(此处已添加圈子卡片,请到今日头条客户端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