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这对“六义”作了更为详细的阐明。以是《诗经》六义便是指风、雅、颂,赋、比、兴,个中前三个指《诗经》的体式,后三个指《诗经》的表现手腕。
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而划分的。风即十五国风,是各地的音乐曲调,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桧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豳风、陈风、曹风十五部分,共一百六十篇。雅分为大雅和小雅,是朝廷正乐,共一百零五篇,个中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三个部分,分别有三十一篇、四篇、五篇,为郊庙敬拜之乐。
赋、比、兴作为《诗经》的表现手腕,宋代朱熹在《诗集传》曾有清楚的阐明:“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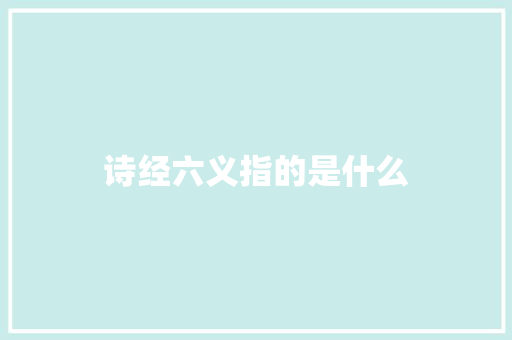
大略说来,赋便是直截了当地表达所要陈述的思想感情,如《邶风·击鼓》所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便是很直接、很热烈地将自己的爱情誓言表达了出来;再如《卫风·氓》险些通篇都是利用“赋”的手腕,将一个弃妇的怨情毫无保留地诉说出来。
比便是打比方,拿一件事物来比拟另一件事物,如《卫风·硕人》中形容美人是“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魏风·硕鼠》一诗将贪得无厌的统治者比喻成一只大老鼠。
兴指的是诗歌在音乐上的起调或用来引起主题的景物或象征物,如《关雎》开篇就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前两句即为起兴,浸染在于引出君子追求淑女这件事;《秦风·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周南·桃夭》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等也是如此。值得把稳的是,《诗经》当中常常是两种或者三种表现手腕同时利用,利用单一表现手腕的作品是不多的。
《诗经》“六义”的说法对后世影响深远,一方面形成了我国诗歌史上的“风雅传统”,另一方面,赋、比、兴的手腕也被后世诗歌所继续,如汉大赋中的“铺陈”便是由“赋”发展而来,《楚辞》中多“隐喻”,是受了“比”的影响,“兴”的手腕则为《古诗十九首》等汉魏诗歌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