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叔齐的业绩被司马迁写进《史记》里,《伯夷列传》是《史记》七十列传的首篇,而且篇幅之短,在全书中罕见,《伯夷列传》最让人感到讶异的是,此文大部分内容并不是在谈伯夷叔齐的业绩,而是引经据典,借题发挥,太史公想表达若何的个人情怀和精神寄托?
这次我们去往渭源首阳山,神秘的伯夷叔齐采薇地,一探究竟。
伯夷叔齐画像。
1. 伯夷叔齐身份竟是孤竹国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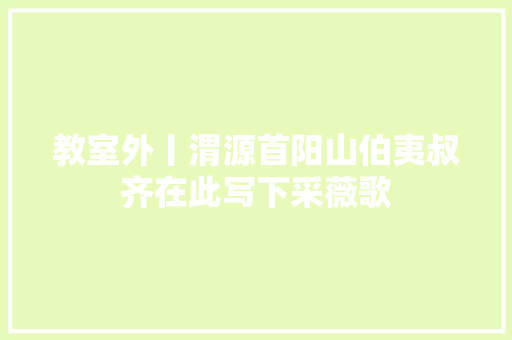
渭源首阳山,传说是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避世采薇之地,独特的丹山、碧水、绿林,在陇上浩瀚丹霞地貌中独树一帜。
一到渭源县莲峰镇,沿着莲峰河溯源而上,风景变得奇异起来,山峦攒聚过来,车窗右侧,有两座形如竹笋、马鞍的山峰矗立在面前,像是在迎客,在清晨阳光的映射下,从山脚到山腰,恍若有红、黄、橙、绿、白、青灰、灰黑、灰白等多种色彩在模糊流动,让人情不自禁想到“丝滑”这个词语。
进了首阳山山门,两边赤赤色的山峦仍旧显露丹霞地貌“陡崖”的特点,山路再往深里走,“丹霞”不见了,山林绿色的波涛一浪浪地袭来,将我们裹挟在个中。首阳山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莲峰山,因此山形取名。清代墨客吴镇的诗句“五峰云散尽,涌出碧莲花”可状其美。
登山到瞭望台眺望,大的山峰有九座,大山、二台、三台、四台、五台、后五台、玉皇洞、释家庵、老君山等等,一座比一座奇,一座比一座美。
来到首阳山的伯夷叔齐,这两位身份可一点不大略,他俩是孤竹国王子。孤竹国,一贯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神秘王国,有史料说大致就在冀东至辽西一带,在公元前17世纪时,被商王朝开国元君商汤封国,这便是孤竹国了。
孤竹老国君去世前留下遗言,命少君叔齐继位。按照当时的规矩,宗子该当继位。伯夷却说:“该当尊重父亲的遗嘱,国君的位置应由叔齐来坐。”于是他放弃王位,逃出孤竹国。大家又保举叔齐做国君。叔齐说:“我当了国君,于兄弟不义,于礼制不合。”也逃出孤竹国,和伯夷一块儿过起了流亡生活。
他们这种“让贤”的举动,受到当时的人赞赏。到了春秋战国时,儒家学派更是大为讴歌,评价说:“能以国让,仁孰大焉,伯夷顺乎亲,叔齐恭乎兄。”
在亡命的日子里,为躲避商纣王的残暴统治,伯夷、叔齐居住在北海之滨,和东夷人一起生活。后来,他俩听说周文王在西方兴起,是仁义之君,就相约去投奔他,但刚走到半路,就遇见了周武王的大军。原来,这时周文王刚刚去世去,周武王率领着大军奔袭商纣王。看到这种环境,他俩大失落所望,于是扣马而谏:“父去世不埋葬,就动起武来,这能算孝吗?以臣子身份讨伐君主,这能算仁吗?”但武王根本不听他们的见地。
周武王与商纣王大战于牧野,由于商纣王阵前的奴隶士兵倒戈,周武王很快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灭掉了商朝,建立了新的王朝——周朝。
伯夷、叔齐听说后,认为这种做法太可耻了,起誓再也不吃周朝的粮食。他俩就相携来到首阳山上采集白薇吃,作《采薇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2.孔子荀子对伯夷叔齐十分推崇
他们吃的薇便是本日我们能吃到的蕨菜。渭源县首阳山一带雨量充足,景象阴湿寒冷,良好的土壤十分适宜蕨菜的成长。
渭源首阳山。
凉拌蕨菜自然是说不出的甘滑鲜美,但如果伯夷叔齐不吃别的,只是每天吃、月月吃、年年吃它,想想都让人皱眉,而绿的、青紫色的蕨菜常见,但白薇又长的什么样子容貌呢?当地老人说那是神仙菜,一样平常人见不到,有民谚说:“首阳山的白蕨菜,早上出来晚上败!
”而伯夷叔齐在渭源民气中不是神仙,那也相差不远!
还有这样的民间传说,听说一位农妇一日上首阳山上采集蕨菜,瞥见两个瘦骨嶙峋、容貌高古的老人也在那里干着同样的事情,她就问询起来。听到两人耻食周粟,农妇笑了:你们两人倒是很有骨气,不吃周朝的粮食,但你们也不想想,普天下都是周朝的呀!
这山,这山上的野菜,也是周朝的,你俩为啥还吃呀?伯夷、叔齐如梦初醒,于是连蕨菜也不吃了,从此开始绝食,双双饿去世在首阳山上。
在一些人眼里,他们成了因循守旧、食古不化、迂腐透顶的范例形象。但在古代的先贤、忠臣、义士们眼里,他们的业绩却是可以与舜、禹的英名一样千载扬名。
孔子的学生子贡曾问:“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立即回答:“古之贤人也。”平时,先生长西席回答问题时,都要慎重考虑一下,然后才“子曰”,可孔子评价伯夷、叔齐的时候,没有任何犹豫,张口就说是贤人,可见孔子对伯夷、叔齐的所作所为是非常肯定的。荀子也惊叹,伯夷叔齐的名声,就像日月一样。
孔子荀子高度肯定伯夷、叔齐,解释他俩的行为比较符合儒家的代价不雅观,儒家认为人生代价不在于得到什么功名利禄,而在于对社会作出了什么贡献,对后世有什么影响。以是孔子强调:“伯夷叔齐……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非圣贤而能若是乎!
”
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也表明他的态度:伯夷、叔齐绝不是为了万古长青才那样做,他们只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态度罢了,他们给后人留下的,是一种独立的人格、一种独立的精神,是一种以生命为代价的执著,这正好是许多人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事情。
伯夷叔齐塑像。
伯夷、叔齐是否来过渭源境内,首阳山五台碑湾一块名为《首阳山辩碑》的明代石碑,洋洋洒洒千余言,有非常详细的论证。在海内,以首阳命名的山显然不止渭源这一处,而每一处都有伯夷叔齐的民间故事流传不绝。首阳山究竟在哪儿?不仅困扰着今人,也困扰着古人,明万历二十三年户部主事杨恩就此事撰文进行论证,后被人雕刻成碑,立在首阳山。这块碑高两米多,宽一米半,碑文认为全国虽有五处首阳山,而以渭源首阳山为真。作者引经据典,多方论证。刻石字迹清晰,书法刚劲有力,堪为明代碑碣书法中的上品。
石碑的背面刻的是崇祯年间,当地官员撰写的碑记,先容了伯夷、叔齐的平生及历代奉祀概况,并解释了改建的缘故原由和经由。由于此碑论据确切,资料翔实,引起了史家的重视,清代名臣左宗棠还以此碑文为原本,撰写了夷齐庙碑文。
3. 历史上有这两人比没有要好得多
对付伯夷叔齐两位先贤的敬拜自古有之。古时渭源首阳山包括俗称“莲峰山”和夷齐古冢所在地享堂湾(本日埋葬伯夷叔齐的墓地)两地。为了官员敬拜方便, 明朝末年,将莲峰山五台湾夷齐庙迁于山外阳坡里,后毁于兵火。从此, 首阳山与夷齐古冢分开成为两个地方,也成为两个名字了。大约在清初,始将夷齐庙迁修到现在的享堂沟,并更名为“清圣祠”。
不同于远处的群山巍峨嵬峨,蜿蜒东去,夷齐古冢所在地却是低矮的山冈围抱的一处普通的小山村落。享堂湾中的“享堂”两字从词义上有这样的阐明:祖堂也。安置祖之像牌以祭享之,故云享堂。而这个山村落的名字就叫首阳,显得不屈常。
伯夷叔齐古冢,左宗棠题写对联。
果真在路边,就看到一座题写着“夷齐古冢”匾额的高大牌楼,山坡上森森郁郁的松柏显示入迷秘、肃穆的气候。沿着石阶缓步向上,浸润着山中午时的寂静,呼吸也变得深奥深厚绵长。
伯夷、叔齐的墓冢就在山湾的正中,两抔黄土隆起,像是伴生的双子星座,其上青草翠蔓,冢前尚未熄灭的喷鼻香火袅袅婷婷,让人陡生追思怀远之意。
冢前是一座碑亭,墓碑上有清代名臣左宗棠题写的“有商逸民伯夷叔齐之墓”,墓碑的篆额是“百世之师”。碑亭两边对联是“满山白薇,味压珍馐鱼肉;两堆黄土,光高日月星辰。”横额为“高山仰止”。或许正是有先贤长眠于此,再小的山冈也会成为精神高地。
古冢之上便是形制大略的清圣祠,每年农历四月初七,生活在首阳山周围数十公里的群众,以及周遭几百公里和渭河下贱的文人雅士,或乘车,或步辇儿,自带干粮,晓行露宿来到首阳山清圣祠,等待越日四月初八敬拜活动的到来。
“伯夷叔齐敬拜”已成为省级非遗项目,它被认为“渭河源头公民群众在分外的首阳山夷齐遗冢的自然景不雅观和文化历史环境中形成的一种‘文化空间形式’”。
的确,历史上有这样两位人物,就为后世之人在生命哲学上供应了一个参照,这比历史上压根儿就没有这两个人要好得多。他们的采薇和绝食,虽说不上富有激情,但却像花木掩映的深井,充满哲学意味和诗意,深刻而执著,让人回味。
文丨奔流新闻 刘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