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王
大家好,我是老王。
本日咱们来聊一个严明的话题:诗经时期的人们,究竟是怎么骂人的呢?
先别急着骂我。韩愈先生长西席在一千多年前已经说过:“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而当人遭受了不平的境遇、面对着阴郁与痛楚,自然也有着痛高兴快去骂一场的冲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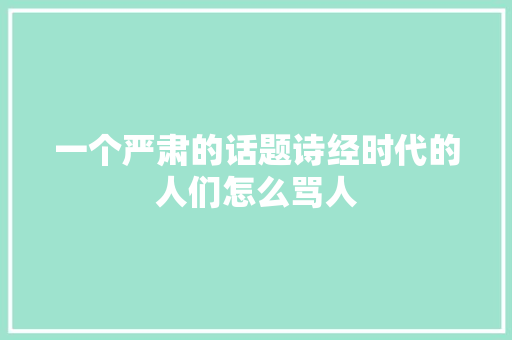
因此,骂人,在我国文学史上,实在有着相称悠久的历史渊源,自古及今一贯绵延不绝。君不见骆宾王同道那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上来便是“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还说人家什么“虺蜴为心,豺狼成性”“杀姊屠兄,弑君鸩母”,把一代女皇骂得那是狗血淋头。
而这种骂人的传统,如果一贯往前追溯,可以追溯到我国第一部成型的文学作品——《诗经》。
很多人对付《诗经》的印象,每每以为它是一部以爱情诗为主的民歌总集,实在这种意见多少有些偏颇。
《诗经》的相称一部分篇目(尤其是《大雅》《小雅》),都是具有相称明显的政治意图的,个中不乏对统治者及贵族进行称美或怨刺的诗歌,也便是学术上所谓的“美刺诗”。而个中对其表示不满和批评的部分,自然便是我们所说的“怨刺诗”。
可千万不要鄙视“怨刺”主题在《诗经》中的地位。我们知道,《诗经》中有风、雅、颂三个部分的诗歌(个中“雅“又分”大雅“”小雅“),而“风”“雅”两部分诗歌中,各有一部分诗歌被称为“变风”和“变雅”,个中大部分便是以这种怨刺为主题的。
《诗大序》中有这样一段话:“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落,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落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用大口语来说,一旦君王做的不好了,政治阴暗了,刑罚严苛了,就轮到墨客们登场来作诗讽谏了。因此,怨刺本来便是当时《诗经》的主要目的之一。
原则上来说,儒家不雅观点下的《诗经》该当是“温顺敦厚”的,纵然是怨刺也该当是”主文而谲谏”,也便是以比喻的办法委婉讽谏的。但我们可以想见,在“王室遂衰,蛮夷交侵,暴虐中国”(史记·周本纪)的年代,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闲情文雅来进行委婉劝谏,更多人想的恐怕便是一个字——
骂!
骂就完了。
只有痛高兴快地把我内心的痛楚和压抑都骂出来,我才能一吐为快,而在委婉劝谏已经失落效的情形下,也只有这种言辞激烈确当头一棒,才能给君王敲响末了的警钟。
因此,这些近乎于“骂人”的、言辞激烈的怨刺诗,就这样出身了。
但是,在《诗经》这样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诗集中,怨刺诗的写法也是五花八门。按照写作手腕来看,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两个不同的流派——“比喻象征派”和“直抒胸臆派”。
1、比喻象征派
这一派是怨刺诗中相称强势的一派,以比喻生动、讽刺辛辣著称。该派中的怨刺墨客,充分地发挥了诗经“六义”中“比”和“兴”的功夫,加以他们的奇思妙想,把他们讽刺的工具比作各种各样神奇的东西。
如果要问该派之首,那恐怕非大名鼎鼎的《硕鼠》莫属: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
三岁贯女,莫我肯德。
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
三岁贯女,莫我肯劳。
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诗经·国风·魏风·硕鼠》
“硕鼠”,便是大老鼠的意思。如果把这首诗大略翻译成当代汉语,大概便是这样:
大田鼠呀大田鼠,不许吃我种的黍!
多年费力奉养你,你却对我不照顾。
起誓定要摆脱你,去那乐土有幸福。那乐土啊那乐土,才是我的好去处!
大田鼠呀大田鼠,不许吃我种的麦!
多年费力奉养你,你却对我不优待。
起誓定要摆脱你,去那乐国有仁爱。那乐国啊那乐国,才是我的好所在!
大田鼠呀大田鼠,不许吃我种的苗!
多年费力奉养你,你却对我不慰劳!
起誓定要摆脱你,去那乐郊有欢笑。那乐郊啊那乐郊,谁还悲叹长呼号!
《毛诗序》对这首诗是这样阐明的:“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直接把自己的国君比作大老鼠,讥讽他苛税重敛、不修德政,可以说是辛辣至极的讽刺了,而“硕鼠”一词,至今也依然被用作国之蠹虫的代名词。
既然国君都可以如此讽刺,别的的作歹者自然也难以幸免。和以“硕鼠”比喻贪腐者同样精妙,墨客们给了那些摇唇鼓舌、喜进谗言的小人另一个比喻——青蝇。
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
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
营营青蝇,止于榛。谗人罔极,构我二人。
——《诗经·小雅·青蝇》
这首诗字面意思还是很好懂的,这里就不放翻译了。
这个“营营”,便是苍蝇飞舞的声音,类似于现在“嗡嗡”之类的拟声词。把那些像是像是苍蝇一样四处乱飞、嗡嗡乱叫、危害公民的进谗之人比作“青蝇”,实在是再贴切不过。而在比喻之后,墨客还担心被劝诫的国君听不懂,补了一句“岂弟君子,无信谗言”,并给出了两个情由:谄人不但会“交乱四国”——恶化多个国家的情形,也会“构我二人”——挑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阐明得不能更明确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营营青蝇”的故事并没有在这里就结束。你可能没看过这首诗,但你很可能见过一个著名的针言。韩愈老人家在《青蝇》这首诗里截取了“蝇营”两个字,然后天才地自己加上了“狗苟”两个字,放在了自己的《送穷文》里——于是,“蝇营狗苟”这个针言出身了。
除了老鼠和青蝇,像是鹌鹑和喜鹊这样的鸟类同样也成为了用来讽刺的喻体。这回,墨客骂的是另一种不合于社会礼法的行为——淫奔。
鹑之奔奔,鹊之彊彊。人之无良,我以为兄!
鹊之彊彊,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诗经·国风·鄘风·鹑之奔奔》
很多学者认为,这首诗是妻子用以讽刺责怪丈夫不忠的。喜鹊和鹌鹑尚且出双入对、忠于配偶,自己的丈夫却沾花惹草、不能忠实。因此,妻子发出了“人之无良,我以为兄”的嗟叹与斥责。
但也有传统说法认为,这首诗讽刺的实在是有详细所指的——便是卫宣公的夫人,宣姜。《毛诗序》中说,此诗为“刺卫宣姜”之作,“卫人以为宣姜鹑鹊之不若也”。认为宣姜整天与公子顽跬步不离,有违礼法。当然,该诗的“作诗之义”究竟是否为此,至今依然是一个有着相称争议的话题。
这种通过比喻和象征来进行讽刺批评的办法,在诗经的“国风”和“小雅”两个部分中是比较常见的。
墨客们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用各种各样的动物来对他们想要讽刺的人物进行比喻,从而达到更加形象生动的讽刺效果。而在“小雅”的另一部分诗歌和“大雅”中,更加常见的是怨刺诗的另一个派别,我们称之为——“直抒胸臆派”。
2、直抒胸臆派
如果以武侠小说中的武器作比,“比喻象征派”的墨客利用的便是小李飞刀,讲究迅速精准、刀刀毙命,而“直抒胸臆派”的墨客用的则是独孤求败的重剑,以绝对、直接的力量,给人以无与伦比的震荡效果。它通过笔墨的直接铺排和情绪的直接表达,来达到其希望的表达效果。
如果说“比喻象征派”的掌门是《硕鼠》一诗,那么对付“直抒胸臆派”,我则要隆重推出《大雅》中的两首“姊妹篇”——《板》《荡》。
熟习李世民的朋友们可能知道,他写过一首《赋萧瑀》,开篇一句便是妇孺皆知的“疾风知劲草”,而接下来一句便是“板荡识诚臣”。而“板荡”这个词,之以是有“社会阴郁动荡”的意象,正是出自《诗经》中《板》《荡》两首怨刺诗。
大雅中的诗歌普遍比较长,全文我就不给你们罗列了,摘取几个片段:
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犹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亶。犹之未远,是用大谏。
——《诗经·大雅·板》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诗经·大雅·荡》
如果你轻微负责看一下这两首诗,就会知道我说它们是姊妹篇是有着相称的情由的。这在它们的首句就已经表示出了惊人的相似:
上帝板板,下民卒瘅。——《板》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荡》
“板”是反常,“荡”是动荡,总之都不是什么好词。但值得把稳的一点是,两首诗责怪的工具彷佛都是“上帝”——这个“上帝”是啥?
放心,反正和耶稣不是一回事儿。古人口中的“上帝”,大概类似于“天帝”或者“天”,总之是对上天的一种称呼。崇奉定命的周人,在面对政局动荡、社会混乱之时,只能直接向上天发出责怪——上天为何如此反常、如此动荡,使得你的公民白白遭殃?
而这种对付上天的责怪,实在同样针对着当时的君王本人(周人认为君王承定命),而《板》《荡》两首诗,责怪的都是周厉王本人,也便是不让国人在路上评论辩论国事,只能“道路以目”的那位。
同样是对上天和君王的责怪,两首诗的写作风格也有着些许的不同。《板》的风格,有点类似与苦口婆心的说教:
天之方难,无然宪宪。天之方蹶,无然泄泄。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译:天下正值多难多难,不要这样作乐寻欢。天下恰逢祸患骚乱,不要如此一派胡言。政令如果折衷和缓,百姓便能融洽自安。政令一旦坠败涣散,公民自然遭受苦难。)
而《荡》的风格,则是正言厉色的质问和责怪:
曾是彊御?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译:多少凶暴强暴贼,敲骨吸髓又贪赃,窃据高位享厚禄,有权有势太专横狂。)
一样平常认为,《板》的写作年代是要略早于《荡》的。因此,在《板》的年代,大臣还对君王进行耐心的说教,希望君王能够悔过悛改;而到了《荡》的年代,人们进一步感到失落望,原来的谆谆劝告,也就成了“曾是彊御?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式的夺命连环问,以及“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的连珠炮式斥责。
这种类似于“当面反复负责劝告/指着鼻子骂持续串”的直接怨刺的办法,正是“直抒胸臆派”的范例写法。
或许你还记得,之前咱们提到了一个“比喻象征派“的流派。事实上,“比喻象征/直抒胸臆”的名字虽然算是我根据写作手腕来自己起的,但这种分类办法,实则对应了《诗经》“六义”之三——赋、比、兴。
所谓“比喻象征”一派,常常利用“比”——比喻,以及“兴”——起兴“来表达感情;而”直抒胸臆“一派,则善用”赋”——铺排的手腕,来“直陈”自己的感情。两者风格不同,自然也没有什么利害之分:善用“比”“兴”的诗歌,每每讽刺得入木三分;而善用“赋”的诗歌,每每抒发得淋漓尽致。
那么——有没有能够那样一首诗,能够集“比喻象征”与“直抒胸臆”两派之长,结合“赋”“比”“兴”三种手腕,来达到一种极致的骂人效果呢?
我的答案是:有。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认识一下这首,官方认证的怨刺诗中的真正大佬:
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彼谮人者,亦已大甚!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谮人者,谁适与谋。
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慎尔言也,谓尔不信。
捷捷幡幡,谋欲谮言。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骄人好好,劳人草草。苍天苍天,视彼骄人,矜此劳人。
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杨园之道,猗于亩丘。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
——《诗经·小雅·巷伯》
这首《巷伯》的地位是什么样的呢?《礼记》里这样说道:“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把《巷伯》提高到了“恶恶”,也便是“厌恶恶人”的诗歌的标杆地位。
这首诗歌和《青蝇》有点相似,同样也是斥责造谣之人,但其手腕则显得比《青蝇》繁复得多。在开篇时,用贝壳花纹和南箕星来比喻造谣者的甜言蜜语,可以说是相称精到;而在后文,则以持续串的“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通过表达自己想要把恶人扔给豺狼、老虎、极北、上天,层层递进,对制造谣言的“谮人”的痛恨,也就溢于言表了。
这种结合了“赋”“比”“兴”于一身的诗歌,骂得可以说是畅快淋漓,也给读者以一种极佳的审美体验。
而《诗经》中这种怨刺的传统,也在历史的长河中被一代又一代继续。每当政治阴暗、民不聊生之时,就会有人推开《诗经》这扇厚重的大门,用手中的火柴,再次点亮针砭时弊的炬火,当仁不让地踏上这条注定艰辛的道路。
这条路上,有“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王粲,有“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的杜甫,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张养浩,也有“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宅”的鲁迅师长西席。
这些声音,虽然在当时或许显得有些刺耳,或许也并没有很大的声音。但一声警钟,或许就足以将沉睡许久之人惊醒;一根火柴,或许已经足以划破漆黑的漫漫永夜。
这,或许便是怨刺诗文不断传承的意义之一。
-作者-
老王,清华大学在读本科生,年十九,喜古文,迩诗词。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大吃一顿。故自傲人生二百斤,会当撰文三千笔。因此浅题四五诗词,闲作六七文章,若承蒙不弃,愿与八九好友共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