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天歌》的根本实在便是《史记 天官书》中对天空恒星的划分,其将天空划分为五大部分,分别是中宫和东南西北宫。而中宫便是拱极星区,与三垣中的紫薇垣基本同等,而四方则分别对应了7个星宿。
在东汉天文学家张衡的《灵宪》中,已初显这种分布,"一居中心,谓之北斗。动变挺占,实司王命。四布于方,为二十八宿……紫宫为黄极之居,太微为五帝之廷。名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座。苍龙连蜷于左,白虎猛据于右,朱雀奋翼于前,灵龟圈首于后,黄神轩辕于中。"这里北斗与拱极星宿相同,而紫宫,太微,天市的名称已经涌现,四象也与28宿相对应。
四象图
在《晋书 天文志》和《隋书 天文志》中,均有与之相类似的天区划分,这也解释了三垣二十八宿这种划分办法的一个逐步蜕变的过程。但是,《步天歌》与这些划分最明显的差别便是对三垣的划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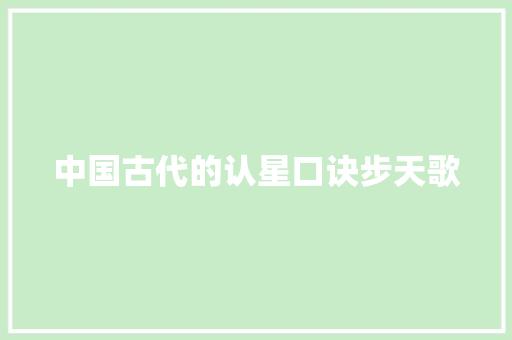
所谓的垣指的便是墙,也有宫墙的含义,人们对付拱极星区的不雅观测中创造天空中的一些星排列比较整洁,并且呈两个半圆弧的形状拱卫着北天极,就像帝王居住的宫廷禁地的围墙,因此这些星被称为垣。用紫宫垣或者紫薇垣来称呼,其包围的天区则视为最尊贵的地方。
紫微垣星图
北极五星,勾陈六星,皆在紫宫中。北极,北辰最尊者也,其纽星,天之枢也……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勾陈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大帝上九星曰华盖……华盖下五星曰五帝内坐,设叙顺帝所居也。
看这段描述,俨然是人间帝王统治在天空的再现。对付两道围墙的星区,则分别称为太微垣和天市垣,这里的星官也是非同一般。
如太微垣中"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坐也,十二诸侯府也。其外藩,九卿也。……黄帝坐在太微中,含枢纽之神也。"而在天市垣中,"帝坐一星在天市中候星西,天庭也"虽然比太微垣稍差了些,但也有宗正,宗人等统治机构的名称,其余还有各诸侯国的名称,这些也表明了天市垣同样的非同一般。
三垣二十八宿
三垣的涌现并未出于天文学本身的须要,而是受到占星术的影响,这与28宿作为恒星区域的划分是有所不同的。因此,相对付《史记 天官书》中对星宿的描述,也是有着一定的发展的。
根据现有文献资料可知,《步天歌》对恒星位置的描述是最早按照三垣二十八宿这样一个体系来进行的,目前我们已经创造的版本有10个,通过对这些版本的订正,我们得到了一个相对准确的校订版的《步天歌》。校订版的《步天歌》分为7个部分,前4部分是按照28宿的顺序阐述了相应各个星官的位置情形,而后3部分则对应了三垣。
古代星图
《步天歌》中的星宿图利用不同颜色表组星宿,因此颜色来区分该星宿的来源,个中赤色星官源自石氏,玄色星官源自甘氏,黄色星官源自巫咸氏,别的还有未注颜色的星官。这解释三垣二十八宿的体系是从三家星官脱胎而出的,但是已经逐渐摆脱了传统束缚,相互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
其余,《步天歌》还对星官的排列形状和与其他星官的相对位置进行了描述,这样更便于在天空中找到,有的还对亮度进行相识释。比如"大角一星直上明""天策,天溷与外屏,一十五星皆不明",这些描述都有助于认星。对付一些排列和形状比较繁芜的星官,描述还会更加详细。例如对翼宿的描述"二十二星太难识,上五下五横着行,中央六个宛如彷佛张,更有六星在何许,三三相连张畔附,必若不能分处所,更请向前看记取……"这个描述分别将高下和中间的各星进行描述,将22颗星分解阐述,解释对恒星的不雅观察非常的仔细。
古代星图
《步天歌》的后三部分对三垣的阐述也是采纳上,中,下的顺序,将太微垣、紫微垣、天市垣分别称为上垣、中垣、下垣,按照从东向西的次序描述。以紫微垣作为根本,太微垣在其西南,天市垣在其东南。《步天歌》中还将三垣称作上元,中元,下元,元有"为首""第一"的含义,这与三垣的尊贵地位符合,同时与垣同音。至于详细各星官的描述则与前面四部分类似。
总的来说,《步天歌》是一首普通的认星歌词,南宋学者郑樵在《通志 天文略》中认为通过图文对照即能得到形象的观点,又能避免在流传中涌现的缺点,而成为认识星空的空想"自学教材"。
步天歌片段
《步天歌》的主要还在于其所运用的恒星分区体系相比拟较前辈,与我国古代独占的赤道天文坐标紧密结合在一起,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按照28宿在东西方向上所霸占的范围来划分星区,与赤道天文坐标系中"入某宿"的观点基本符合,而紫微垣又突出了北天极的浸染,这样总体看来以北天极和天赤道为基准的特色就十分明显了。
步天歌片段
当然,三垣28宿的体系在相称大的程度上还是迎合了占星术的需求,中国古代存在一种将天空恒星的区域与地面行政区域相对应的做法,这便是所谓的"分野"。在《史记 天官书》中就有"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从来久矣。""角亢氐,兖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28宿对应了12州。在《晋书 天文志上》中又列出了28宿与各州郡之间对应的细节,三垣区域的星官与帝王统治也进行了对应。因此,三垣28宿内的各个星官都在占星术中具有分外的意义,可以根据不同星区的天象来显示与其对应的地面上的区域或者事物的凶吉征兆,这也正是统治者非常重视的。因此,这种划分体系也就得以延续,一贯贯穿封建社会。
步天歌片段
《步天歌》中涉及的星数,根据郑樵在《通志 天文略》中的统计,石申记载的星官138,计810星,巫咸记载的星官44,计144星,干德记载的星官118,计511星,总计星官300,计1465星。而根据潘鼐在《中国恒星不雅观测史》中的统计,除石申星官的数量有较大出入外,其他基本符合。而石氏星官中多出的17个星官可能是由其他星官拆分出来或者重复所致。
《步天歌》是在早期的三家星官根本上发展起来的,并将其完全成一个涵盖北半球及部分南半球星空的星座体系,结合占星术和诗歌的特点,成为古代人们认星的一个主要工具。在我国古代天文史上起到了非常主要的浸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