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暮,闭上了眼》是个人的第三部诗集。和前两部一样,依旧是一年来‘在地铁中体验天下的不安,在地下不雅观照地上的飘浮’的产物。”李瑾在《诗歌是自由的吗》一文中谈到。
“他一方面将当代诗与各种文学文体结合起来,创造了戏剧体、日记体、书信体、年谱体、回顾录体等样式,拓展了当代诗叙事和抒怀的空间,另一方面借鉴经史子集、古典小说和散文等经典和名篇,将古典资源整合成为新诗的内在元素和外在修辞。须要把稳的是,李瑾创作中的‘古典’‘日常’都是一种母体,他真正表达的是时期、当下及其在内心深处留下的深刻烙印。尤要指出的是,李瑾作为一个抒怀主义者,谢绝用晦涩的词句、玄奥的意象,他在营造意境,以情动人的同时,惯于熬炼‘问题意识’,展开‘生命之问’。”作家、墨客安歌指出。
李瑾是山东沂南人,历史学博士。作品常揭橥于《公民文学》《诗刊》《公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并入选多种选本。曾获东丽文学大奖、李杜诗歌奖、中国诗歌网2018年十佳墨客、华西都邑报2018十佳墨客等奖项,出版有诗歌集《人间帖》《孤岛》,故事集《地衣——李村落寻人缘由》,评论集《纸别裁》,儿童文学作品《没有胳肢窝可怎么生活啊》,学术作品《未见君子——论语释义》等。
(附李瑾文章《诗歌是自由的吗》,安歌文章《在日常中创造诗意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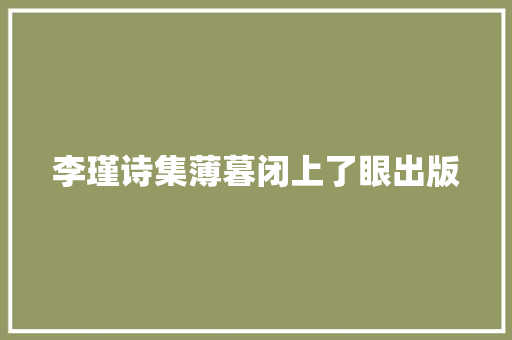
诗歌是自由的吗
文丨李瑾
“新诗是自由的。”因这句话供应了墨客所须要的最主要的精神图谱,业已成为收留他们灵魂的乌托邦。不过,当新诗被视为彼岸时,鲜少有谁磋商该“格言”指涉的究竟是什么,以及墨客在何层面上利用“自由”这个充满激情和疑问的语词。
如果荷尔德林所说“如果没有诗,我说,他们乃至永久不会成为一个哲学的民族”可以成立,那么,新诗无疑是墨客确立自我身份的尺度。当评论辩论起源意义上的新诗时,一定是在抛弃古诗/传统——这种讲究格律的措辞集束,充满了压抑、束缚,在表达上捆绑了墨客的身体。而新诗则是旷达澎湃的、可吞日月的,墨客吟咏“我是一只天狗”之际,其和新诗同体了,他们统为自由的象征。
检视中原文明的进程即可通达,如果古诗没有批驳性,就不会造诣诗经和杜甫;没有人的自我创造,就不会有离骚和李白。当我们看到古诗始终处在道德的玄学的历史语境里——这是一种自我意志认识的偏见——是否复苏地看到新诗也一贯在“符号化”的过程中?
代价/精神层面指摘古诗不自由站不住脚,在形式上的否定也难圆其说。常日意义上,我们说古诗是讲究格律的,严格讲求起来,如此界定有失落公允。就古诗而言,其始终在格律体和自由体的贯通中求得成长,纵然五律、七律,五绝、七绝,也讲究一、三、五不论和各种拗救及邻韵通押和多式音节。尤要值得把稳的是,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伟大墨客随处颂扬的佳作,大都因此古风和乐府为主的自由体。保罗·策兰指出:“诗歌不是没有韶光性,诚然,它哀求成为永恒,它探求,它穿过并把握时期——是穿过,而不是跳过。”这些时期精神的高歌者,始终在保持思想、艺术上的敬畏的同时,追求着生命的体验而非音字词的抠索:墨客从来就不是诗工或诗奴。当然,将新诗和自由勾联起来首先指的是形体的改造。这里,不妨引用胡适的言说,他在《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中指出:“我常说,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哀求措辞笔墨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欧洲三百年前各国国语的文学起来代替拉丁文学时,是措辞笔墨的大解放;十八十九世纪法国嚣俄、英国华次活(Wordsworth)等人所提倡的文学改革,是诗的措辞笔墨的解放;近几十年来泰西诗界的革命,是措辞笔墨和文体的解放。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哀求措辞笔墨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措辞是口语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主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冲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桎梏。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不过,这位日后转为古诗创作的启蒙巨头也曾反思道:“师长西席论吾所作口语诗,以为‘未能脱尽文言窠臼’。此等诤言,最不易得。吾于去年夏秋初作口语诗之时,实力屏文言,不杂一字。……其后忽变易宗旨,以为文言中有许多字尽可输入口语诗中。故今年所作诗词每每不避文言。”就新诗和古诗的纠葛,梁宗岱的总结最为彻底:“和历史上的统统文艺运动一样,我们新诗底提倡者把这运动看作一种革命,便是说,一种玉石俱焚的毁坏,一种解体。以是新诗的发动和当时的理论或口号,——所谓‘培植明了的普通的社会文学’,所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不仅是反旧诗的,切实其实是反诗的;不仅是对付旧诗和旧诗体的流弊之洗刷和拔除,切实其实是把统统纯粹永久的诗的真元通盘误解与抹煞了。”
只想再次强调如下论点,诗歌是自由的,自古而今皆然。“形式”问题并非诗歌的终极问题,退一步说,纵然新诗较古诗自由,也是指完备放弃了格律。五四往后,很多墨客试图将古诗、新诗嫁接起来,实现诗歌可以朗朗上口的“新形式主义”,终极归于徒然,毕竟新诗是西学东进的产物。当新诗打破了古诗所谓的形式主义,无论怎么传播,都没法将墨客个体的灵魂转换为大众的灵魂。这就导致了一个悖论,新诗在得到大众化、娱乐化之后越来越小圈子化而无法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她丢失了中央位置。我们可以考验一下,当代墨客都能背诵几首古诗,但谁能背诵自己乃至别人的作品?新诗已成为私人的笔墨游戏,虽然写作者将其视为精神的。
由此造成的困境是,新歌的评判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今,会写三五句分行,便是墨客;报刊上揭橥几首,便是大师。分行成为新诗的唯一规定性,大家怀有对新诗的一套认知、理解,且洋洋得意,并以自由为名谢绝评判。正基于此,墨客对“诗歌是自由的”的代价追求,经由唯形式论的误会性消解后,沦为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自由。
姑且打住。《薄暮,闭上了眼》是个人的第三部诗集。和前两部一样,依旧是一年来“在地铁中体验天下的不安,在地下不雅观照地上的飘浮”的产物。诗歌能够揭橥,诗集能够出版,得益于诸多亲朋师友的关心,感激之情铭记于心,名号不再逐一从俗具出。
在日常中创造诗意之美
文丨安歌
新诗百年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迎来了一轮轮对诗歌这门“最高文学造诣”“措辞的最高造诣”的检视与反思,究竟“什么是诗歌”“诗歌为什么”成为当下文坛关注的焦点。但不管怎么磋商,诗歌对大众而言,“替中国文化保持了圣洁的思想”(林语堂语);对个人而言,“永久是个人对自我的追问、对天下的不雅观察”(谢有顺语)。所谓“感其况而述其心,发乎情而施乎艺也”,诗歌作为对生活的一种诗意表现和书写,是探索人生的代价一种利器、不雅观照社会的一壁镜子。《薄暮,闭上了眼》是墨客李瑾面对当下、立足生活、扎根日常精心创作的作品,这部诗集的出版,进一步表明通过措辞建立起来的精神天下,是我们抒发生命感悟、生活感怀和人生感想熏染的诗意栖居之所。
李瑾的诗歌创作,一贯具有一种富于人文气息和个性特色的“新意识”。这种“新意识”表现为,将一些看似平常的事物授予诗学意义,通过日常之“物”进行对自我和天下的省思,进而建立起“自古典要诗艺、自日常要诗意”的诗学典范。林语堂曾说:“中国人特性的写作天才,长于约言、暗示、遐想、凝练和专注。”李瑾在诗歌实践中,非常看重从眼下和琐细处创造和提炼朴素之美,从而显现出一种爱好生活和享受生命的艺术家风姿。李瑾作品的“朴素之美”包涵三个维度。
一是时期的。我们都知道,诗歌是时期提高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期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期的风气,也便是说,诗歌是人类思维与社会现实领悟而生的最直接的精神产物。能否贯彻“诗歌是生活的表现”这一命题,不仅是现实主义所倡导的准则和方向,也是一个墨客“写什么”“怎么写”的创作态度问题。通过诗歌参与和参与现实,直面时期,是李瑾的一大特色。他笔下所历经由生命内核的隐秘部分,经由墨客个体的精神承担,实现了与社会和时期有效沟通、持续同步。而墨客也由于关注人类的生存和精神的发展,在时期这个伟大的系统中“创造”了自己,找到了自己的代价坐标。
二是生活的。从本源意义上说,生活是诗歌的唯一源泉。不过,只管个人无时无刻不处于宏伟的历史潮流之中,但正在进行着的生活才是人最直接、最根本的“环境”,“日日新”的山河之美、自然之魅包括锅碗瓢盆都给墨客带来新的灵感和冲击,引发新的想象和空想,催生新的生活办法和不雅观念代价。在李瑾的诗歌中,环球化、网络化、智能化这些典范性的生活之变和在“我”之外却又与个人息息相关的青山绿水、安居乐业都是描摹和抒发的工具,《购物城记事》《街边一景》《西山一日》《画师》等作品都带有浓郁的生活体温,散发着湿润的“泥土”的气息。李瑾被称为地铁墨客,他的作品都是利用高下班乘坐地铁的韶光完成的,这样的“在场性”“即兴式”写作具有光鲜的动感,可以说很好地表示了他自己所说的“在地铁中体验天下的不安,在地下不雅观照地上的飘浮”的代价追求。由是,诗歌在李瑾内心深处和生活密切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或日用气质,从而让诗歌真正具有了一种“接地气”的精神品质。
三是自然的。如果说中国诗歌和西方诗歌有共通的地方,一言以蔽之便是“自然主义传统”。在一篇文章中,李瑾曾说,当代墨客心目中的自然某种意义上差异于陶渊明式的寄情自然,即仅仅将自然和“情绪性”书写等同起来,而是更方向于一种“思想性”书写,自然不是墨客咏叹的工具和目的,而是通过它将个人的思考引向宇宙层面,进而创造出自身的时空天下:自然退居第三位,个人位居第二位,而生命、韶光和命运则成为主体和主题。他是这么说的,在详细实践中也是这么做的。李瑾是一个标准的自然墨客,他的绝大多数诗歌都是关于自然的吟诵并终极落实到对生命的诘问上,比如名篇《致母书》:“炊烟安静,几棵树扶住了微风,院子里/光影薄弱,却能让落日转头/人间那么老/我怎么舍得伤心。站在房檐下,绿色的/星辰湿漉漉的,它比河流匆忙,更懂得/一个人的暮色能够留住多少归鸟/……米饭来了/蔬菜来了,白发也来了/但我甘心躲进生活中尝一尝受饿的滋味/母亲面前,我谢绝和她身上的韶光和解。”诗中,自然的、环境的诸事诸物和对母亲的爱结合在了一起,自然让个人与天下建立起了“亲缘关系”,基于此,生命、身心与自然实现了同质性统一。
总结而言,李瑾“自古典要诗艺、自日常要诗意”的典范性在于,他一方面将当代诗与各种文学文体结合起来,创造了戏剧体、日记体、书信体、年谱体、回顾录体等样式,拓展了当代诗叙事和抒怀的空间,另一方面借鉴经史子集、古典小说和散文等经典和名篇,将古典资源整合成为新诗的内在元素和外在修辞。须要把稳的是,李瑾创作中的“古典”“日常”都是一种母体,他真正表达的是时期、当下及其在内心深处留下的深刻烙印。尤要指出的是,李瑾作为一个抒怀主义者,谢绝用晦涩的词句、玄奥的意象,他在营造意境,以情动人的同时,惯于熬炼“问题意识”,展开“生命之问”。
(光明日报全媒体李晋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