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自题金山画像》
苏轼仕宦生平,事情过的地方实在远不止这三个。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北至定州、密州,南至惠州、儋州。眉州是苏轼的故乡,杭州是苏轼两次担当地方官的地方,等同于苏轼的第二故乡。
苏轼初次贬谪之后来到黄州,黄州的主要性无需多言,那里虽然是苏轼人生的低谷,却造诣了他诗文艺术上井喷式的发展;儋州、惠州是苏轼末了的谪居之地,也造诣了他文学上的高峰。有人曾绘制了一张苏轼仕宦生涯的行迹分布图,从中就可以看到他走过的地方。
苏轼行迹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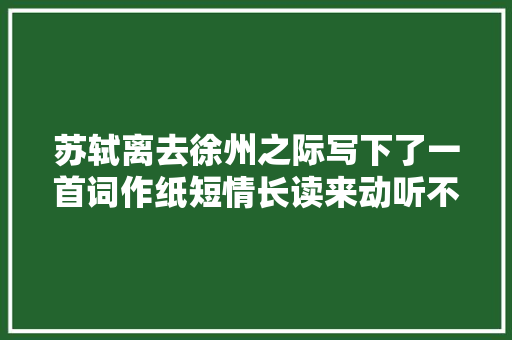
在苏轼事情过的许多地方中,徐州也是个中之一。苏轼在徐州的任职韶光虽然不长,只有两年旁边,但他在徐州的事情岗位上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他深入田间一线,稽核农桑,发展生产。
苏轼有一套管理徐州的方略。他曾蓑衣草鞋、舍家忘身,和徐州公民一起在雨季抗洪抢险,他组织有方,且常常奋击在第一线,与徐州公民结下了深厚的情意。
徐州
当徐州天旱影响农业生产的时候,作为一州之长的苏轼心坎不安。贰心系百姓生活,亲自前往石潭为民求雨。甘霖普降之后,徐州的旱情得到了缓解,人们带着雨水到来的激情亲切投入到热火朝天的田间耕种中。
苏轼又按照民间风尚,前往城外的石潭村落举行谢雨仪式。他将谢雨沿途见闻和村落庄体验融进笔端,持续写了五首反响村落庄生活的词作《浣溪沙》。
在徐州期间的苏轼,不仅事情兢兢业业,恪尽职守,而且他的诗词风格也为之一变。尤其是词作,苏轼还考试测验以诗入词,他不但对付多种平韵的小令、中调和长调的利用已得心应手,笔下不乏可歌可传的佳构,而且对付仄韵的中、长调的利用出神入化,取得了很高的艺术造诣。
苏轼在徐州的词作,可以说无一不是因人、因事、因景而作。作为涌如今作品中的抒怀主人公,词人有时是乡情刻骨铭心,却无奈流落天涯的游子,如他在《临江仙》中写的“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有时他是在功名与退隐间进退取舍,与苏辙惺惺相惜的兄长,如他在《水调歌头》中写的“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
有时他是关心民情、民平易近的一州之长,如他在《浣溪沙》中写的“问言豆叶几时黄”;有时他是与一方百姓深情惜别的离职官员,如他在《江城子》中写的“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
徐州风光
徐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苏轼来到徐州后,他曾对这里的山川河流、风尚民情,作过详细稽核。苏轼热爱徐州,热爱徐州的百姓,流连徐州的山水人情,他用真情赞颂徐州的山水风景与人物风情。
白发老翁、顽皮孩童、采桑女子、络丝姑娘以及人们的生活办法、节日习俗乃至各种农作物,都成了苏轼诗词取材的工具,也成为了他寄托思念,抒发情绪的素材。苏轼在徐州的词作不只题材广泛,而且名句迭出,如: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阳关曲》
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水调歌头》
一别苏州已四年。秋风南浦送归船。——《浣溪沙》
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临江仙》
落日有情还照坐,山青一点横云破。——《蝶恋花》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宅心眼。——《永遇乐》
在徐州任职的两年光阴里,苏轼一首首纸短情长的词作,不仅是对徐州的赞颂,更是对徐州的流连,他的诗词,被徐州公民广为传诵。
以是当苏轼调离徐州时,人们舍不得他离开这里,人们把他送了一程又一程,苏轼也与徐州公民依依惜别。
面对送别的徐州百姓,那种依依不舍的情愫交织在词民气头,于是他写下了一首《江城子》的词作。
也可以说,这首词作为苏轼的徐州之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只不过这是一个充满温情的句号,也是一个意蕴深长的句号。
正由于苏轼对徐州那样的依依不舍,才会写出这样一片纯情的告别词来。在《江城子》一词中,苏轼这样写道:
天涯流落思无穷!
既相逢,却匆匆。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
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顾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苏轼画像
由于苏轼从徐州调任到湖州,这本来是正常的事情调动,但苏轼眷恋徐州这片地皮,眷恋徐州激情亲切的百姓,依依不舍之情长短分分外强烈的。
这首词便是苏轼离去徐州为他送行的父老乡亲时写下的,以是词作开篇三句“天涯流落思无穷!
既相逢,却匆匆”,便是苏轼发自内心的一声感慨。这三句大意是说:徐州一别,又要到人生地不熟的湖州去,面对送别的情景,叫人感慨不已。愁烦的心绪无穷无尽,在徐州虽然只有短短两年韶光,但光阴如白驹过隙,须臾即逝,还没来得及与你们好好相聚,本日却又要分别。
这两句也蕴含着无尽的伤离去的情愫。试想一下,苏轼离开故乡,离开京城的朋友,远道而来,来到徐州这片陌生的地皮上,在与徐州公民相处过程中,他们同甘共苦,抗洪抢险,预防旱灾,共建美好家园。在一点一滴的光阴中,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徐州公民也深爱着这位年轻的文章诗词俱风骚的父母官,可想而知,徐州的这一别,对苏轼来说,是有多么的不舍,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徐州公民对苏轼的不舍之情。
这三句也蕴含着苏轼的出生之感。苏轼自从考中科举,参加事情以来,一贯在阔别故乡和京城的地方任职,很少有机会回老家省亲,也很少有机会与京城的老师和朋友相聚。
以是苏轼一贯将自己认为是一个飘零天涯的人,在陌生的地方去,没有归属感的觉得在他的心中就愈加显得强烈。
他在杭州任职时就发出过“天涯同是伤沉沦腐化”的感慨,在徐州他也发出过“天涯倦客”的喟叹。他在徐州仅两年,又调往湖州,步履一直,这就更增加了他对流落天涯的无尽感慨。
苏轼须要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可是离开徐州去湖州,这种觉得会随着韶光与足迹的前行而加倍微弱,这也是苏轼发出感慨的缘故原由。
“既相逢,却匆匆”两句,续写苏轼与徐州公民的交往,相知到离去。苏轼来到徐州时已年届四十,他与徐州公民相逢既晚,但相逢的时日短暂,离去又是这样的匆匆!
苏轼离去时的心情是繁芜的,有曾经相逢的喜悦,也有对骤然分别的痛惜,这两种抵牾的情绪交织在一起。词人是欲言不能、而又不吐烦懑,以是他以凌厉、沉重的笔势与口吻,和盘托出这句感情激越的话之后,心情彷佛沉着了一些。
然后他才开始回到对徐州的点滴影象中,回到徐州公民送别他的场景中。就像是打开一本泛黄的相册,又彷佛是从相册中挑出一张张记载着流光的照片。
“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写他永久不能忘却离开徐州时依依惜别的动人一幕。但是在描写送别的这一幕时,词人并没有截取徐州百姓的与同事们的送别的场面,而只是从这送别的行人中截取了一个很特殊的镜头:
那是几位也前来送别苏轼的红粉佳人,她们是在送别宴会上演唱歌曲的女子,苏轼在徐州的一首首歌词也是由她们传唱出去的,她们既是身兼歌舞的才艺女子,也是苏轼的粉丝。苏轼的离去,对她们来说也是一件很伤心的事情。
“和泪折残红”,这一句形神兼备的描述,将词人的情绪细腻地抒发了出来。“残红”表明这是暮春时节,离去在落花时节,这让本来就由于伤春而惆怅的心绪又增长了一份惆怅。
睹物更添伤怀,这让送别的情思与气氛在空气中弥漫开来,词人辗转不忍拜别,各类离愁与烦一韶光涌上词人的心头绪,都融进“和泪折残红”这一句情与景俱在的句子里。
接下来的“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大意是说:这些女孩子们梨花带雨地含泪送别词人。假使问这美好的春天还剩多少,纵然春意尚在,又能和谁一同欣赏这美景呢?
女孩子们的眼泪和这暮春时节的落红两相照料,在词人眼中,更绝动人。“景为情而设,词为情而作”,苏轼这饱含情绪的唯美动人的笔墨,将离去的情景渲染得非常伤感。
清末词学评论家况周颐曾说:“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反不雅观苏轼描写离去场景的这几句词作,情真意浓,真情流露,也将他对徐州景致人情的留恋之情抒发地淋漓尽致。
词人由面前的落红而遐想到更为广阔的空间和韶光,那便是春天的脚步已经附近尾声。纵使春光仍在,而此刻词人却不得不离开徐州,踏上前往湖州的道路。自己步履一直,那么春光也是无法挽留他的,又有谁会与他同赏呢?
在前往湖州的道路上,无人问我粥可温,无人与我立薄暮。词人一步三转头,笔触一唱三感叹,婉转而动人的曲调抒发了词民气坎深深的情绪。苏轼通过描写离开徐州后孤单的身影,以不同的笔墨相同的感情,表达出对徐州这片地皮的无比眷恋。
如果说这首词的上片侧重于情绪的抒发的话,那么下片则是侧重于景物的渲染,但又不仅仅是纯挚的景物描写,而是借景抒怀,折旧与上片中的情绪很好地关联在一起。
“隋堤三月水溶溶”,是写词人前往湖州路途上的景致。苏轼是由汴河水路离开徐州的。汴河是隋代开通的一条水路,西入黄河,南达江淮,在北宋仍是沟通京师与江淮的主要水道。
人们沿着汴河筑起长长的堤岸,还在堤岸上栽种了一排排的柳树,这条堤岸也被后世称为“隋堤”。每到暮春三月,绿水荡漾,柳枝依依,绿水倒映柳枝,柔情似水,这时的隋堤游人如织,美不胜收。
接下来的“背归鸿,去吴中”两句,大意是说此时鸿雁北归,我却要到飞鸿都已离开的湖州去。这两句写的也是词人途中的见闻。春光妖冶,鸿雁北归,而词人离开徐州,到湖州去,去湖州的方向是南下,这与大雁前行的方向相反。
苏轼显然是把徐州当成了他的故乡,而自叹不如归鸿。苏轼内心是不愿意离开徐州的,到到湖州市事情须要,以是词人还是带着无限的留恋与不舍离开了徐州。他在途中频频停下来,望着身后的徐州大地,词人的足迹渐行渐远,直至徐州在他的视线中渐次模糊。
在无数次的回顾中,只见那清澈的泗水由西北而东南向着淮水缓缓流去。看到泗水,又触发了词民气坎本意逐渐平息的波澜。看到泗水,又让词人想到徐州,由于泗水这条河正是流经徐州的,这正是触景生情。
词作以“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三句扫尾,大意是谁:想要让泗水寄去相思的点点泪水泪,奈何它流不到湖州去呀!
这三句即景抒怀,读来让人冲动不已。在词人痛彻心扉的叫嚣声中,是对徐州无尽的流连。在词人看来,徐州一别,要想再回到这个地方,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
纵然自己想回来,那也是一厢宁愿的事情,路途的迢遥暂且不说,在新的地方,还有新的事情等着他,他也是抽不出韶光再回徐州的。
既然在此回到徐州的希冀很渺茫,以是词人打算让这暮春三月清清的泗水把他的相思泪水寄往徐州,奈何泗水偏倾向东流去,却不会流经湖州。
泗水东流,一片相思之情本想请托流水,可是流水难寄词人的一片相思,这叫人情何以堪!
词作就在这样沉痛与惆怅的旋律中曲终阕尽。回顾苏轼的这首词,不管是词人在情绪的抒发上,还是在景致的渲染上,都是景中生情,情景交融,情与景是如此的真切,如此的情真意切,正应了一句话“统统景语皆情语”。
说到情真,是由于苏轼对徐州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是真实的,以是词人对描写的景致自然而然,不矫揉造作,不堆砌辞藻。也正是由于词人对徐州有着感同身受的热爱,以是情绪的流露也是自然而然的,不忸怩作态,落落大方。
纸短情长,在苏轼的这首徐州告别词中,他要告别的,是全体徐州,这包括了徐州的一山一水,徐州的风土人情,徐州的同事百姓,还有他在徐州两年韶光里洒下的激情亲切和汗水。以是词中所流露的感情是朴拙动听的,也是弥足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