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长云暗雪山,
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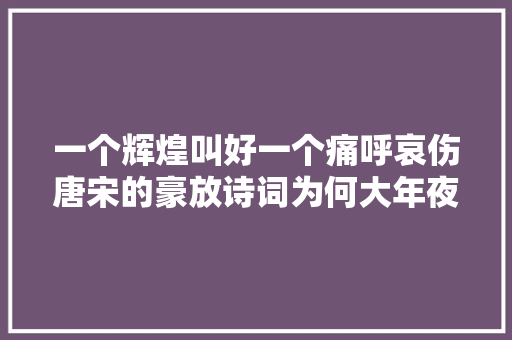
宋代的豪放词,写出的是词人无尽的凄凉,无法再实现的年夜志,无法再期待的未来。比如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疆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唐宋两首词作,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唐宋两代的豪放作品相较,不论是描述情境还是内蕴感情,都有很大不同:唐作豪迈之下蕴含的是直欲透纸而出的昂扬进取、奋发向上的年夜志壮志;而宋作豪迈之下难掩的是难以诉尽的壮志难酬,无力回天的悲壮、苍凉之情。这种不同不仅只存在于一两个人,而是贯穿了险些所有两代同期间作品,而这,肯定是有其内在缘故原由与联系的。
产生唐宋两代不同豪放之情的缘故原由,无疑是繁芜的,这个中最主要的,起到了最决定性成分的还是唐宋两代不同的政治、军工作况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即所谓不同的时期造就了不同的作品。
唐代可以说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空前繁荣期,这种繁荣可以说是涉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政治上,唐朝是“天朝上国”,各个国家的使节争相前来,所谓“万国来朝”;军事上,唐王朝的几次对外用兵,除了对高句丽之外,险些都取得了胜利,实力强大,开疆拓土。国家的强大,极大的引发了唐代墨客的进取心,全体国家国民性中的尚武精神,又使他们拥有了热血的军事英雄主义思想,受时期氛围的影响,一次次的胜利,一次次的提高,大国之下的边塞墨客是斗志昂扬的,他们的作品亦染上了这个时期的色彩,如初生朝阳,光芒万丈。
而宋朝,虽然宋朝也称为是我们古代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但宋比唐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宋代的壮盛是壮盛在经济、文化乃至科技,但却绝不壮盛在政治和军事,这两项,宋代可以说难望唐时项背。宋朝自建立伊始,就置于四围少数民族政权的巨大军事压力之下,再由于自身“重文抑武”的国策,其对外战役基本没有胜利过,对外一贯采取的是带有屈辱色彩的“进贡”策略,在外交上也处于下风,可以说,宋朝举国高下弥漫的都是当心翼翼,不知何时游牧民族的铁蹄就又会叩响边关的感情,宋代文人在全体生理底色上就不会有唐代墨客所拥有的那种巨大的底气。再到了北宋灭亡,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无力收复故土,全体宋代国民的的整体心气,就更是弱了下去,这种感情反响到宋代文人的诗词作品上,我们亦可以明显的看到这种无可奈何,这种在个人豪情之下的时期的悲怆与苍凉。
此外,作者个人的境遇也大不同。
唐代豪情抖擞写作边塞诗的墨客,如边塞诗造诣较高的岑参、王翰、王昌龄大多是从过军或者在边塞游历过,个中仕途最成功的高适,更是因战功封侯。他们这一群体,参与或见证了勇往直前的大国气候,这使他们在全体生理上是非常强大的,以是就算是暂时自身没有造诣,经历坎坷,但他们置身在沙场上时,周围充斥的是无畏的报国情怀,他们心里充满了希望,他们知道身后的国家是强大的,是抖擞着巨大的生命力的,这给予了边塞墨客最大的生理安慰。在这种支撑之下,这些墨客,他们笔下的边塞诗作中的心气就不会堕,他们的作品说眼下是奋发进取,无限可能,看未来是充满希望,一片光明,这种边塞墨客整体感情中的年夜方豪迈,支撑起了边塞诗情绪最深处的亮色。
宋代的文人也从军,像笔者前文提到的陆游和辛弃疾,都亲自上过抗击金兵的前哨,有过立时取功名的激情岁月,但是他们所参加的战役,过程是惨烈的,结局是失落败的。他们在战役中,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无法看到自己梦寐以求的结果,以是在他们的笔下,几次再三想到过去,想到军营,这种过往岁月的豪情,但一映照现今的处境,只能是更添凄凉,再多的豪情万丈,现在看来都只是梦一场,因此他们的诗词有豪情有年夜志,但是到末了,在冰冷的现实面前,都看不到未来,都失落去了依托,都只能转为一声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