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已经闲居三年了,岁月蹉跎,贰心里有点焦急。从二十岁起,陶渊明便开始了游宦生涯。“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他肚量胸襟壮志,放下锄头拿起长剑,仗剑江湖走天涯,在一些政府部门担当过低级官吏,干得还不错,生活也有改进,领导也很赏识,“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管吃管住还有人为,干了一段日子,就有了一些积蓄。
但是作吏并非正途,干一辈子也当不了官,因此他辞职回家了。“恐此为名计,息驾归闲居”。这些基层事情混不出“名”来,没有名就走不上正途,当不了大官,实现不了空想。因此他带着一些积蓄和所在州府领导对他的事情评价以及当地绅士对他的推举语回到了家乡。毋庸赘言的是,这些评价无疑是正面的。这一年他二十二岁。
二十五岁,他把家从乡下的“园田居”搬到市区。之以是搬家,是为了更能靠近权力中央,为自己下一步出仕做准备。经由几年运作,功夫不负苦心人,二十九岁,起为江州祭酒。刺史王凝之,乃王羲之四子,妻子谢道韫。王凝之是个温文扬洒的上层贵族,信奉五斗米道,写得一手好字。
祭酒分管一州军事、治安、仓储、民事、水利、军需等事务。王凝之不理庶务,全体江州的军政重担就压到陶渊明一人身上。可惜陶渊明没有处理细务的能力,繁重的事情让他喘不过气来,没干几天就辞职回家了。“少日,自解归”。辞职缘故原由很大略:“不堪吏职”。王凝之没有放弃他,又征辟他作州主簿,而且持续征辟了三次,可是陶渊明都没有出山。由于主簿杂事大概多,每天文案操心,还要迎来送往。毋庸讳言的是,这些并非陶渊明强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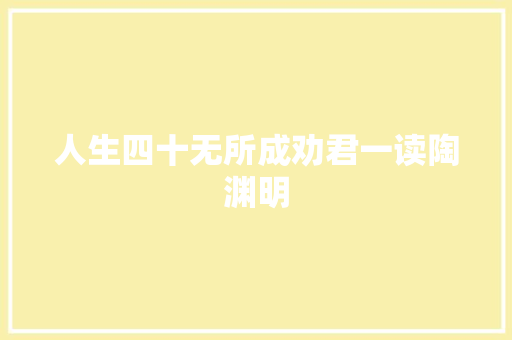
三十四岁,陶渊明入桓玄幕府。桓玄知道陶渊明干不了杂活儿,就聘任他为幕僚,实在便是帮闲,每天陪桓玄喝饮酒聊谈天,下下棋作作诗,俸禄还不低。陶渊明过得很愉快,可是愉快中看到了危急,便是桓玄所谋者大,准备自主为帝,之以是聘请陶渊明,皆因陶渊明名声在外,是当时隐居绅士中出类拔萃的人物,颇有影响力。养着陶渊明,可以向其他军阀(紧张是刘裕,他最有力的竞争对手)显著自己的号召力,连陶渊明这样“性本爱丘山”的大隐都可以网络幕中。
陶渊明自幼熟读儒家文籍,当然明白“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道理,因此时时想着抽身而退。奈何桓玄反态虽萌却未显,处于“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状态,大家知道桓玄要反,可是大家都不能说破,如果谁说破了,便是“察深渊之鱼”,会给自己惹来杀身大祸。就这样当心翼翼干了将近两年,一个噩耗传来,从小把他含辛茹苦养大的母亲去世了。
陶渊明于是光明正大的向桓玄请假,哀求回家奔丧尽孝。实在桓玄也知道陶渊明心思,想尽快分开自己掌控,可是也没有道理难堪他。晋人“以孝治天下”,为母守孝是所有士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不孝”会遭来杀身之祸,孔子二十世孙孔融便是因“不孝”的罪名被曹操满门抄斩的。桓玄于是给了他一笔钱粮,派人护送他回了家。实在还有个缘故原由,便是陶渊明实质上是个“散淡的人“,举大事用不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母亲的“恰好去世”救了陶渊明一命,就在他离开桓玄幕府不久,桓玄便举兵造反,自主为帝,却被刘裕等人打败,身死名灭。如果陶渊明依然是桓玄座上宾,后果不堪设想。
贤人云,四十不惑。又云,四十无闻,斯不敷畏。前一句说的是学有所成,后一句说的是业有所成。一个人活到四十岁,就能在学业上独当一壁,也能在奇迹上出人头地。闻即闻达。《论语·颜渊》:“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在邦必达,在家必达。”
奈何人生于世,“不快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谁人不爱颜如玉,谁人不爱千钟粟,谁人不爱黄金屋,只可惜这要看命中五行有没有安排上。坐拥豪宅,美人在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大家艳羡,个个敬仰,这样的“美好生活”当然可以有,但是这种生活只属于极少数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如陶渊明一样,过着“耕植不敷自给”“稚子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的生活,挣点勉强糊口的人为,养活一家老小,没有一分钱积蓄,想干点多挣钱的活儿,却是有心无力,找不到来钱的路。
陶渊明不是没有机会,事实上许多人都在给他机会。他身为晋室复兴名臣陶侃之后,也算出身名门,虽然没落了,可是其祖余荫尚在,因此二十多岁便进入各个州府视野,纷纭辟召他出仕为官。他也不是不把握机会,正好相反他是“汲汲于富贵”的,从小立下年夜志壮志,“进德肄业,将以及时”,时候准备大干一场,光宗耀祖,重振家风。为此孤身仗剑,走遍大江南北,最北到达幽州,最西到达张掖。这些地方盗匪各处,虎狼成群,时时都有性命之忧。可是陶渊明绝不畏惧,“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饿了吃野菜,渴了喝泉水,探求志同道合的人。奈何天下虽大,竟无一个心腹,“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饿去世首阳山的伯夷叔齐墓丘在秋风中萧瑟,提一匕首赴不测强秦刺杀秦王嬴政的荆轲孤魂在萧萧易水边的寒风中飘荡。
没人用他当夷齐,也没人用他作荆轲,只有人用他当一个食少事繁的小吏,干些毫无出息徒耗光阴的事情,日复一日,宛若一头蒙眼拉磨的驴。可惜这不是陶渊明想要的生活。
大丈夫进不能一遂平生之志,便只有退而躬耕读书,以求灵魂上的安宁。东晋期间,“读书无用论”大行其道,绅士领袖王恭就说:“绅士不须有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绅士。”殷仲文一代文豪,也是“读书不甚广”。在这样一个读书风气淡薄的时期,绅士们个个热衷于饮酒服散清谈(清谈便是扯淡,扯淡的淡便是清谈的谈),相互吹捧贬低,毫无真才实学可言,唯有陶渊明是个异类。
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的读书境界,便是孔子所谓的“乐”。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又说,君子之学为己,小人之学为人。君子读书学习是为了提高自身教化,做一个纯粹上道的人。小人读书学习是为了混口饭,顺便积累点吹牛逼的成本。陶渊明读书,便是君子之学。他一不为著书立说,二不为清谈玄言,没有任何“目的”,便是喜好读,并能从中找到乐趣。“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习至,自谓羲皇上人。”读书在我心,快乐似仙神。
陶渊明从前游历中原,曾入一个坞堡,坞堡是中原人为了躲避战乱凭险而据聚族自保的半军事化组织。坞堡中人活的无欲无求,“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陶渊明后来根据这段亲自经历写了《桃花源记》,桃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语云,不敷为外人性也。”
《桃花源记》是个文学作品,坞堡中人也过得没那么幸福清闲,却是大家神往的空想生活。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要有个桃花源,如果不堪世事骚动,便能避入个中,“怡然自乐”,而且此乐“不敷与外人性”。
陶渊明四十岁隐居的“园田居”,便是他的桃花源。他可以随意所欲的读书弄子,饮酒品茶,暮春时节,带着老婆孩子,穿着宽袍大袖,来到东郊野外,看绿草青青,白云悠悠,听流水潺潺,鸟鸣啾啾,闲咏以归。
但是,躲避只是暂时的,毕竟生活还得连续。四十岁正值壮年,陶渊明壮志未消。他“总角闻道,白首无成。”学了一肚子经世报国的知识,头上已生白发,却是一事无成。譬如驽马,恋栈不已。避入桃花源只是暂时小憩,吃饱喝足,还得重整装备,再次出发,毕竟下有唯唯幼子,中有跟自己同甘共苦费力操劳的荆妻,一味躲避,绝非大丈夫所为。一时躲避可谓疗伤,一世躲避便是懦夫。
此后不久,他便再次出山,担当刘裕幕府参军。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桃花源,当你心情低落时,彷徨无助时,只需避入其间,便能瞬间被治愈。陶渊明将自己安身立命和修身养性的大聪慧,奥妙而自然的融入每一首诗里,读来让人怡神忘忧,焦虑烟消云散。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陶渊明集》,注释清新,装帧雅美,随书附赠三首古筝曲,实为爱书之士阅读收藏之佳选。人生四十无所成,劝君一读陶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