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建
自去射虎得虎归, 官差射虎得虎迟。
独行以去世当虎命, 两人因疑终不定。
朝朝暮暮空手回, 山下绿苗成道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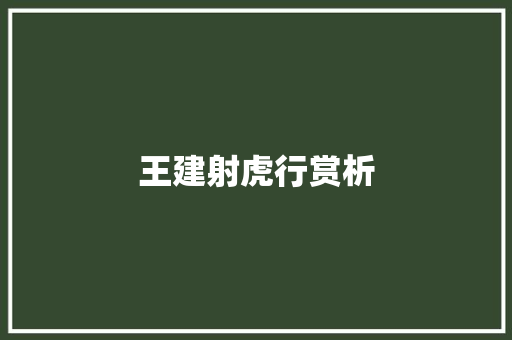
远立不教污箭镞, 闻去世还来分虎肉。
惜留猛虎着深山, 射杀恐畏终生闲。
初读《射虎行》,可能以为它和某些当代派的“朦胧诗”相似:每两句构成的一个局部都是明明白白的,组合到一起的整首诗却颇有点模糊。王建在这首诗里表达的究竟是若何一种认识和情绪呢?是早在《论语》里即已写到的“苛政猛于虎”,是俗话所说的“三个和尚没水吃”,抑或还有其他?
不过,《射虎行》这首乐府毕竟不是朦胧诗,它的意向旨归还是确定的。只要过细一点,就不难创造,解读这首诗的“密码”仅在于弄清第二句中“官差”二字的含义。对“官差”二字的不同理解,将影响着对付全诗主题的论定。
作为一个名词,“官差”是指官府的差役,胥吏也罢,兵丁也罢,他们本是公门中人;作为一个主谓词组,“官差”则指官府差派。官府可以差派哪些人呢?固然可以差派“公门中人”,但也不排斥差派猎户和一样平常山民的可能。当然,还不妨把“官差”作为一个省去中央词的名词性词组阐明,不过含义仍同于第二种。
大概把“官差”理解为官府差役是一条较好的思路。由于如果解为猎户、山民,以下诗句难以得到合乎情理的阐明,而且和王建总体创作方向相悖。只有解为官府差役,诗意才显豁畅达。
诗的前四句,两两相对地构成比拟。“自去射虎得虎归,官差射虎得虎迟”,这是两种结果的比拟;“独行以去世当虎命,两人因疑终不定”,这是两种态度的比拟。正是不同的态度带来不同的后果。百姓们身受虎害,射虎时自然以去世相拚,总要撤除虎患;至于官府差来的人,他们心中各有一番计算:我何必冒着生命危险奋勇当先,坐收渔利岂不更好?以是态度总是游移的。五至八句,墨客以淋漓的笔墨着意刻画官差卑怯贪婪的丑态:每天煞有介事地上山射虎——自然少不了吆五喝六地让百姓们供奉应酬,恐怕连虎的影子也难以见着,军队倒是浩浩荡荡的,“朝朝暮暮空手回”,竟然把“山下绿苗”也踩成了道路。等到真地见到虎了(这多数还是无法忍受猛虎为害和射虎“勇士”糟践的百姓们自发扑虎的时候),他们大家畏缩,远远地站立着,一支箭也不敢放,直到虎被打去世,他们才装怯作勇,蜂涌而上,而目的却是分一块虎肉。结尾两句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作者(或者射虎的百姓)对官差的反语讥讽:你们是故意把虎留在深山的吧,如果射杀了,你们这一辈子干什么呢?一种是“勇士们”的自我解嘲。意思和上一种理解大体相同,不过要把话语中的“你们”换成“我们”。人称改换了,味儿也就变了。“惜留猛虎在深山,射杀恐畏终生闲。”现在你们把猛虎射杀了,我们再到哪里去讨这份美差呢?言外之意,不外乎山民们射去世猛虎反而害苦了他们,对不住他们!
把这两句作为解嘲之语,加倍能够画出官差们的无赖相。
根据上述理解,我们可以说《射虎行》不仅为公民发出了反抗的呼声,而且闪耀着讽刺的光芒。且不说前文已经引用的那些正面描写官差丑态的生动的诗句,单是“远立不教污箭镞”中一个“污”字,就显露出墨客对付官差们的极度厌恶与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