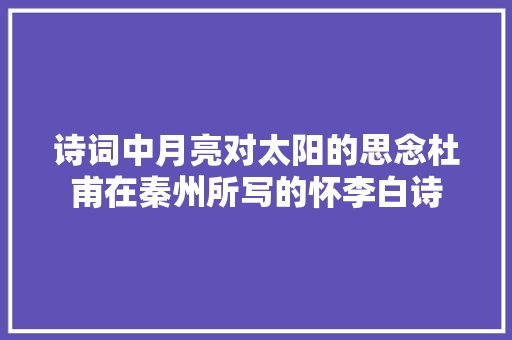梦李白二首
去世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
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落坠。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干瘪。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清人方不雅观承云:“少陵梦李白诗,童而习之矣。及自作梦友诗,始益恍然于少陵语语是梦,非忆非怀。”(方世举《兰丛诗话》引)说二诗“语语是梦”,不很准确,由于第一首的前四句分明是写未梦之前,第二首的前四句也是交代梦之由来。但是说全诗主旨是梦而“非忆非怀”,则一语中的。由于是写梦境,全诗就笼罩着一片迷离恍惚的雾气。试以第一首为例:“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写梦中与李白相遇,竟疑惑来者并非生人的魂魄,言下之意故人或已化为幽灵,由于路途迢遥,存亡未卜。“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二句分写李白所在之江南与杜甫所处之秦州,两地相隔万里,景象皆惨淡阴森。清人沈德潜说这是“点缀楚辞,恍恍惚惚,使读者惘然如梦”(《唐诗别裁集》)。
蒲松龄在谈神说鬼的《聊斋志异》自序中说:“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显然也是有取于这两句杜诗的阴惨气氛。及至结尾四句,清人浦起龙解曰:“梦中人杳然矣,偏说其神犹在,偏与打发叮嘱。”(《读杜心解》)也便是把梦境的恍惚感一贯延伸到梦醒之后:残月的余晖映照在屋梁上,仿佛还照着李白的容颜,于是诗人情意殷殷地叮嘱他在归路上务必把稳安全。刘辰翁说:“落月屋梁,有时实景,不可再遇。”(《唐诗品汇》引)“落月满屋梁”确实可能为实景,但用一缕暗淡的落月之光来衬托凄迷的梦境,又是何等的生动真切!
如果说第一首的着力之处是渲染梦境,那么第二首中的重点便是刻画梦中所见的李白形象。曾经是英风英气不可一世的李白如今变成了一个干瘪老人,他匆匆告别,再三诉说远道而来的困难:江湖上风波险恶,扁舟出没于其间,令民气惊肉跳。临出门时,他举手搔搔满头白发,一副潦倒失落意的样子容貌。这便是曾被贺知章称为“谪神仙”的李白吗?这便是那位“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二韵》)的李白吗?如今安史之乱初步平定,长安城里满盈着王侯将相,而李白却独自干瘪如此!
于是杜甫对命运发出了严厉的责问:谁说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李白垂垂老矣,却反而受到如此的牵累!那么,为什么杜甫梦中所见的李白是如此落魄潦倒呢?为什么杜甫要为李白心坎不安且年夜声鸣冤呢?让我们再读写于同时同地的《天末怀李白》: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达,病魅喜人过。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与《梦李白二首》的恍惚意境不同,此诗以非常复苏、非常镇静的语气抒写对李白的思念。秦州地处北部边陲,秋风已寒,鸿雁南飞,此时此地,杜甫分外思念远在天边的李白。后四句说到魑魅,又说到汨罗冤魂,表明此时杜甫已经得知李白开罪长流夜郎的。原来在去年(公元758年)仲春,李白因误入永王李銮军一事被判处长流夜郎,本年夏秋之间,李白行至夔州,适遇朝廷大赦,当即乘舟东归。“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轻快诗句便是那时写的。但是古代传得很慢,杜甫又僻居边陲,以是他仅知李白长流夜郎,还以为此时李白正在走向夜郎的途中。唐代的夜郎处于现在湖南西部的芷江,李白从江州出发前往夜郎的路线是溯江西上,至夔州再南下,经由地处湘西的“五溪”。十四年前李白送王昌龄贬龙标尉的诗中说“闻道龙标过五溪”,也是指的这条路线。杜甫当然不知道李白所走的实际路线,他以为李白会从洞庭湖折而向南,并经由汨罗江一带。汨罗江与“五溪”相隔不远,古人认为那里是瘴疠之地,是魑魅魍魉出没的地方。据《左传》记载,舜曾流放“四凶”:“投诸四裔,以御魑魅。”由于魑魅是食人的厉鬼,喜人经由而得以食之。如今李白被远流夜郎,怎不令杜甫忧虑万分?杜甫又想到李白才高见谤,无罪受罚,当他经由汨罗江畔时,一定会像汉初的贾谊一样,投诗汨罗,与屈原的冤魂相互倾诉苦处。这既是对李白的透彻理解,又是对李白的深切同情。关于“魑魅喜人过”一句,清人何焯引其师李光地之解曰:“嵇叔夜耻与魑魅争光,此句指与白争进者言之。鬼神忌才,喜伺过失落。古人四声多转借用之,非‘过从’之‘过’也。”(《义门读书记》)这种阐明也可讲通,但不如前解意味深长。正如仇兆鳌所评,此诗“说到流落死活,千里关情,真堪声泪交下,此怀人之最惨败者”(《杜诗详注》)。
李白入永王李璘军因而开罪之事,其经由环境非常繁芜,后人的议论也莫衷一是。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六月马嵬坡事变发生后,玄宗连续西奔。七月,太子李亨登基于灵武,是为肃宗。玄宗在入蜀途中,没有及时得到太子登基的,仍以天子的名义颁令支配,永王李璘被任为江陵府都督及江南西道等四道节度使。李敖是李享的幼弟,幼年丧母,曾由李享抚养,晚上常由李享抱着睡觉。但李璘长于深宫,不明道理,履新江陵后见地方富庶,就滋长野心,想要向东南发展势力。肃宗闻知,令其归蜀,李璘不从,并引军沿江东下。肃宗随即支配军队予以讨伐。李抟军路经九江时,正在庐山的李白应聘入李璘军为僚佐。次年李璘军溃败,李白先是奔逃,后又自首,系于浔阳狱中。及至乾元元年,终于被判长流夜郎。李白后来自称是受到胁迫而入李璘军的:“半夜水军来,寻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但事实并非如此,李白的《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便是明证,像“雷鼓嘈嘈喧武昌,云旗猎猎过寻阳。秋绝不犯三吴悦,春日遥看五色光”(其三) ,像“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其五) ,哪里是被胁迫的口气?但要说李白是有心从逆,则难免不免厚诬古人。李白其人,向有报国济时的远大志向。李璘聘其入军,当然会被李白看作实现报国雄图的绝好机会,这在《永王东巡歌》之二中表露得非常清楚:“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原来李白齐心专心想着像东晋的谢安那样,在谈笑之间建立奇功,一举平定叛乱。李白是个激情亲切洋溢的墨客,他对朝廷内部的明争暗斗不甚了然,对李逵的个人野心也毫无觉察。宋人朱熹说:“李白见永王璘反,便从臾之,文人没头脑乃尔!
”(《朱子语类》)说李白“从臾”永王是毫无根据的,但说他“没头脑”倒不无道理,李白确实激情亲切有余而镇静不敷,他毕竟是个英气干云的墨客而已,其政治见识不但不如善于运筹帷幄的李泌,也比不上长于不雅观察形势的杜甫。但是,李白此举虽然不足明智,毕竟不是什么弥天算夜罪,又何以受到流放蛮荒的严重惩罚?况且李白英才盖世,齐心专心报国,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怎么也该予以保护呀!
大概杜甫在两年往后所写的《不见》一诗更可加深我们的理解:“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众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为什么李白会落到“众人皆欲杀”的地步呢?除了政治缘故原由以外,恐怕与他的才太高、名太大不无关系。凡是才高一世者,每每会遭到庸众的妒忌。名满天下者,谤亦满天下。况且李白一向恃才傲物,唾弃权贵,朝廷中对贰心怀忌恨者大有人在。在这种环境下,杜甫的这三首诗尤其值得重视。一方面,杜甫为人,特重感情,梁启超称他为“情圣”,诚非虚言。一部杜诗,凡咏及友情者,无不情文并茂。另一方面,杜甫与李白的交情又非他人所能及,正如浦起龙评杜甫所云:“公当日文章契交,太白一人而已。”(《读杜心解》)宋人严羽说得更加真切:“少陵与太白,独厚于诸公。诗中凡言太白十四处,至谓‘众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其情好可想。”(《沧浪诗话》)以是当李白蒙冤流放时,全体诗坛上只有杜甫在迢遥的北陲连写三诗以抒情念之情。清人《唐宋诗醇》评《梦李白二首》曰:“沉痛之音,发于至情,情之至者文亦至。友情如此,当与《出师》《陈情》二并读,非仅《招魂》《大招》之遗韵也。”又评《天末怀李白》云:“悲歌年夜方,一气舒卷。李杜交好,其诗特地精神。”的确,只有杜甫才能写出如此情真意切的怀念之诗,也只有李白才当得起如此触目惊心的怀念之诗。《梦李白二首》的末了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这既是杜甫为李白发出的不平之鸣,也是杜甫对自身命运的准确预言。万里上苍上只有一对日月,千年诗国中也只有一对李杜,以是《梦李白二首》与《天末怀李白》是千古独绝的友情颂歌。